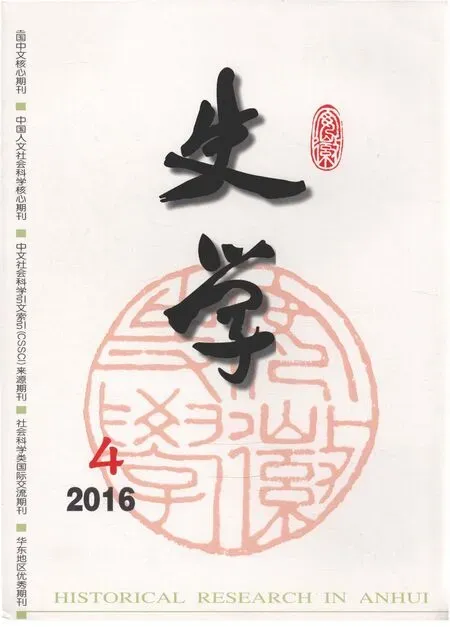民主政治對于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
——以抗戰時期知識界對“中華民族復興”的討論為中心
鄭大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
民主政治對于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
——以抗戰時期知識界對“中華民族復興”的討論為中心
鄭大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摘要:抗戰時期隨著民族復興思潮的興起,知識界圍繞中華民族能否復興和如何復興展開了熱烈討論,而“民主政治對于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是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當時主流知識界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取得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而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就必須實現政治的民主化,使全國人民享有各種民主權利,使各黨各派能夠真誠地團結起來。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民族是不可能復興的,而只有實行民主政治,國家才有可能實現長久的統一。同時,民主政治本身也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特征,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政治要求和目標。。
關鍵詞:抗戰時期;民主政治;民族復興;知識界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華民族復興”之思想則有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概而言之,清末是“中華民族復興”之思想的孕育或萌發期;五四前后是其初步發展期;“九·一八”后的抗戰時期是其進一步發展并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思潮期*詳見鄭大華:《甲午戰爭與“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萌發》(《中國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論“中華民族復興”思想在五四時期的發展》(《安徽史學》2015年第2期)、《論“九·一八”后“中華民族復興”思潮的形成》(《史學月刊》2015年第6期)。,當時的知識界圍繞中華民族能否復興和中華民族如何復興這兩個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而“民主政治對于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是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當時主流知識界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取得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而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就必須實現政治的民主化,使全國人民享有各種民主權利,使各黨各派能夠真誠地團結起來。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民族是不可能復興的,而只有實行民主政治,國家才有可能實現長久的統一。同時,民主政治本身也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特征,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政治要求和目標。但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學術界對中國近代民族復興思潮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鮮有學者涉及到“九·一八”后的抗戰時期知識界有關“民主政治對于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的討論。有鑒于此,筆者不揣冒昧,擬對這一問題作一初步探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關于抗日戰爭的時間,采納“14年說”,即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因為“九·一八”事變后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不僅促進了中華民族復興從思想發展成為一種思潮,而且從“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的日本投降,知識界對“中華民族復興”的認識也呈現出明顯的連續性。
一
“九·一八”事變,使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危機迫在眉睫。中國知識界希望通過抗戰來實現民族復興。“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不久,陳啟天即撰文指出,中華民族已無退路可言,“中國要起死回生只有對日作戰”,只有堅持對日作戰,才可以改造我們衰弱不振的民族精神,才可以鼓舞人民的斗志,使一般國民打消個人的和家族的觀念,不得不共赴國難,因此“對外作戰是創造斗爭的民族精神之最好方法”*陳啟天:《我們主張對日作戰的理由》,《民聲周報》第2期,1931年10月。。曾琦等人認為,古今中外,未有不戰而能立國者,歐洲的普魯士與亞洲的日本都是通過戰爭確立其強國地位的,中國也只有通過艱苦抗戰才能實現民族建國偉業,并堅信通過抗戰一定可以實現民族復興:“現在正以空前勇敢的精神,接受建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流血洗禮,我們相信一個獨立自由的全民福利國家,必然在血的洗禮后產生出來,而且也只有在血的洗禮中才能產生出來,因此我們對于抗戰的前途,絲毫不悲觀,不氣餒,我們準備與全體中國同胞攜手勇敢地接受這個歷史的任務。”*《中國青年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青年黨》,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124頁。馮玉祥指出,民族復興的問題雖然“關涉的范圍至為廣大,內容亦千頭萬緒,非常復雜”,但總的來說是“以救亡圖存為中心,……即我們必須用抗戰手段,以清算‘九一八’以來的外來侵略,而達到民族自由平等的目的”,因此中華民族復興的核心問題“第一個是抗戰,第二個是抗戰,第三個還是抗戰”*馮玉祥:《復興民族的基本方案——抗戰,抗戰,抗戰!》,《解放日報》1937年l月22日。。黃炎培回憶說:“自從‘九一八’事發,吾們內心起了極大的沖動,精神受了極大的影響。吾們親切地看出,在我們中國這樣一個政治上經濟上受著種種枷鎖的國家,所謂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統一于國家民族的解放。”*黃炎培:《從困勉中得來》,《黃炎培教育文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頁。
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實際上,自鴉片戰爭以來,民主政治就一直被視為挽救民族危機的重要手段,爭取民主政治與爭取民族獨立始終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以林則徐、魏源、徐繼畬等人為代表的經世派士大夫們,為尋求國家富強之路,開始睜眼看世界,盡管當時他們還不可能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有真正的認識和理解,但作為晚清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他們已朦朧地感受到這種制度在某些方面要比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優越。19世紀七、八十年代,當鄭觀應、王韜等早期維新思想家提出采用“君民共主”的政制時,其根本目的是通過民主政治實現國家的獨立富強,抵抗外族的侵略。因為在他們看來,西方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在于能有效地消除君主與人民之間的隔閡,從而做到上下一心,舉國團結。稍后,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思想家之所以主張興民權,也是因為他們認識到,“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西方富強的原因,就在于實行的是民主制度,“人人有自主之權”,中國所以貧弱,也就在于中國實行的是封建專制制度,“收人人自立之權,而歸諸一人”。既然有無民權,是西方和中國一盛一衰、一強一弱、一富一貧的根本根源,那么,中國要救亡圖存,實現富強,其不二法門自然是“興民權”。用梁啟超的話說,“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梁啟超:《愛國論》,《飲冰室合集》第1冊“文集之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3頁。孫中山之所以要推翻清王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他看來,中國陷入被列強“瓜分豆剖”之境地的根源,是清王朝的軟弱不振和賣國投降。他曾沉痛指出:“曾亦知瓜分之原因否?政府無振作也,人民不奮發也。政府若有振作……外人不敢側目也。”因此,中國“欲免瓜分,非先倒滿洲政府,別無挽救之法”*孫中山:《駁保皇報書》, 《孫中山全集》(一),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33、234頁。。這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走狗。”*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頁。
抗日戰爭時期,空前的民族危機使知識界進一步認識到實行民主政治對于救亡圖存、取得抗戰最終勝利的積極意義。
首先,只有實行民主政治,給廣大民眾民主自由的權利,才能充分調動他們抗戰的積極性。1938年,中國青年黨在紀念抗戰周年的宣言中指出:“在這個抗戰建國的艱巨工作上,我們認為非發動民眾共同一致努力,不能收到圓滿的成功。而發動民眾,則非實現民主政治,不能使民眾自動自發的繼續犧牲,毫不反顧。因此我們主張為使作戰的政府建筑在更廣大更熱忱更自動的同情基礎之上,中國政治是有更進一步地擴大民主化運動之必要,國民參政有更進一步設立各省各縣民意機關之必要。”*《中國青年黨為抗戰周年紀念宣言》,《國光》第12期,1938年7月。1939年,韞明在文中寫道:“兩年來抗戰的教訓指示給我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重要基礎,是建筑在動員全國民眾參加抗戰建國的上面。而唯有建立起憲政規模,才能收取動員全國民眾參加抗戰建國的實效。”*韞明:《實行憲政與抗戰建國》,《時與潮》第4卷第5期,1939年。潘梓年在文中強調:“抗戰需要憲政”,需要實行民主政治,因為抗戰要能堅持下去,取得最后勝利,必須依靠廣大民眾,將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智力統統的動員起來,來為抗戰服務,來準備起足夠的力量,對敵人進行戰略上全線的反攻。而要把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智力統統動員起來,就需要實行憲政,實行民主政治*潘梓年:《憲政運動與抗戰建國》,《理論與現實》第1卷第3期,1939年,第1—4頁。。高靈光則認為:我們的抗戰是以持久消耗敵人的實力為戰略,需要動員全國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的支持,尤其是人力“為最重要之因素”,而動員全國民眾積極投入到抗戰中來,“自非尊重民意伸張民權不為功”,也就是說,要“動員全國民眾爭取最后勝利”,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高靈光:《抗戰建國與實行民主政治》,《學生之友》第1卷第2、3期合刊,1940年。。
其次,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實現各階層各黨派的大團結,也才能真正使全國的力量集中起來。李拾豪在批評那種認為“民主政治是不適宜于抗戰時期,抗戰時期所需要的是集中力量”的言論時指出:在抗戰中需要集中各階層各黨派的力量,這是毫無疑義的,但目前各階層各黨派利害的對立是事實,各階層各黨派的“相互猜忌、嫉妒及恐怖”也是事實,而要緩和各階層各黨派的利害對立和沖突,緩和這種相互間的“歷史的和現實的猜忌、嫉妒及恐怖”,實現各階層各黨派的大團結,“民主的憲政制度的確立是最需要的”。因為“民主政治并不是一般所想象的可以制造糾紛增加紛亂的事情,相反的,他可以變紊亂的暗中摸索的相互磨擦,成為公開的、坦白的、光明的、有規律的匯合。中國過去解決政治問題,只是用力的方式來解決,不是用合理的政治方式來解決,所以二十余年來的政治,永遠不會走上軌道”,各階層各黨派永遠處于分裂內爭的狀態。法國是一個黨派最多的國家,內閣的更迭也很頻繁,但由于法國實行的是民主的憲政制度,“軍事力量始終統一在整個系統之下”,國力沒有受到任何影響。法國的經驗告訴我們,要真正實現各階層各黨派的團結,使各階層各黨派的力量真正集中起來,從而保證抗戰建國取得最后的勝利,就必須實行民主的憲政制度*李拾豪:《抗戰建國與確立民主的憲政制度》,《抗戰十日》第2期,1938年。。
再次,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才能“得道多助”,爭取到國際上民主國家的支持。高靈光指出,此次抗戰,不僅僅是要爭取本國的獨立與自由,而且也是為了維護國際正義,其性質與18世紀的美國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相類似,美國之所以能以小勝大,以弱勝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是為獨立和自由而戰,其“宗旨正大”,博得了各方的同情和支持。我國現在進行的抗日戰爭,也是弱者抵抗強者的侵略、公理反抗強權欺凌的正義戰爭,其目標也是要爭取國家的獨立與自由,“故必外則排除暴力羈絆,內則維護全民福利,伸正義于世界,博國際之同情,得道多助,其有造于抗戰建國者至要且切,所謂爭取獨立自由,維護國際正義,必須實行民主政治。”*高靈光:《抗戰建國與實行民主政治》,《學生之友》第1卷第2、3期合刊,1940年。
除了正面闡述實行民主政治對于救亡圖存、取得抗戰最終勝利的積極意義外,知識界還對種種懷疑甚至反對于抗戰時期實行民主政治的觀點提出了反駁和批評。韞明指出,那種以為“在抗戰緊急的階段里倡議施行迂緩的憲政問題”,有些“緩不濟急、時非所宜”的“看法是不對的”,因為,第一,“發揚民主施行憲政是爭取最后勝利不可缺乏的主要因素,舍此幾乎可以說談不到最后勝利”;第二,“一般所倡議的民主和憲政,也是要機動地適應戰時的,并且必須是非漢奸的個人或非漢奸的團體,才能使其享有身體的和言論集會結社的充分自由”;第三,“敵寇政治進攻的花樣很多,已導演著汪逆精衛在滬召開過偽國民黨代表大會,現正積極籌備偽中央政權的開幕,在這個時期說不定還要演出召開偽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等把戲,為了打擊汪逆漢奸也有及時從速實施憲政的必要。”*韞明:《實行憲政與抗戰建國》,《時與潮》第4卷第5期,1939年。曾琦也對那種認為軍事力量是實現抗戰勝利的根本保障,而政治上是否民主根本無所謂的觀點進行了駁斥:“殊不知集權國家全憑一人之智能,以決國家之運命,其對內則尚獨裁而反民主,對外則主侵略而反和平。民主國家則賴萬眾之同心,以謀國家之福利,其對內則尚民主而反專制,對外則尚和平而反侵略,……能合全民之力以一致御侮”,并指出軍事與政治是相輔相成的關系,“軍事之勝利,有資于政治之調整;而政治之調整,實賴于憲法之綱維。然則憲政運動與‘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又何沖突之有哉?”*陳正茂等編:《曾琦先生文集》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212、214頁。沈鈞儒批駁了“抗戰時期談不上民主,也不需要民主”的謬論,強調抗戰不單純是軍事力量的較量,更是民眾力量的比拼;抗日戰爭曠日持久,“在這樣嚴重的全面持久抗戰中間,中國很迫切需要造成一個全國整的力量。這個整的力量,是民眾與軍事的配合”,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才能改變“在政治落后于軍事的現狀下,民眾動員還大大的不夠” 的不利現狀,進而取得抗戰的勝利*《沈鈞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0、434頁。。
既然要實現民族復興,就必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取得民族的解放和獨立,而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取得民族的解放和獨立,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因此在抗戰時期,知識界普遍強調民主政治與民族復興之間的有機聯系,強調以實現民族復興為目標來推動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他們紛紛以著書立說、創辦報刊、參政議政等方式,積極宣傳他們的抗戰思想和民主政治主張。章漢夫強調說,“絕對不是完全工業化后才能實現民主,而是一定要民主,然后才能實行全民動員,抗戰到底,掃清工業化發展的障礙。”*章漢夫:《批判兩種錯誤理論》,轉引自虞和平:《中國現代化歷程》第2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7頁。侯外廬則提出了“抗戰民主”的概念,認為抗戰民主是一種戰時民主的特殊形式,是適應抗戰需要、取得抗戰勝利的必要手段,因為“抗戰依賴民力,而民力與民權(民主)則相為因果”,其最低限度的任務是“建立反貪污、反漢奸的,遂行積極動員民眾的政治機構;同時在于融洽少數民族,并使自主參加政治的廣泛政治機構;抗戰民主最要的,是在抗戰過程中,積極淘汰腐朽動搖不定份子,而廣泛容納進步的抗戰最力的新的社會力量,使抗戰的民主號召的形式,與抗戰犧牲的民主權利的內容,相配合起來。抗戰的民主平等形式,同時亦是民主自由形式。”*侯外廬:《抗戰建國與民主問題》,《抗戰建國論》,生活書店1938年版,第1—9頁。梁漱溟則提出包括政治民主化的抗戰三原則,并且強調指出,要“舉國都工具化”,“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有知識的出知識”,就必須實現“舉國主體化,那就是全國國民的感情要求思想意志,必須疏通條達,求其調協而減少矛盾,求其溝通而減少隔閡”,而要做到這一點,政治就需要“民主化,政府與社會打成一片,而后統一節制始得順利進行。”*梁漱溟:《怎樣應付當前的大戰》,《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3—1034頁。鄒韜奮認為,中國的抗戰只是動員了一部分的軍事力量,而未充分調動全國整個的民眾力量,如果實行民主政治,讓“全國人民都以赤誠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盡量反映民意,結果只是增強政府抗戰的力量,也就是增強全國抗戰的力量。”*鄒韜奮:《反映民意與抗戰前途》,《韜奮全集》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頁。胡愈之也撰文指出:“要支持抗戰,得到最后勝利,只有一條路,就是民主。”沈鈞儒在《新華日報》上題詞:“以團結支持抗戰,以民主鞏固團結,是目前救國的途徑。”*沙千里:《漫話救國會》,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頁。陳啟天指出,西方民主史上重要的文獻如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都是產生于戰爭時代。因此,中國在抗戰時期也應實施民主憲政,并列舉出三條理由:“一由于戰時需要人民出錢出力,而使人民樂于出錢出力的方法,則莫如實施民主憲政;二由于戰時需要人民精誠團結,而使人民易于精誠團結的方法,亦莫如實施民主憲政;三由于戰時需要予人民以政治上的希望,而使人民感覺政治有希望的方法,更莫如實施民主憲政。”*陳啟天:《民主憲政論》,商務印書館1945年版,第14、15頁。
總之,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的抗戰積極性,才能實現各黨各派的真誠團結,從而確保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實現民族的解放和獨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必要的前提。這是民主政治對于民族復興的第一個重大意義。
二
民主政治對于民族復興的第二個重大意義是:民族復興的基礎或根本條件是國家的統一,而只有實行民主政治,國家的統一才有實現的可能。建人從民族與國家的關系入手,論證了國家統一對于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他指出:民族與國家的關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民族是構成國家的基本要素,即所謂沒有人民即沒有國家是也。第二,民族雖是構成國家的基本要素,但國家是民族生存的絕對保障。第三,國家和民族的利害是共通的,一致的。國家之福亦即民族之利,民族之敵亦即國家之害,未有民族受威脅而國家獨能安固,亦未有國家受壓迫而民族仍能無事者。基于以上三點,我們可以知道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是一件事,沒有統一的國家而民族衰亡,也沒有復興的民族而國家不統一。民族雖然構成國家,但不必一定構成國家,反之,國家雖由民族所構成,但民族非受國家的力量保障不可。就此而言“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要保障民族的獨立生存,必須有強固的統一的國家。我國積弱至今已數十年,其原因雖然很多,然國家不統一實為其主要原因。因為國家不統一,致國力不能集中,外侮乃無由抵抗,國家隨陷于次殖民地位。”中華民族欲謀求“復興”,非有統一的國家不可,“統一國家是民族復興的前提”*建人:《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現代青年》第5卷第3期,1936年。。和建人不同,楊錦昱主要是從各項救國工作的輕重緩急著眼,強調了要實現民族復興就必須先實現國家的統一。其文章寫道:我們在提出種種民族復興的建議和方案的時候,“首先須注意到一個前提,就是不在于多開些怎樣挽救民族危亡的方案,而在要使每一個方案都有實行的可能,因為方案雖好,假使其事實上不能實行,則終不過是紙上談兵,到底不能發生效力,究有什么用呢?”在作者看來,中國目前所急需進行的工作,不是振興教育,開發實業,刷新內政,整頓國防,而是在于完成統一,“換句話說,一切民族復興的方案,不在完成實質統一之后,則無著手實行的可能。”*楊錦昱:《復興民族與鞏固統一》,《江漢思潮月刊》創刊號,1934年。
國家的統一對于民族復興是如此的重要,那么怎樣才能實現國家的統一呢?對此,知識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蔣廷黻提出了武力統一論。他在《論專制并答胡適之先生》一文中寫道:中國要實現統一,而“統一的敵人是二等軍閥和附和二等軍閥的政客。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聯合起來,假打倒專制的名,來破壞統一”。由于“破壞統一的就是二等軍閥,不是人民,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他們既以握兵柄而割據地方,那末,惟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從而實現國家的統一*蔣廷黻:《論專制并答胡適之先生》,《獨立評論》第83號,1933年12月31日。。吳景超在總結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后也贊同武力統一論,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例外,統一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因此,中國目前要實現統一,也只能夠以武力來完成*吳景超:《革命與建國》,《獨立評論》第84號,1934年1月7日。。
對于蔣廷黻等人提出的武力統一論,參加討論的大多數人并不贊成。胡適就指出:“武力統一是走不通的。”因為,一方面,中國知識思想界存在著“種種沖突矛盾的社會政治潮流”,這不是武力所能打倒和解決的。另一方面,“中國疆域之大和交通之不便。這都是武力統一的絕大障礙。”*胡適:《武力統一論》,《獨立評論》第85號,1934年1月14日。退一萬步說,即使武力能夠統一國家,但也不能持久。“一個國家的統一,決不能單靠武力一項把持各部分使他們不分崩。國家的統一其實就是那無數維系各部分的相互關系的制度的總和。武力統一之后,若沒有那種種維系,統一還是不能保持長久的。”*胡適:《政治統一的意義》,《獨立評論》第123號,1934年10月21日。
武力不能統一中國,那什么能夠統一中國呢?胡適認為,只有政治才能統一中國。為此,他先后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政治統一的途徑》和《政治統一的意義》等系列論文,就“政治統一”的有關問題進行了闡述。他指出:“我們要認清,幾十年來割據的局勢的造成是因為舊日維系統一的種種制度完全崩壞了,而我們至今還沒有建立起什么可以替代他們的新制度……今日政治上的許多毛病,都只是制度上不良的結果。”*胡適:《政治統一的途徑》,《獨立評論》第86號,1934年1月21日。而所謂“政治統一”,就是要建立起能夠“維系全國,把中央與地方連貫成一個分解不開”的新制度,從而使中央與各省密切地連貫起來,“使全國各地都感覺在這重重疊疊的關系之中,沒有法子分開。”而民主政治下的“國會制度”就“是一個最扼要又最能象征一個全國大連鎖的政治統一的制度”*胡適:《政治統一的意義》,《獨立評論》第123號,1934年10月21日。。因為“國會制度”的功用,“是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交通聯貫的中樞,它是統一國家的一個最明顯的象征,是全國向心力的起點。”*胡適:《政治統一的途徑》,《獨立評論》第86號,1934年1月21日。胡適要人們相信,只要我們建立起民主政治下的國會制度,國家的統一是完全可能實現的。首先,華夏文明大一統的民族國家歷史為后人奠定了實現統一的靈魂,共同的歷史文化、風俗宗教以及語言文字都是促進中國實現統一的向心力。其次,近代興起的文化機制(如新式教育、報刊、報紙)、交通通訊工具(如鐵路、輪船、郵政、電報),也十分有益于民族國家觀念以及愛國思想的傳播。“今日我們的民族國家的輪廓的統一,是靠那些老的歷史關系和這些新的連鎖支撐著的。”*胡適:《政治統一的途徑》,《獨立評論》第86號,1934年1月21日。
胡適提出的“政治統一”的主張,得到了常燕生的支持。他說:“現在所急切要問的是怎樣才能完成中國的統一?中國的民族,文化,語言,文字,乃至經濟生活,本來都早已是統一的,所以中國的問題就僅僅余下了個政治統一的問題。怎樣才能使中國政治統一?這就是我們目前所迫切要問的問題。”*常燕生:《建國問題平議》,《獨立評論》第88號,1934年2月4日。齊思和同樣建議利用現代政治制度來實現國家統一。他認為:“現代國家之所以能夠達到徹底統一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一般人民在思想上大體是一致的(至少大多數是一致的),而他們在思想上的一致是根據物質環境。交通的便利掃除了地方間的隔膜,大規模的生產統一了大家的嗜好。”以美國為例,從前美國因為面積太大,交通不便,各地方的思想觀念很不一樣,但自從工業革命以后,交通大大地便利,而交通的便利促進了信息的傳播,地方的偏見也就漸漸地消失了,“到了現在,全國人民所看的是同樣的電影,所聽的是同樣的播放,所讀的是同樣幾個風行的報紙,所乘的是同樣式的汽車,所用的都是那幾個公司的出品,又何怪他們所想的都是同樣的問題,所討論的是同樣的事體呢?”因此,他認為目前中國統一的關鍵,是在大力發展交通的同時,加強各地之間“文化思想上”的“溝通”,如“將內地出版的書籍、報紙、雜志”,盡量向各地尤其是偏遠的地方“介紹”,各大學實行教授交換,“借以交換思想”,“而私人方面多組織旅行團、考察團,觀摩彼此的情況,促進正確的了解”,從而為“政治統一”打下良好的基礎*齊思和:《兩粵事變與中國統一》,《獨立評論》第213號,1936年8月9日。。
和胡適等人不同,王造時認為,中國不統一的根本原因是國民黨的不統一造成的。他在《國民黨怎么辦?》一文中指出:六年的訓政告訴我們,國民黨本身是絕對不能統一的。武有武的地盤,文有文的系統。黨內有派,自昔已然,于今尤烈。這是事實,無可諱言。六年的訓政,也同時告訴我們,中國在不統一的國民黨的專政之下,是絕對不可能統一的。“國民黨既不能統一,國民黨不統一的專政致使中國也不能統一”,那么,我們要想中國統一,結束分裂的局面,其唯一方法,就是“結束訓政,實行憲政”,讓國民有言論、出版和政治結社自由*王造時:《國民黨怎么辦?》,《主張與批評半月刊》第1期,1932年11月1日。。張培均也認為,“唯民主的力量”,方可制裁軍閥,“破除割據”,實現國家的統一。他曾游歷過四川等地,發現“民主輿論愈薄弱者,軍人愈專橫;民主輿論愈強毅者,軍人愈畏縮。”所以,民主政治的有無,事關國家的統一*張培均:《內政的出路》,《主張與批評半月刊》第2期,1932年11月15日。。
曾仲鳴主張用和平的方式統一中國,而要和平統一中國,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并從多個方面論述了實行民主政治對于和平統一中國的重要意義。他指出,首先,我們要和平統一中國,必須國中的各民族能夠統一,而要國中各民族統一,就只有實行民主政治。因為在民主政治的制度之下,各民族皆處于平等的地位,對于國家所盡的義務,各民族一樣的,所享的權利,各民族亦是一樣的。各民族既處于平等的地位,自然樂于促成國家的和平統一。其次,我們要和平統一中國,必須國中的政治能夠統一,而要國中的政治統一,亦只有實行民主政治。因為民主政治的制度,是最適宜于現今時代的需要,民主政治的目標,是可以滿足現今民眾的要求的。其次,我們要和平統一中國,必須國中的軍政能夠統一,而要國中的軍政統一,亦只有實行民主政治。因為實行民主政治,則在軍事上可以打破以人治軍和劃分防區的制度。武力既不寄托于個人,則統率武力的個人,則不僅不敢借武力作惡,亦不能借武力以作惡,軍隊既無劃分防區的制度,則軍餉取之于國家,由國家規定預算,按期發給,軍人便不至于視軍隊如私產,占防區為地盤。再其次,我們要和平統一中國,必須國中的財政能夠統一,而要國中的財政統一,亦只有實行民主政治。因為實行民主政治,則要求財政永遠公開,人民有監督執政者出納財政之權,執政者對于財政亦不至有營私行賄之弊,國家財政的收支,從人民的負擔而來,為人民的利益而用,人民自樂于繳納,財政自易于統一。歐美的共和國家,莫不守此制度,所以國家終能和平統一*曾仲鳴:《和平統一與民主政治》,《中央導報》第8期,1931年。。
民族復興的基礎或前提條件是國家的統一,而要實現國家的統一,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否則,即使國家一時統一了,也不會持久,也終會分裂。這便是胡適、王造時等人主張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也是民主政治對于民族復興的第二個重大意義。
三
民主政治對于民族復興的第三個重大意義是:民主政治是創建近代民族國家的基本要素之一,而近代民族國家的創建正是民族復興的題中應有之義,甚至可以說是民族復興的最終目的。李立俠在《民族復興與抗戰建國》一文中就明確指出:“民族和國家的關系,最初是由國家形成民族,而在近代社會中,都是由民族形成國家。近代英美德法之建國,都是如此。抵御外侮與反抗侵略者的壓迫,只是民族復興階段中必經的過程,也可以說只是達到民族復興目的之必要手段,而真正復興民族的目的,還是建立一個獨立生存的民族國家。”*李立俠:《民族復興與抗戰建國》,《青年向導周刊》第25期,1938年。
中華民族的復興,不是回到封建社會的國家形態,而是要采取近代民族國家的國家形態,這可以說是近代以來,尤其是抗戰時期中國知識界的主流觀點。眾所周知,中國開始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起始于20世紀初的辛亥革命。當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主張“排滿”和建立單一的共和制的漢民族國家,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則主張“合滿”和建立包括滿族在內的立憲制的多民族國家,雙方為此而展開過激烈的論戰和斗爭,結果是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成了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基本共識。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的成立,是中國近代民族國家初步建立的重要標志*鄭大華:《辛亥革命與中國近代民族國家的初步建立》,《教學與研究》2011年第10期。。但不久,袁世凱則篡奪了革命果實,中華民國所確立的近代民主制度成了一塊有名無實的空頭招牌,廣大人民并沒有像《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所規定的那樣實現人人平等,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的現象依然存在,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壓迫和掠奪依然存在。近代的民族國家并沒有在中國真正地建立起來。
辛亥革命失敗后,中國人民繼續為建立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而奮斗。孫中山在吸取辛亥革命以及后來的護國戰爭、護法運動相繼失敗教訓的基礎上,并借鑒美國的建國經驗,于1920年前后提出了建立“大中華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的主張,用他的話說,就是“拿漢族來做個中心,使之(指滿、蒙、回、藏等其他民族——引者)同化于我,并且為其他民族加入我們組織建國底機會。仿美利堅民族底規模,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底民族國家。”*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74頁。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則在1922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了“統一中國本部(包括東三省)為真正共和國”;“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的建國方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共中央統戰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頁。。1924年國共實現第一次合作,標志國共實現合作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提出的建國方案是:“于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后,當組織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中華民國。”在中華民國內,“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8、120頁。1928年國民黨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建立起南京國民政府后,拋棄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提出的建國方案,沒有去完成孫中山未竟的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事業,中國仍然是一個前近代的傳統國家。陳獨秀就曾指出:“中國的辛亥革命也是企圖步武歐美,建立一個近代國家。雖然成立了民國,產生了憲法與國會,民族工業也開始萌芽,然以國外及國內巨大的阻力,所謂民主革命任務,并未真實的完成。因此乃有1925—1927年的第二次革命和此次抗日戰爭。”*陳獨秀:《抗戰與建國》,《政論旬刊》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七·七”事變后,為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拯救民族于危亡之中,國共捐棄前嫌,實現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綱領的“總則”規定:“(一)確定三民主義暨總理遺教為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二)全國抗戰力量應在本黨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集中全力,奮勵前進。”在“總綱”之下,分別就“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眾運動”和“教育”各項提出了“綱領”,以“使全國力量得以集中團結,而實現總動員之效能”*《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485頁。。《抗戰建國綱領》第一次將抗戰的意義提升到了建國的高度,即抗戰的終極目的,不僅僅是要取得勝利,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而且還要通過抗戰,來實現國家的重建和民族復興。
《抗戰建國綱領》公布后,知識界圍繞抗戰建國的有關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當時人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抗戰的目的是要“建國”或“興國”,即將中國從一個前近代的傳統國家建設成為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羅寶冊在文中就寫道:無可諱言的,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不是一個現代的國家,但是,我們卻不能亦不敢因為中國不是一個現代的國家,就誤認中國不是一個國家。中國不但是一個國家,而且是一具有內容、有潛力、世界上壽命最長而且軀體最大的大國,如果我們避免稱他是一個“世界”、一個“東方世界”的話。同樣是無可諱言的,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古老的大國,因為感受到歷史的和哲學的要求,已由不安于他自己的古老,而趨向蛻變之途,要從中古式的古生活中過渡到現代。“今天,東亞大陸上的彌天烽火和震動的殺聲,正是象征著大地慈母已屆臨產前夜之巨烈陣痛的大時代,一個偉大的中華新國即將向世界宣告誕生。”*羅寶冊:《抗戰建國之歷史哲學與歷史使命》,《新認識月刊》第2卷第1期,1940年。李立俠也指出:從各國民族復興史來看,沒有一個民族的復興不是由抗戰得來的,比如,德意志民族是經過30年的奮斗,在趕走了拿破侖的壓迫之后而實現復興的,并且從中世紀的封建束縛之下,把德意志帝國解放出來,建設一個新的德意志國家。目前我們抗戰的目的,固然是在于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以救國家民族于垂亡,但是我們另外一個更大的目的,和德意志民族復興過程中一樣,也是要建立一個新的民族國家。“抵御外侮與反抗侵略者的壓迫,只是復興階段中必經的過程,也可以說只是達到民族復興目的之必要手段,而真正復興民族的目的,還是建立一個獨立生存的民族國家。”*李立俠:《民族復興與抗戰建國》,《青年向導周刊》第25期,1938年。陶希圣認為,抗戰建國有“消極”和“積極”兩重意義,“在消極方面,我們的抗戰是為了維持民族國家的生存,日本侵略我們,使我們民族國家的領土和主權不能保持完整,于是我們起而抗戰;在積極方面,我們的抗戰是為了建設現代民族國家。”*陶希圣:《抗戰與建國》,《政論旬刊》第1卷第16期,1938年7月5日。馮友蘭也再三強調,抗戰的最終目的,就是使中國成為一個“近代式底國家”。否則,“所謂中國,無論它是如何底地大物博,將來會只成為一個地理上底名詞;所謂中國人,無論他是如何底聰明優秀,將來會只成為一個人種上底名詞;所謂中國文化,無論它是如何底光耀燦爛,將來會只成為歷史博物館中底古墓。所以,中國非求成為一個近代式底國家不可。”*馮友蘭:《抗戰的目的與建國的方針》,《當代評論》第2卷第3期,1942年。
那么,怎樣才能“建國”或“興國”,即將中國從一個前近代的傳統國家建設成為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呢?這是抗戰時期知識界討論的主要問題。李拾豪指出,我們“要建設一個現代國家”,必須要“有幾個基本的條件”,這就是:一、對外求得獨立;二、建立一個憲政制度;三、建設重工業;四、農民解放。而在這四個“基本的條件”之中,“對外求獨立,是一個建設現代國家的主要條件”,“民主的憲政制度的確立,又是建設現代國家的各種條件中的中心問題。”因為,在對外未求得獨立以前,(一)國內的政治是不會走上軌道的,在帝國主義者與國內軍閥官僚、以至于豪紳地主相結托的局面下,不但內亂不會停止,憲政不能建立,就如民國初元的召集議會,實行民治,亦不過是掛了一張民治的招牌,究其內容,還是一個貪污的官僚政治而已。(二)政治不上軌道,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沒有停止,農民生活沒有改善,不但重工業無法建設,就是萌芽的輕工業也不能維持。(三)在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及封建剝削的兩重壓迫之下,要挽救農村經濟的衰落是不可能的。農村的崩潰,農民生活的極度貧乏化,反映出農民要救解放的迫切。就此而言,“對外求獨立,是一個建設現代國家的主要條件。”而要“對外求得獨立”,在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爭中,除了軍事上的動員外,更需要的是一個良好的政治制度——民主的憲政制度的確立*李拾豪:《抗戰建國與確立民主的憲政制度》,《抗戰十日》第2期,1938年。。陳獨秀回顧了“此前五六百年整個民主革命時代”,西方各國從一個前近代的傳統國家變成為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時所完成的“主要的民主任務”,這就是“民族的國家獨立與統一;立憲政治之確立;民族工業之發展;農民解放。”他并強調指出:“在這一時代的各民族,必須完成這些民主任務,才能夠摧毀舊的封建經濟與政治,開展新的較高的生產力和新的政治制度,以成為所謂近代國家,即多多少少民主制度的國家。”他還分析了個中的原因:“為什么要國家獨立與統一?因為非脫離國外非民主的壓迫和國內的分裂,一切經濟政治都不能自由發展。為什么要確立憲法政治?因為非如此不能確立政府的權限,保障人民的權利,使全國人民的智力和道德能夠普遍的發展,以增加整個國家的力量。為什么要發展工業?因為非如此不能增高國家物質的力量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與文化,以減殺整個民族的落后性。為什么要解放農民?因為非如此不能根本摧毀封建的社會勢力,繁榮本國工業的國內市場。”既然西方各國是在完成以上這四個“主要的民主任務”后,才從一個前近代的傳統國家成為了一個近代的民主國家,那么,中國要想成為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也就必須完成這四個主要的民主任務,“這便是我們建國的整個概念”*陳獨秀:《抗戰與建國》,《政論旬刊》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民族建國,要建立的不僅是一個民族獨立的國家,更是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這可以說是抗戰時期知識界的主流要求。胡秋原在《中國革命根本問題》一文中就指出:“中國革命之實際目的,即在求中國之現代化,……使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一個工業國家,由一個官僚政治國家變為一個民主政治國家。”*胡秋原:《中國革命根本問題》,《中華心——胡秋原政治·文藝·哲學文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4頁。馬寅初撰文強調說:“現在的世界已成了個民主世界,無論任何國家,在戰爭結束之后必須走向民主的一條路,否則無以保其生存與獨立。”*馬寅初:《中國工業化與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民主與科學》第1卷第1號,1944年12月22日。在張瀾看來,民主政治,主權在民,人人有獨立的人格,人人有共守的憲章,所受之教育,所得之享受,皆期趨于平等,“因為有次列各項優點,所以當前和未來的世界政治,都要以民主政治為最高原則。”*張瀾:《中國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張瀾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頁。陳啟天強調:“所謂建國,即是要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已”,而政治民主化正是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指標之一*陳啟天:《中國需要思想家》,《國光》第9期,1938年6月。。沈鈞儒撰文指出:“加強民主之要求,實已成為今日世界廣泛之潮流”,蘇聯在蘇德戰爭爆發以后實行了全民共享的民主政治,英、美在戰時也采取了一系列加強民主、改善民生的措施,中國不能自外于世界,只有實施民主政治“才能使民族走上復興的大路”*《沈鈞儒文集》,第463、437頁。。
為什么只有實施民主政治“才能使民族走上復興的大路”呢?因為民主政治是一種先進的政治制度,代表了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方向。伍藻池指出,19世紀下半葉以來,“民主政治的權威,與日俱增,大有所向披靡之勢”,其間雖經受了不少曲折和挫敗,“然終不能止它向前邁進的洪流。”*伍藻池:《民主政治的危機與其將來》,《再生》第3卷第9期,1935年11月15日。鄒文海詳細論述了民主國家的四個優點:第一,“民主國一定是最能保障人民利益,而受人民愛護的”。第二,民主國家像個“大學校”,為國民提供了學習和實踐政治知識的條件。第三,“民主政治應當是最合正義的政治”,它以一種中立的立場,賦予各社會團體、階級以平等的機會。第四,民主國家的“政府已變成服務的機關”,人民有權利監督政府的行動*鄒文海:《選舉與代表制度》,《再生》第2卷第5期,1934年2月1日。。曾琦具體分析了民主政治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歷史意義,即“以其由人治而趨法治,由專制而趨自由,由黑暗而趨光明,由秘密而趨公開,由少數決而趨多數決,由國家私有而進于國家公有,由決勝疆場而改為決勝議場,實為人類比較合理之政治形態。”*曾琦:《祝三十而立之中華民國》,《曾琦先生文集》上冊,第235、236頁。潘光旦指出,“英文中所稱的‘德漠克拉西’,合而言之,是民主;分而言之,是民有、民享、民治”,其基本內涵包括自由、平等、人民參與政權以及法治等價值理念*潘光旦:《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01、33—38頁。。作為教育家,潘光旦還強調了民主與教育的關系,認為“沒有民主的政治與社會環境,自由的教育是做不到的,……從教育的立場上看,唯有一個真正民主的政治環境,始能孕育真正民主自由或通達的教育,才可以造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二者實在是互為因果的。”*潘光旦:《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01、33—38頁。周谷城在《復興民族之民主政治論》一文中,以“民族活力”為視角,比較了專制政治與民主政治的不同,從而充分肯定了民主政治的進步性。他指出,專制政治的成功,實為民族活力之失敗,“驅人民于政治生活范圍之外,為逸民,為流寇;或納人民于政治生活范圍之內,為奴隸,為愚夫,皆非所以發揮民族之活力者。”民族活力之發揮,雖然有賴于生產方法的改進和教育效用的完成,但政治的作用不僅更為“直截”和“深宏”,而且就是生計和教育,也都直接或間接的依據政治為轉移。政治能發揮民族活力的,是民主政治。“故就民族活力而言,吾人于此可得一分野:一方面為窒息民族活力之專制政治,另一方面為發揮民族活力之民主政治。兩者之間并無徘徊回旋之余地。故當今日民族復興之會,有識之士,以及當局諸公,皆力言民主政治之重要者,盡為此也。”什么是民族活力呢?民族活力就是全民族中各個人之活力的集合體,各個人的活力如果能夠得到充分發揮,那么民族活力也就自然的強盛。“專制政治無他長,人民之有活力者,則驅逐于政治生活范圍之外,留在政治生活范圍之內者,則強其活力萎縮,至等于零。活力萎縮等于零者,奴隸是也。民主政治則不然,首要之圖,在尊重國民之人格。……國民而得被人重視為有人格之完人,則其為民族國家效力也,若為自己效力然,能自覺而負責。集自覺而負責之個人,以成民族國家之全體,則其生存之力之大,必遠較奴隸似之國民全體為有加。”*周谷城:《復興民族之民主政治論》,《憲政月刊》第2號,1944年。
以上是抗戰時期知識界關于“民主政治對于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的認識和討論。這些認識和討論在今天讀來仍然引人深思,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對于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有其借鑒的歷史意義。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課題“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復興歷程研究”(13@ZH018)、2013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重大招標課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方英
中圖分類號:K2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05X(2016)04-0029-09
作者簡介:鄭大華(1956-),男,湖南永順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湖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to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Centered on the Discussion of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he Intelligentsi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ZHENG Da-hua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Abstract:As the rise of thought of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intelligentsia launched a heated discussion on whether or not the Chinese nation could rejuvenate and how to rejuvenate,one of the major issues wa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to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One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mainstream of intelligentsia is that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we must first defeat the aggression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win the libera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untry.In order to defeat it,we must realize the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so that the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can enjoy various democratic rights and all parties can unite sincerely.It is impossible for a divided country to rejuvenate and only by democratic politics,it is possible for a country to achieve long-term national unification.At the same time,the democratic politics is also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nation-state,and the political requirement and target of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democratic politics;the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the intelligent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