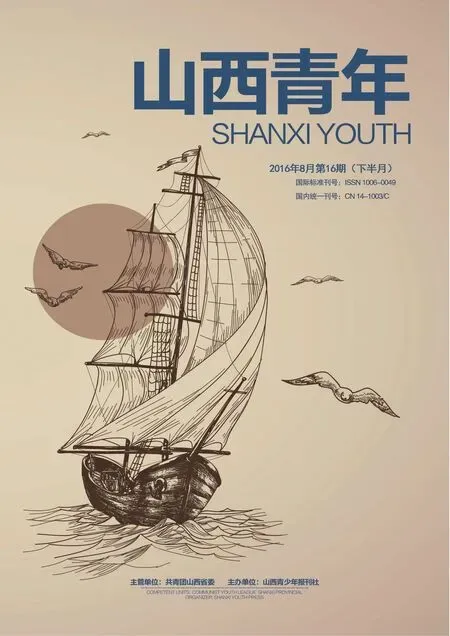阮籍五言《詠懷詩》對《詩經》的繼承與發展
楊琳琳*
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
阮籍五言《詠懷詩》對《詩經》的繼承與發展
楊琳琳*
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河南新鄉453007
阮籍的五言《詠懷詩》在文學史上占據重要的地位和意義,其淵源辨析歷來眾說紛紜,自鐘嶸提出阮籍詩源出于《小雅》以來,學界質疑的聲音不斷,發展到現在有“小雅”說、“離騷”說、“古詩十九首”說、“莊子”說等,不可否認的是《詠懷》飽滿的浪漫主義情懷跟《莊》《騷》一脈相承,但《詠懷詩》中大量現實主義的描寫卻是對《詩經》的繼承與發展。本文就從諷刺精神、超現實的審美取向兩個方面來闡述阮籍五言《詠懷詩》是如何繼承和發展《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
《詠懷詩》;《詩經》;諷刺;超現實
南朝梁鐘嶸《詩品上》“晉步兵阮籍詩”條曰:“其源出于《小雅》,無雕蟲之巧,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于《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指出阮籍《詠懷詩》的淵源在于《小雅》。清人王夫之對于《詠懷詩》也有自己的觀點,他說:“步兵《詠懷》,自是曠代絕作,遠紹《國風》,近出入于《古詩十九首》,而以高朗之懷,脫穎之氣,取神似于離合之間。大要如晴云出岫,舒卷無定質。”認為阮籍《詠懷詩》的遠祖是《國風》,近祖是《古詩十九首》。但不管是《小雅》還是《國風》,《詠懷詩》與《詩經》的密切關系似乎是毋庸置疑了。近人方東樹也說,阮公《詠懷》“宏放高邁,則與《騷》、《雅》皆近之”并認為“不深解《離騷》,不足以讀阮詩。”方氏在這里提出了《離騷》對《詠懷詩》的闡釋理解影響很大,但也充分肯定了《詩經》和《詠懷詩》的淵源關系。
阮籍所創作的《詠懷詩》是我國文學歷史發展長河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詩歌以獨特的美學風貌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和意義。在這八十二首五言詩中,阮籍將深邃的玄學哲思與詩歌中的情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讓詩歌不僅具有深沉的內涵,同時呈現出無比廣闊的境界。如此瑰麗宏大、影響深遠的巨作從繼承古老的藝術傳統來看,《詠懷詩》絕不僅僅詩從一家,而是博采眾長,融合眾美,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味。就淵源而講,鐘嶸認為阮詩出于小雅,似乎也是學術界廣泛認可的說法,除了寫作背景的相似,《詠懷》對《詩經》的“諷刺”精神,比興的表現手法,意象的大規模沿用都是對《詩經》的絕好繼承,但從美學特征來看,《詠懷》融合《莊》、《騷》特點更為明顯,當然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本文旨在說明《詠懷》是如何繼承和發展《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的。
一、諷刺精神
作為中國詩歌的源頭《詩經》突出的特點是它們的諷刺精神。阮籍繼承了《詩經》的諷刺精神,寫了不少政治諷刺詩,他的《詠懷詩》內容除了少數“憂生之嗟”和懷念親友者之外,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諷刺力作:
如《詠懷詩》第十首: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游子,俯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僶俯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云游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
這首詩是阮氏深刻地指出了魏帝荒淫是導致魏室衰亡的原因。
再如第五十三首:
自然有成理,生死道無常。智巧萬端出,大要不易方。如何夸毗子,作色懷驕腸。乘軒驅良馬,深榭設閑房。被服纖羅衣,憑幾向膏粱。不見日夕華,翩翩飛路傍。
這首詩是譏諷司馬氏集團的作品。五到十句以反詰語氣,通過對司馬氏集團的吃喝玩樂所謂富貴生活的描寫,揭露他們的驕奢淫逸。
這樣的諷刺詩在《詠懷》中頗為常見。綜合來說阮籍最愛批評的是兩類人:一類是虛偽而又拘謹的“禮法之士”比如《詠懷》其六十“儒者通六藝”,其六十七“洪升資制度”;另一類人則是浮華交結,馳逐名利,生活奢侈,終日應酬結交的貴族子弟,阮籍稱之為“繁華子”“夸毗子”,這兩類人物是當時上層社會的主要構成部分。他們出于同一階層之中,表現的方式盡管不同,但目的都是追名逐利。阮籍對其的基本態度與其說是諷刺,不如說是悲憫。
《詩經》大部分諷刺詩都是貴族士大夫的作品,是為維護貴族統治而作的,有很多詩篇作者直抒胸臆指出創作的目的是為了勸諫,正因為此詩三百表現出一種溫柔敦厚的風格。魏晉之際的阮籍和他的父親都是魏臣,深得曹氏父子的賞識。所以他的諷刺詩是對曹魏政權的哀落表示惋惜,同時對司馬氏政權的篡立進行指斥和揭露。他的諷刺詩是站在一個將亡的政治集團的立場上反對另一個將代之而興的政治集團,它所反映的矛盾是封建政權內部兩個政治集團的矛盾,阮詩的諷刺與揭露是一針見血似的,深刻而不講情面,并沒有繼承《詩經》“溫柔敦厚”的精神。
二、超現實的審美傾向
阮籍《詠懷詩》,從詩歌形象中所體現的審美取向來看,具有強烈的否定現實美并追求超現實美的傾向,這又是對《詩經》現實主義精神的超越。但比《詩經》更進一步的是,阮籍的《詠懷》也從《詩經》中多次取材,但是作者并不熱衷對現實事物的表態,對一般的人類感情相當淡漠。青春、歌舞、美貌、愛情,這些在任何時代、任何形式的文學作品中向來是創作者們贊美、渴望、視如珍寶的形象,在阮籍這里則成了被懷疑、被諷刺、被否定的對象。可能與阮籍對莊子的繼承有關,“大象無形”,阮籍在詩歌中對呈現于感官上的外在事物的美的形式,持一種冷靜思辨又殘酷的態度,他往往從美中看出丑,從生中看出死:
視彼桃李花,誰能久熒熒。——其十八
幽蘭不可佩,朱草為誰榮。——其四十五
清露為凝霜,華草成蒿萊。——其五十
《詩經》很多時候在表現事物的形象形式之美,比如《采薇》在興的時候表現出薇這種植物的萌芽、生長,充滿美好向上的感覺,《蒹葭》中更是賦比興連用,重章疊嶂,音律諧婉,蒹葭的蒼茫與伊人的朦朧融為一體。但阮籍對素材的處理方式和態度方面則有很大不同,究其根源在于作者那種對現實美的否定懷疑信念。當然這種審美觀念究其緣由還是阮籍因強烈的不滿現實的情緒所決定的,是他在現世中跌跌撞撞之后形成自己的哲學體系,他用這種武器闡釋外在的世界。
[1]陳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邱鎮京.阮籍詠懷詩研究[M].臺北:臺灣文津出版社,1980.
楊琳琳(1991-),女,漢族,河南南陽人,河南師范大學,2014級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
I207.22A
1006-0049-(2016)16-01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