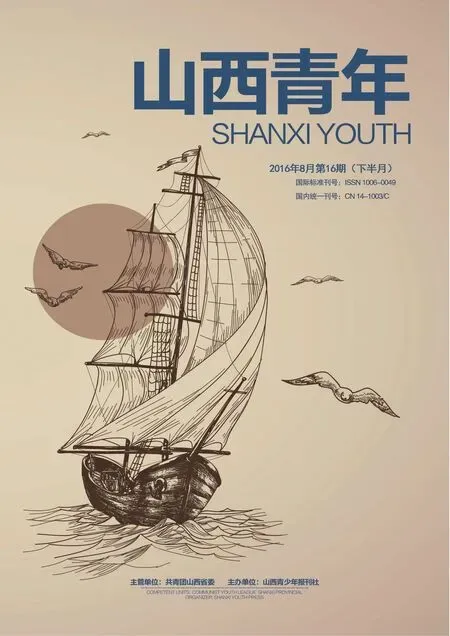《一個女人》評介
豆萌萌*
天津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院,天津 300204
?
《一個女人》評介
豆萌萌*
天津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院,天津300204
《一個女人》;評介
一、引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法國文壇呈現(xiàn)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其中的傳記文學曾一度輝煌,還出現(xiàn)了親子關(guān)系小說(récit de filiation)這種新形式——通過講述父母的故事,搭建起一張親子關(guān)系網(wǎng),間接曲折地言說自我。《一個女人》(Une Femme)便是其中一部典型的自傳作品,題目中的“一個女人”即作者的母親。此書形式上的主人公是“母親”,但實質(zhì)上更多是對自我的言說。該書由Gallimard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法國女教師兼作家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埃爾諾一生創(chuàng)作了多部優(yōu)秀的自傳題材作品,豐富了法國當代傳記文學。鑒于中國讀者對其作品了解不多,而其自傳的新穎性和獨特性對我國的自傳文學頗有啟發(fā),本文擬對該書作簡要介紹和評述。
二、概述
《一個女人》這本書以“我”為敘述角度,講述了“我”的母親平凡的一生。
本文擬將全文分為三個章節(jié)。
第一章主要講母親的去世和“我”的悲痛心情。從行文的組織結(jié)構(gòu)上來講,這一部分是整本書敘述方案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它引起母親去世后各個場景的上場,同時也奠定了此書的基調(diào):淡淡憂愁中亦有冷靜克制。
由第二章開始,作者由始至末地講述母親的一生。敘述時間戛然轉(zhuǎn)到了20世紀初,母親出生在一個貧民家庭。她的父親酗酒,母親嚴厲。她早早就退了學,去工廠里打工賺錢維持生計。故事一直向前發(fā)展,1928年母親嫁給父親,1940年作者出生。為了有更好的生活,兩人辛勤奮斗,終于從工人變成小商人,擁有了一間小雜貨咖啡館。“我”的母親希望“我”過的比她好,實際也如此,“我”順利完成自己的學業(yè),并通過婚姻進入了中產(chǎn)階級家庭。
第三章的敘述速度減緩,作者用與前一章同樣的篇幅,卻只講述了1967到1987年之間20年的故事。說明母親生命中的最后20年在作者心中占據(jù)著很重要的位置。這20年是父親去世后,母親獨自與生活抗爭的20年。她自己堅持開了幾年店,后搬去作者的“資產(chǎn)階級的大房子里”與其同住,慢慢適應另一個階層的人的生活模式,然后又漸漸厭棄這種狀態(tài),獨自一人回老家的房子里生活。最后不幸罹患阿爾茨海默病。于1986年去世。痛失母親是人生中的一場劫難,作者在書末深情告白:“她對人付出的比得到的多,把她寫出來是否也是一種補償呢?”①
三、簡評
(一)自我書寫
在傳統(tǒng)西方文學中,“我”不是文學作品中的主角。作家們對自我的言說受到多方的阻礙:在亞里士多德時代,人們崇拜開創(chuàng)式的英雄人物,在任何戲劇或者史詩中都找不到個人的影子;同時也有道德和宗教因素的制約,在人們的宗教觀念里,自我是可憎的,上帝是神圣的,大肆宣揚自我是褻瀆圣人的表現(xiàn);另外,從美學標準上來講,人們認為自傳并不夠格被納入文學藝術(shù)作品,因為想象力是批評家所看重的重要文學因素。書寫自我是如此容易,不需要任何的想象,隨便一個人都能用筆記錄下自己的生活。小說則不同,小說家是去創(chuàng)造角色,創(chuàng)造事件,必須要靠天分和才華,以及恰到好處的想象。所以在西方文學傳統(tǒng)上,自我書寫是一種末流的體裁,很少有文學家選擇這一領(lǐng)域。
時到如今,自我書寫的文學體裁已被文學批評界和讀者慢慢接受。自我書寫涉及的種類也越來越多樣化,它包括自傳、回憶錄、日記、傳記、及自撰等多種形式。自傳是其中一種特殊形式。談及自傳(autobiographie)歷來眾說紛紜,長期以來批評界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針對這一文學體裁的思考研究也不多。批評家們只看到了它的資料價值而忽視其思想價值和藝術(shù)價值,讀者所關(guān)心的自傳的真實性問題得不到應有的解答。因此,1969年,菲利普·勒熱內(nèi)將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在自傳上,開始了在自傳研究這片荒蕪原野上的開墾工作。經(jīng)過兩年的潛心思考和研究,他將研究成果寫成《法國的自傳》一書。他在書中給自傳下了一個定義:“當某人主要強調(diào)他的個人生活,尤其是他的個性的歷史時,我們把此人用散文體寫成的回顧性敘事稱為自傳。”②誠然,這個定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確立了自傳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和研究對象獨立存在的地位,啟發(fā)了后來的自傳研究。
批評界的自傳研究不斷升溫,并一直持續(xù)至今。由于50年代以來一大批著名作家如薩洛特、萊里斯、薩特、勒杜克、佩萊克、巴特等對自傳的偏愛,自傳在創(chuàng)作上也走向繁榮,迎來了它的高潮時期。三十多年之后,法國女作家安妮·埃爾諾的《位置》出版,并于1984年獲得雷諾多文學獎,其女性自傳體創(chuàng)作特點,個人與社會的雙重維度視角,以及平實簡潔的語言獨樹一幟,給法國自傳領(lǐng)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三年之后,安妮·埃爾諾又發(fā)表了《一個女人》。
同時,《一個女人》和《位置》也證明了一種更新的文學體裁的出現(xiàn):親子關(guān)系小說。這類自傳的敘述特點是通過講述父母或者子女的故事而間接地講述自己。作者寫作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搭建與親人的關(guān)系網(wǎng),自然地講述其自身的成長經(jīng)歷和性格特點。以本書為例,初讀之下讀者會發(fā)現(xiàn)小說講述的是安妮·埃爾諾的母親,通過努力和奮斗,改變了社會地位的故事。但是深入分析,會發(fā)現(xiàn),對母親的形象構(gòu)建不是最終目的,作者的寫作目的更為宏遠,發(fā)生在她母親身上的事件,是激發(fā)她思考社會的導火索。這篇作品的主題,依然是一部自傳,而且是社會自傳。
(二)安妮·埃爾諾的自傳體寫作投射的社會學意義
作為讀者,乍讀《一個女人》這一題目,依然不能從中尋到確切的自傳作品的蹤跡。那么標題——《一個女人》,到底蘊含著怎樣的意義呢?這個題目簡明扼要:它只由一個不定冠詞和一個名詞組成。然而,在它的簡潔和客觀背后還隱藏著復雜的成分。名詞“女人”無關(guān)緊要,它的修飾成分“一個”,是很值得分析的。“數(shù)詞+量詞”的這種成分可以組成一個名詞意群,可以指一類事物的集合,如:“一只狗永遠是一只狗”,也可以指某一特殊事物,傳說故事中經(jīng)常這樣開頭:“從前有一個人”。區(qū)別很明顯,前一個例子中的“一只狗”具有普遍意義,指的是任意一只狗,而后面一個例子中,“一個人”則指的是一個特定的人,并不是整個人類。
那么在我們這本書的標題《一個女人》中,問題的關(guān)鍵就在于弄清楚“一個”所代表的意義是普遍性的還是特殊性的。這兩者之間的模糊性就是安妮·埃爾諾對標題選擇的成功所在。如果我們傾向于它的普遍性,那么這個女人就充當著一個典型的形象,而如果說它是特殊性的,這個女人就只指向某一個體。躊躇在這兩種解釋中間,書中的一個女人是安妮·埃爾諾的母親,但她同時又代表著在一定社會階層中的典型形象。因此在這對母女關(guān)系中,這個女人不僅僅是一位母親,她也是她所處的那個社會階層的成員。安妮·埃爾諾作品中的社會學意義就是對這個問題最好的解答。她希望其作品講述的是不僅僅是自己或自己家庭的故事,而是一整個社會,一整個時代的縮影。關(guān)于社會問題的思考,尤其是統(tǒng)治階級和被統(tǒng)治階級方面的問題,是文學作品中頻繁出現(xiàn)的主題。
除了《一個女人》這部作品,安妮·埃爾諾創(chuàng)作的大量文學作品,展示了那個時代平民階層的生活,以第一人稱形式記錄了自己從社會底層到中產(chǎn)階級的社會遷徙過程。安妮·埃爾諾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通過婚姻進入中產(chǎn)階層,也因此成為了她自己口中所謂的“階級變節(jié)者”。自身的階級演變經(jīng)歷給她帶來了獨特的視角,也孕育了她獨具特色的社會自傳的構(gòu)想。
同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社會區(qū)隔理論激發(fā)了她對社會結(jié)構(gòu)和運行機制的思考。通過對兩個階層的對比,“勾勒出位于不同社會空間的的個體所表現(xiàn)出的不同性習,客觀地展示出不同階層之間隱形的區(qū)隔,使‘區(qū)隔’這一抽象的社會學概念具體到社會生活實踐的方方面面。埃爾諾以個人經(jīng)歷為基礎(chǔ),從群體視角反映了社會變遷,將個人回憶融于社會大背景中,使個人的傳記成為了一部社會自傳”③。在她的作品中,常常可以見到關(guān)于兩個階級的親人各方面的對比。兩個家庭同時也代表著兩個階層,處于不同階層中的人在生活背景,受教育程度和處世態(tài)度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是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一點一滴積累出來的,是這個社會運行機制下的結(jié)果。作者在書的末尾寫道:“我這里寫的……可能是介于文學、社會學、和歷史之間的什么東西吧。”①她慣以歷史的和社會的視角去看問題,力圖以個人反映社會,以小歷史對照大歷史;以個體回憶喚起集體回憶。
(三)安妮·埃爾諾寫作的語言特色
安妮·埃爾諾慣以平實的語言風格著稱,她拒絕在書寫中加入過多的個人情感,通過書寫,達到客觀化的效果。因此我們也可以理解她的語言為何如此平淡,甚至可以說蒼白了。沒有任何的修飾,只是平淡如水的敘述。甚至像機器人的編碼語言,但是這樣的語言在她筆下依然是有溫度的。她認為只有最簡單的語言才能表達最真實的東西,才更接近事物的本質(zhì)。而用中性的語言風格,有利于使自身從事件中脫離,去除特殊性,更易引起讀者的共鳴。
雖然埃爾諾在作品中對母親傾注了更多的感情,但是母親的一生是平凡的,因此她也無法用華麗的語言去講述一個平凡的人的一生,只有最貼近實際的語言,最平淡自然單調(diào)的筆調(diào)才能表達最真實的生活。客觀的語言使她既能把自己的情感拉近也能將其推遠,也能很好地將個人故事定位于那個時代的歷史大事件中,《一個女人》以其有力、快速,同時混合著一種強烈思念的敘事風格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
我們偶爾也會見到作者動情的宣泄,比如:
“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里,我無論身在何處都總是心理很難受,常常以淚洗面。當我從沉沉的夢中醒來時,什么都記不清了,只記得母親真的去世了,她真的離我而去了。每天除了做飯,洗衣服等這樣必須要做的事情之外,我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有時甚至干著這些活計,腦子就亂了起來。擇完菜后得要想好一陣子才知道該去洗菜了。讀書是不可能的……到外面去更讓我感到難受。我開著車,突然一陣傷感涌上心頭‘她永遠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①
然而作者想表達的也不僅僅局限于個人的悲傷和不舍:
“我的母親出生在下層社會,她一直想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我按照母親的意愿進入了這個掌握語言與思想的世界里,我必須將她的故事寫出來,為的是讓我在這個掌握語言與思想的環(huán)境里不覺得太孤獨和虛假。”①“掌握語言與思想的世界”當然就是文學世界,因為母親去世,“我失去了我與我出生的那個世界相聯(lián)系的最后一根紐帶”,所以才孤獨,我孤獨地生活在這個本不屬于我的世界,唯有靠書寫來找回母親,來自我拯救。
“我再也聽不到她的聲音了。正是她和她的語言,她的手,她的動作,她的一顰一笑,把現(xiàn)在的我和童年的我聯(lián)系起來。現(xiàn)在我失去了我與我出生的那個世界相聯(lián)系的最后一根紐帶”。①從最后一段話里不難讀出,作者是借助母親,把“現(xiàn)在的我和童年的我”聯(lián)系起來的,母親就像是一根紐帶,串起了“我”與世界。看到了母親,“我”便會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我”原本的位置在哪里。而“我”如今的社會位置得以轉(zhuǎn)變,又全都是因為母親和“我”整整兩代人的辛苦拼搏。可以說母親的一生都是在為“我”而活,試想世界上的其它母親,哪一位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因此,簡單的語言并不蒼白,而是有彈性的。作者省掉了繁復的修飾和美化,同時,也在文本間留下空間,使得讀者能夠進入,能身臨其中,如此,作者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她想要的,正是這樣一種大互動。簡單并非容易,簡單亦有大能量。
[注釋]
①《一個女人》[M].郭玉梅譯.
②菲利普·勒熱內(nèi).《自傳契約》[M].
③彭瑩瑩,王靜.《游走于個人與社會之間——解讀安妮·埃爾諾自傳的社會性》[J].
[1]Annie Ernaux,La Place,Gallimard,Paris,1983.
[2]Annie Ernaux,Une Femme,Gallimard,Paris,1988.
[3]埃爾諾.一個女人[M].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
[4]勒熱納.自傳契約[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5]彭瑩瑩.“我”是誰?——安妮·埃爾諾社會自傳中的無人稱敘事[J].法國研究,2015(2):60-65.
[6]彭瑩瑩,王靜.游走于個人與社會之間——解讀安妮·埃爾諾自傳的社會性[J].法國研究,2014(4):60-67.
豆萌萌(1991-),女,漢族,河北保定人,天津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院,法語語言文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在讀。
I207.42A
1006-0049-(2016)16-004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