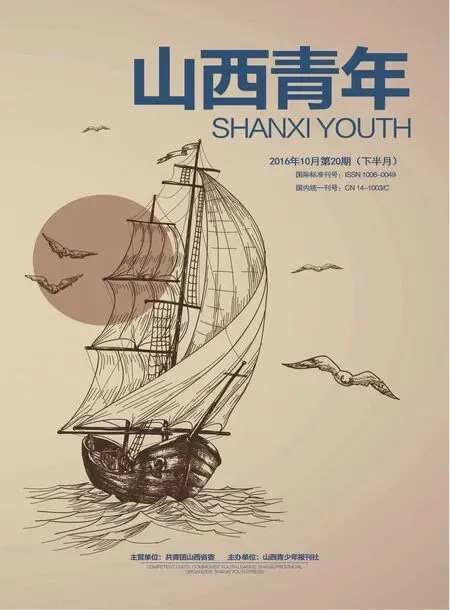傳統“規矩”與現實的碰撞
——從文化學角度分析電影《老炮兒》
弓藝霏
遼寧大學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
傳統“規矩”與現實的碰撞
——從文化學角度分析電影《老炮兒》
弓藝霏*
遼寧大學文學院,遼寧沈陽110036
電影《老炮兒》一上映,便引起許多影評家、各類學者的關注。對影片的評價褒貶不一,筆者認為“老炮兒”中這種另類“流氓文化”的存在恰恰是最貼近社會底層生活本質的。整部影片折射的是傳統的“規矩”與現實的碰撞,是老一輩人對文化的堅守,而這種堅守,看似悲壯,實則無力。
老炮兒;傳統“規矩”;文化堅守
北京人重視“理兒”。人們常說有理兒有面兒,北京人把有“理兒”放在前面,有了“理兒”,才會有“面兒”。老北京的“理兒”、“規矩”不是哪位皇帝御批的,也不是純粹民間發展起來的。從種種特征來說,老北京的“理兒”“規矩”源自周禮和孔孟儒學,伴隨著社會的演變,不斷地流傳和發展。正所謂“道家講究和諧,佛家講究包容,儒家講究規矩”。《老炮兒》正是一部“講理兒”的電影。
“老炮兒”一詞源于“炮局”,炮局是老北京的俚語,借指警局、派出所,而“老炮兒”就是那些因為犯事經常出入“炮局”的人,影片中的主人公“六爺”(馮小剛飾)就是昔日家喻戶曉的“老炮兒”六爺堅守的文化傳統正是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他要的是仁義,要的是禮貌,要的是長幼有序,要的是循規蹈矩。對不符合這樣要求的人,六爺一概看不順眼。看見小偷,他教育人家拿錢走人可以,證件給人家寄回去,要懂得盜亦有道;看見有人跳樓,圍觀的人起哄看熱鬧,只有他義憤填膺譴責他們的冷漠“都是些什么人那!”。他認為知法犯法不對,損人錢財不對,暴力執法不對,蓄意傷人不對……這些情節讓我們看到了恪守規矩和底線的“六爺”,看到了凡事論理、講道義的“六爺”,看到了心里始終有著一桿計算仁義的秤的六爺。
至于不顧長幼次序,打了他一個巴掌的青年,六爺更是完全不能容忍的,這一巴掌,挑戰的是他心中恒定的規矩,這比兩千元變成十萬塊更難以容忍。所以他在約完茬架后,特意回頭說:“三天后,你也在這兒!”。同樣,劇中反復出現一個老人的形象:他頭發花白,僅單單一坐就有凜然不可侵犯的氣質。路過的人往往會為他點支煙,以示敬意。“六爺”最在意這個細節。甚至在赴生死之約前,他還鄭重其事地將煙含在嘴里,點燃后再送到老爺子口中。以這類獨特的告別方式,他無聲地道出了自己的潛臺詞:無論江湖上的人物如何流轉更迭,但不能改變的是民間的“規矩”——其中之一,就是有所敬畏。這固然來自儒家倫理學,但也是他對抗主流的精神武器——在權力和金錢的邏輯之外,維系民間的秩序和道義。它設定了底線:即便你有權有錢,也不能蔑視人的尊嚴。
那六爺的死,真的就意味著傳統“規矩”的消逝了么?實則不然。劇終前,一群“老炮兒”神采奕奕的走出看守所,有說有笑。這是意味深長的隱喻,暗示民間的“理兒”仍然活著。痊愈后的曉波實現了“六爺”的遺愿,開了家名為“聚義廳”的酒吧,工作之余不停地教自己的鸚鵡喊“爸爸”,這顯然也暗示著傳統民間文化的某種延續。曉波身上兼具傳統民間文化與新時代價值觀。當情景再次重現:騎自行車的青年問路時,當了酒吧老板的曉波不再僵硬地恪守江湖教條,不再強求對方使用敬語,而是表現出更為寬容的態度,笑著回答路人的問題。顯然,在新時代的社會,“規矩”顯示出了更為開放的精神氣質。于是,老祖宗所強調的東西不但得以薪火相傳,更展示出自我超越的跡象。這也體現了文化所特有的特質:調整性,即“指適應性的保護功能,使文化本體面對強大意志文化不至于崩潰,甚至以形變、部分質變來形成本體的維系。”
在導演管虎的眼中,老炮兒是一種文化和精神,是一種原本人人都擁有卻被高速發展的社會環境不得不逼退的人性本真。所謂的“老炮兒”彰顯著這座城市曾經的規矩道理,像老北京城曾經雄壯時候存留的一口硬氣,這口氣是活的精神養分給予曾經的主人們驕傲的底氣,在老北京曾經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滋養了一干“頑主”,而隨著時光荏苒這批曾經的輕狂少年開始妥協,這口氣被往來穿梭的新興人潮沖擊潰散。六爺是這口氣的守護者,然而,他雖看不慣當下的“禮崩樂壞”,卻無能為力,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孤身固執所要扶起的“理”早已不適用于這個變化的時代。有人認為六爺最后親自寫舉報信的行為不合理,違反了他一直恪守的“規矩”,不按常理出牌,但。這難道不也正是傳統價值觀與現代法治社會碰撞所產生的火花么?即便要信奉“理兒”,也要講究法,這似乎也是六爺的一種默認的妥協。
“文明與野蠻,秩序與混亂,并行生長的混沌,難以調和的復雜。”這既是《老炮兒》這部電影里呈現出的情節,也是我們生活的今日中華大地的現實。管虎大膽揭露了當今社會官富階層和平民間的尖銳矛盾,并讓六爺作為群眾代表去反擊這種不公。但這畢竟是電影。現實中我們需要公平,卻還是應該寄托于社會整體向法治的轉向,而不能指望每個胡同口都站著一個維持秩序的六爺。
如果說《老炮兒》表現了時代的更迭,那么,它也展示了更迭中的連續性:“好的東西需要有傳承,盡管江湖終歸會變化,時代也會有交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不同,但有些精神是不應該改變的。”對于一種文化的堅守,不應該是腐朽的,而應該與時俱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不至于在我們老后,感覺一生所學、所用、所想,在時代巨變面前毫無存在價值。這也體現了現代性文化的特點,在現代化社會,文化的樞紐型特質開始解構,社會開始由人倫社會向多元化分立社會轉型。只憑“規矩”辦事的舊時代已經過去,法律、政治、經濟,都是當代社會的必需品,每個人都必須強迫自己順勢時代的發展和演變。
從個人角度來說,我希望這是一個警醒:形式上的墨守,只會顯示我們的老舊,時代背景下的社會公德價值觀的遵守,才是本質與核心。在法治尚未建立的情況下,傳統的價值觀仍有其存在的價值。傳統“規矩”與現實碰撞的結果是促使社會進行轉型,是幫助人們在更深刻地認識和了解當代文化的同時不忘記傳統文化,是加深文化與現實的融合。時代雖變,“規矩”常在。
[1]高楠.中國古代藝術的文化學闡釋.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
弓藝霏(1992-),女,遼寧沈陽人,遼寧大學文學院,研究生在讀。
J943
A
1006-0049-(2016)20-01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