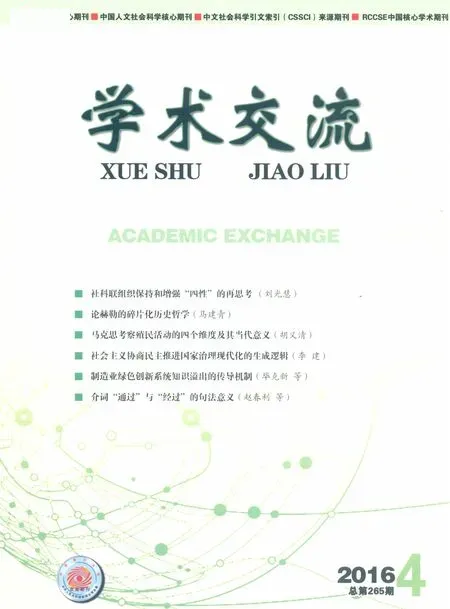選擇與權利界定的問題
——重新理解“科斯定理”
張洪新
(吉林大學 法學院,長春 130012)
?
法學研究
選擇與權利界定的問題
——重新理解“科斯定理”
張洪新
(吉林大學 法學院,長春 130012)
[摘要]科斯定理是關于權利界定的,然而定理中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被科斯繼承者所忽視。科斯定理能夠提出主要因為“損害具有相互性”這個新的分析角度,但相互性的本質是稀缺資源配置問題,將權利沖突等價于相互性并以此分析權利配置,只會消解權利的多重屬性。科斯為權利界定的難題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分析思路,但僅以財富最大化為準據太冷酷、更非充分。法律人要想正確理解科斯,必須重視“企業的性質”所提出的方法。
[關鍵詞]選擇;權利界定;相互性;財富最大化;制度
一個人一定要下很大的決心和勇氣才敢于寫一篇有關“科斯定理”的文章。[1]1通常來說,科斯定理,就它是“定理”而言,既擁有堅定的支持者,也有徹底的批評者。本文目的并不是判斷哪一方正確,也無意為科斯定理進行理論證明,或者經驗上的證偽,而是試圖確認問題是什么,特別是法學研究者(主要是法律經濟分析者)應用這一定理作為論辯前提來分析法學上一些問題時,所忽略或者所不思的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一般認為,科斯定理的標準含義是: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不管法律對權利如何配置,有效率的結果總是會通過市場交易主體的自由協商而出現。換句話說,如果交易成本不為零,那么資源是否得到有效率地運用,就取決于法律對產權的初始配置。其規范或者政策含義便是構建法律以便消除私人交易的障礙,減少因不能達成市場交易所帶來的損失。[2]即是說,法律權利界定和經濟效率經由交易成本而牽連在一起。
可見,權利界定對于經濟分析既可以非常重要也可以無足輕重,這重要性取決于交易成本是否為零。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主的科斯對傳統經濟學的獨特貢獻在于,他使經濟活動中無處不在的交易成本進入經濟學者的分析視野,開創了交易成本新的分析范式。但科斯定理之于法學的聯結,為什么是權利界定,權利界定又在哪種意義上與科斯定理相關?科斯的回答是清楚的,“通常認為商人得到和使用的是實物(一英畝土地或一噸肥料),而不是行使一定(有形)行為的權利。我們會說某人擁有土地并把它當作生產要素,但土地所有者實際上擁有實施一些有限制行為的權利。”[1]43-44在經濟學意義上,如果物的歸屬不明確、權利沒有主人,那么就不可能有有序的市場交易,因而必須對權利的歸屬作出判斷和決定,因為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
然而,科斯沒有注意到的是,從法學的角度,權利界定問題則要復雜得多。因為權利界定不僅僅是市場交易的基礎和前提,也可以織合進市場過程中,是市場交易的結果和目標。本文認為,在邏輯和語義上,所謂“權利界定”包括權利的確定以及權利的界限兩方面,存在著以下三個問題:(1)某些主張、利益或者行為是否能夠在法律上以權利之名得以確認,以及已得到法律確認的諸種權利的界限在哪里;(2)權利界定的上述問題是或者應該以什么準則進行;(3)由誰或者應該由誰依據上述準則進行權利界定。沒有疑問,法律本身對權利界定的問題不能告訴我們很多,“科斯定理”也沒有直接告訴我們答案。科斯也說是社會成本的“問題”,而不是答案。對社會成本或任何其他問題的分析,設想科斯或者任何權威的話就是結論是很輕率的。然而,對權利界定的問題,科斯本人確實能夠給法律人某種有意義的啟發。法律人應該公正地對待科斯,像科斯一樣理解科斯。
所謂像科斯一樣理解科斯,就是理解科斯分析問題的角度。眾所周知,科斯定理之所以能提出,主要是科斯從“損害具有相互性”的角度分析了一個古老的經濟學爭議性論題,即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的分離問題。具而言之,針對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的分離問題,以庇古為代表的傳統經濟學的處理方法是讓社會成本內部化。例如,工廠對周圍居民造成了煙塵損害,政府可以向工廠征收同等數額的稅收,使損害所產生的社會成本內部化。但科斯認為,“傳統方法掩蓋了不得不做選擇的本質。通常人們會把問題看成A損害B,然后決定該如何制止A。但這是錯誤的。我們處理的問題具有相互性本質。若要避免損害B,就會損害到A。真正必須決定的是允許A損害B還是允許B損害A?問題要避免較嚴重的損害。”[1]2顯而易見,“選擇”和“相互性”是上述引句中的兩個關鍵詞,然而,科斯的大部分追隨者強調“相互性”,卻相對忽視了“選擇”這同樣重要的語詞。對于選擇,與權利界定的上述問題相呼應,也有三個問題需要分析:(1)什么是選擇,科斯所說的選擇是哪種意義上的選擇,這涉及選擇的場域;(2)選擇存在本身有什么理論和現實意義;(3)選擇得以作出的前提是什么。我們要把“選擇”貫穿于權利界定的上述三個難題之中。
二、選擇的場域問題
權利沖突是近年來法學研究中的熱點和爭議性論題之一。通常來說,所謂“權利沖突”指的是合法、正當權利之間的沖突,這就排除了侵權行為、違法行為,同時排除了法律權利與道德權利、道德權利與道德權利之間的沖突。當然,也有學者認為,任何權利在法律上都有特定的界限,權利的邊界通過諸如立法技術、司法解釋、法律原則、公序良俗等法律方法予以劃定,因而不會發生沖突。[3]例如,任何人都有生育權,他可以和自己的心儀對象結婚生子,但他卻不能強迫對方為自己生育且一定要生兒子。但這種觀點的問題在于,既然事后可以通過上述方法來確立權利的界限,為什么當初在立法的時候不把各種權利界限劃定好?事實上,權利之所以發生沖突,主要就是因為權利界限的模糊。當然,我們不必限于“權利是否存在沖突”這種語詞上的無謂爭論。其實,這兩種觀點是對不同問題的兩種回答,本身并不是沖突的。權利的界限通過各種手段得以確立的結果就是權利沖突的解決,但這種回答又是以權利界限存在模糊為前提,無論你是否將這種狀態稱之為權利沖突。
除卻權利沖突語詞上的爭論,關于權利沖突的分析通常將權利沖突的本質歸結為利益沖突。本文認為,這種分析權利沖突的思路是片面的。實際上,分析者之所以將權利沖突歸結為利益沖突,重要理據就是科斯所提出的相互性。分析者的邏輯是把科斯所提出的“損害的相互性”等同于權利的相互性。然而,對于相互性這個概念,分析者沒有注意到科斯的概念是狹義、有限定的,他們是依據權威進行論辯,但引用的權威恰好又被誤解了。把權利沖突解釋為權利的相互性并進而等價于損害相互性,存在著邏輯上的問題。這種分析權利沖突的觀點實際上預設了權利本質的單一性,即利益(interest)總是權利的相關項。但事實卻是,權利與利益之間的關系要復雜得多,權利是正當的事物,利益本身無所謂正當與否。[4]權利的相關項還可以是自由(freedom)、資格(entitlement)、能力(power、capacity)以及主張(claim),與利益沒有必然的相關性。[5]把權利等同于利益就必然會耗散權利的多重屬性。如果法律上所有的對立主張都可以以利益的形式進行比較和衡量,那么權利主張就不會在本質上不同于利益主張。拉茲對“核心權利”和“派生權利”的區分,能夠幫助我們澄清權利和利益之間的關系。拉茲認為,“個人自由權利是一種核心權利,其他權利都由它派生出來。……通常權利所有者對于他們有著派生權利的客體都有著直接的利益。但是,那些利益并不總是成為他們權利的基礎。一種權利的基礎是權利存在陳述的正當理由中體現出來的權利,這種利益與核心權利直接相關,而與他的派生物卻是間接地相關。”[6]我對我的電腦擁有所有權,并不是因為電腦本身的價值有多大,雖然我的電腦的品牌和價位可能比其他人的要低,但我對電腦的所有權和其他人對電腦的所有權是等價的,它們都是由更高層次的個人自由所派生出來的。
在寬泛的意義上,把利益作為權利的相關項本身也并沒有多大的問題,只不過我們需要知道,這里的利益指的是哪種形態的利益。在法律上,人格與尊嚴、家庭關系、從事實業與締結合同自由、與他人友好和諧關系、就業穩定、公共安全,等等,這些都是利益,而且是每一個人、每一民族或國家所向往和追求的。但是,如果這些利益分散地由相關主體享有,例如丈夫擁有做父親的利益,妻子同時擁有不想生育的利益;孕婦擁有自我決定的利益,胎兒(或國家)同時擁有生命的利益……也就是說,沖突的兩造利益沒有附麗和著力點的話,分散的主體就會把影響自我利益的各種權重因素,特別是一些不相關、不重要的因素加入到利益的識別和加總中,最終變成了純粹量上的比較和判斷。對利益沖突解決的結果就是諸種權利之間存在等級,這顯然違背了法律的一個基本精神——權利的平等保護原則。
因此,讓利益成為權利的相關項并進而將權利沖突歸結為利益沖突,或許本身并沒有多大錯誤,只要分析者能夠找到兩造沖突利益所共同的著力點。但這并非科斯分析相互性問題的本意。真正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在兩造沖突利益之間,科斯提出了“不得不選擇”的問題。那么,這種選擇是哪個層面上的呢?我們發現“損害”的相互性存在一個隱含的或者說絕對的等價命題是損害的不可避免,由此才有可能引出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換言之,科斯的選擇確切地說是損害存在前提下的選擇,此種意義上的選擇,必然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一個單純數量上的判斷和取舍,此時的選擇是定量的。
但法律人不應該止步于此,必須追問是誰在選擇,又是在哪個層面為誰作的選擇?實踐中首先人們需要決定的是生產多少稀缺物品,然后才進一步決定誰能有資格得到這些稀缺物品。人們在處理稀缺物品的這兩種決定之間,有時候會舉棋不定,遭遇“悲劇性選擇”。有時稀缺狀態不是作為一個客觀的假定,也并非由資源絕對匱乏所造成,而是一個社會有意識地公共選擇的結果,這是一個需要分析的問題。社會要想進步,生活水平要想繼續提高,就必須有某種損害。我們不能決定損害是否發生,但我們可以選擇損害發生的時空和程度。企業可以不必為排放的污染空氣買單,并不僅僅是因為對該區域稀缺空氣的競爭使用企業所產生的社會產值最大化。更主要的是因為,該地區的居民選擇了承受這種污染。這里的選擇包括但不限于,企業在該區域的選址與否以及能夠排放污染物的種類和程度。因此,所謂經濟學意義上的相互性問題,必須首先存在選擇的可能,之后才有稀缺資源配置效率的問題。注意到選擇存在的這種場域,就使得我們將理論和實踐的關注點集中于如何制定一些實體規則識別出相關利害關系人以保護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和利益,同時科學設計合理制度結構和安排、構造正當的程序,以保證利害關系人的充分參與來確保選擇的公共性。這是選擇的第一個面向。
三、選擇的向度與權利界定的規則
在“社會成本的問題”中,科斯另一個分析角度是以權利看待生產要素。在經濟學那里,任何東西都可以看作是生產要素,只要能夠作為生產過程的輸入成分。因此,判斷某種東西能否作為生產要素的衡量標準就是看它是否對生產起到積極作用以及最終產出份額的大小。在權利可以產生社會財富的意義上,權利也是一種生產要素。那么,一種“權利”或者“生產要素”得以成立的準據是什么呢?科斯寫到:“行使一種權利(使用一種生產要素)的成本是該權利行使讓別人遭受的損失。……顯然,行為只有在得大于失的情形下,才是人們所追求的。”[1]44科斯的繼承者、法律經濟分析者們認為,在判斷是否確定一項權利以及劃定權利的范圍時,方法就是對該權利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即對社會財富總和所產生的影響。我們的問題是作為判準的“財富最大化”中的“財富”指的是什么,如何量度;這種以財富最大化為權利界定的準則,是否會使得我們丟掉某種至關重要的東西。
(一)選擇的主觀性與財富量度
在傳統禮法社會,說起對疑難案件的智慧處理,人們會想到包拯和狄仁杰。然而,我國學者蘇力提醒不要忘了海瑞,特別是海瑞對財產兩可案件的智慧處理,即“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鄉宦計奪小民田產債軸,假契侵界威逼,無所不為。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鄉宦小民有貴賤之別,故曰存體。弱鄉宦擅作威福,打縛小民,又不可以存體論。)”[7]可見,對疑難案件的處理上,海瑞很有自己的獨特心得。蘇力依據他那嫻熟的經濟學分析技巧和原理,將海瑞的司法經驗總結為:“在經濟資產的兩可案件中,無法明晰的產權應配置給經濟資產缺乏的人;以及文化資產的兩可案件中,無法明晰的產權應配置給文化資產豐裕的人。”[8]即是說,兩可案件的產權配置應該遵循財富最大化原則。
為什么必然這樣選擇呢?在蘇力的分析中,“財富”指的是什么,特別是以什么為衡量準據呢?在中國傳統禮法社會,窮人和小人占有著較少的經濟資產,對于占有更多的經濟資產擁有更大的個人效用。同樣,傳統禮法社會中的兄長、叔伯、愚直和鄉宦之類的人,除經濟資產以外,還占有著大量文化資產,并且更能夠保持和守護所擁有的文化資產。在這個意義上,由于窮人和鄉宦各自占有著不同資產,爭議產權的不同配置不僅對個人產生不同功效,且對以個人效用測度的整體社會財富總量產生不同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判決結果同樣滿足法律的公正,從合乎情理的視角,法官應當將爭議產權配置給對其產生最大個人邊際效用即占有財富相對較少的一方當事人。但蘇力沒有注意到,在經濟學中效用只是一個概念,真實世界中并沒有其物,無法觀察,是一個應該取締的概念。[9]經濟學上的效用概念應該取消還是維護,我們不去爭論。為了使分析不那么片面,我們的問題是能否以及如果可以的話,應該在哪種意義上以效用來量度社會財富?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當然可以以主觀效用衡量社會財富。財富之所以是財富在于其能夠滿足人們的某種欲望。倘若某種財產不能滿足人們的欲求,人們便沒有理由把它作為社會財富而去生產和占有。反過來,如果人們普遍地對某種財產的主觀效用越強烈,社會所能夠生產和占有的這種財產越多,該社會的財富就越大。問題是當事人的主觀效用能否被第三人客觀地觀察以及相應地權衡,觀察的結果能否與行為者的主觀效用相一致。同時,這里的主觀效用究竟是誰的?很顯然,在這里是當事人的。在預測理論中,當事人的主觀效用和偏好是被給定的,被看作是固定不變的。但也可以說這里的主觀效用是行為者的。這絕非僅是語詞稱謂的問題,因為涉及分析效用的一個重要角度,即是靜止還是動態。我們必須從選擇的角度,來分析以主觀效用量度的財富最大化問題。
那么,從選擇的角度,選擇的存在意味著什么呢?經濟學者一般認為,成本起因于選擇,有選擇就有成本。但起因于選擇的成本,必須理解的是在選擇理論中,成本形態是主觀還是客觀的。不同于預測理論,選擇理論中行為者的主觀效用是內生的,完全是主觀化的,存在于行為者的頭腦中,它側重于從動態、變化的角度看待行為者的主觀效用。因為忽視了選擇和行為者的偏好因素,我們不能客觀地對主觀效用進行衡量,這是選擇的存在本身在經濟學上的意義。
從選擇的角度,在上述疑難案件中,鄉宦等人對爭議案件產權的主觀效用反而要大得多。因為他們能夠進入到“司法”途徑主張產權,倘若對其效用不是很大的話,鄉宦很有可能通過和解、調解或者其他途徑解決。即使舍棄這一點,他們中的一方得到產權以后會怎么樣?同樣根據定義和經驗,鄉宦之所以是鄉宦,就是因為他們對產業的經營更嫻熟,通過法律將兩可財產案件配置給他們,對社會的產出反而更有可能是財富最大化的。只不過,這里的財富強調的是動態的社會產值和產出,而不僅僅是靜態的主觀效用。我也許極其渴望得到一輛寶馬轎車,而且比起現在車主或任何其他從該車主那里購買該車的人都想得到,同時我還把這一想法告訴了我身邊的很多朋友,無論從哪個角度衡量,我從這輛寶馬車中獲得的效用要比其他人大得多。但是,如果我不愿或不能支付寶馬車的購買價,社會的財富就不會因為一輛寶馬車從它現在的所有者手中轉移到我的手中而增加。也就是說,財富與貨幣相聯系,沒有支付能力作為基礎的欲望是站不住的。這種以市場為中心的賦值具備價格機制的某些優點,包括對個人偏好的敏感性,但這也并非沒有問題。當存在外部性時,價格的信息傳遞就會發生困難,而且這種以市場為中心的賦值容易導致對分配問題的忽視,即對個人的貨幣分配以相等的權重,無論個人是富裕還是貧困。[10]
(二)作為一種獨立價值和善的選擇
作為疑難案件指導原則的財富最大化在技術上存在著難題和困境,不過這些技術上的批評無關痛癢。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夠僅以財富最大化為準據進行權利的界定和配置。倘若是這樣的話,就很容易得出以下結論,即一個人是否享有權利以及所享有權利的范圍,僅僅取決于該權利對社會財富總和的影響。那么,作為經濟學家的科斯是如何看待財富最大化的呢?
雖然經濟分析注重于資源的有效配置以及財富最大化,但科斯認為在進行權利安排與社會制度選擇時,經濟分析并非唯一,更非充分,“應該在比此更廣泛的條件下進行選擇解決問題的不同社會安排,應該把這樣或那樣的對生活諸多方面影響的總體效果考慮在內。弗蘭克·奈特指出,最終福利經濟學的問題必然轉變為美學和倫理學的研究。”[1]43科斯理論的繼承者們,無論是新制度經濟學還是法律經濟分析,大部分忽視了科斯的這一告誡。就權利界定而言,“把權利的基礎建立在功利性的移動的沙灘上就是把它們置于危險之中,因為在正當的條件下,它們將被擱置一邊或被侵犯。這樣的情況可能并不常見,但是這卻是一個取決于功利性條件的隨機事件。把權利的功利性置于我們人類處境之上顯然就是使它們受制于那種可能變化的東西。”[11]
進一步,法律人一般都會承認人們能夠享有的權利并不僅限于法律的規定,有些權利,它們不僅獨立于社會認可和強制實行,而且為法律以及其他社會制度提供了正當性基礎。如果社會安排侵犯了這些權利,它們必然會受到相應的批判。事實上,我們不會僅僅根據侵犯個人自主是否會增加社會財富,而決定是否允許侵犯個人自主性的社會安排。社會無論多么繁榮或者貧困,總會存在乞丐和無所事事的人,倘若把他們都抓起來集中在某個地方參加生產勞作,無論是從社會財富最大化的角度,還是個體效用的角度,都是非常可取的社會政策。但我們之所以不去這樣做,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做法傷害了我們的感情,違反了我們每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一些道德直覺,即人的尊嚴。這些東西在我們每個人心中根深蒂固,這就決定了不允許財富最大化到處起支配作用。
因此,選擇的存在本身,可以也應該作為一種獨立的價值和善,這是人之尊嚴的當然含義。可以這樣說,一個人的尊嚴就是他(她)能否選擇以及具體面對的選擇范圍的函數。某種權利安排和社會制度是否可取,在很大程度上應該由擴大或縮減個人的選擇領域是便利還是阻礙個人選擇所決定。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作為善的選擇應該作為權利界定準則的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財富最大化的適用范圍。
四、選擇的前提預設
關于選擇的三個基本問題,我們已經分析了其中的兩個,但選擇的一個最為重要前提我們還沒有指出,即選擇能夠作出的依據是什么?清楚的是,選擇經由比較而作出,這至少隱含了以下兩種含義:(1)選擇的相關項是兩個以上;(2)選擇項之間具有可比性。那么,比較并進而選擇的相關項是什么呢?科斯對這個問題也給出了回答,但答案并不存在于“社會成本的問題”中。對科斯回答的追尋不要忘了科斯經濟學家的身份。法學經濟分析者要想自稱為科斯繼承者,一個需要認真研習的文本就是科斯1937年所寫的“企業的性質”。[12]實際上“社會成本問題”就是前者所提出的分析方法的一個具體應用,那么在“企業的性質”中,科斯說了什么呢?
要點在于以下方面:傳統經濟理論把企業僅作為價格機制下的一種生產函數,科斯則從組織的角度對企業予以分析。在科斯看來,企業作為一種組織機構,在經濟活動中的特征在于其是價格機制的一種替代物。建立企業之所以是有益的,是因為使用價格機制組織生產是有成本的,但企業作為市場的替代并不意味著所有的生產都由企業來組織,現實中仍然有很多的生產和交易由市場組織。從經濟學的角度,由于企業運行本身是有成本的,那么當價格發現成本的節約與企業運行成本的上升在邊際上相等時,企業就停止擴張。這時企業規模得以確定,作為組織企業替代市場的機制就會停止。在科斯的分析框架中,成本、選擇、替代、比較、邊際、限制以及競爭,這些語詞代表著同樣的含義,歸結為一點就是比較制度分析。令人不解的是,這一點卻遭到了法律經濟分析主張者無情的漠視。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返回到“社會成本的問題”。科斯從權利的角度看待生產因素,但科斯眼中的權利不能等同于法律人所理解的權利,當然法律人對成本的理解也不能等價于經濟學者眼中的成本。科斯眼中的權利不是像法律人所理解的那樣書寫在律法條文中,更多的是作為制度選擇和決策的結果。在科斯的分析中,他列舉了一些普通法法院的法官判決作為其分析結論的佐證,這很容易給人以錯覺,即在交易成本不為零的時候,應該由法院替代市場并壟斷對權利的界定。這種法律替代市場的分析,是不是意味著科斯舍市場而去,唯獨看好法院呢?例如,波斯納將科斯定理之于法學分析的意義在于,“法律的功能是便利自由市場的運轉,并且在市場交易成本高不可攀之處‘模擬市場’,對那些如若市場交易可行本可以被期待產生的結果,予以法律上的確認。”[13]是否像一些學者所批評的那樣,科斯忽視了法律本身界定權利的成本呢?[14]
本文認為,權利的界定確實會存在“問題”,但不是“成本”的,而是制度的。首先,權利界定總是在特定制度環境中進行。對疑難案件的權利界定,必須要考慮決策的制度環境。忽視了法律這一規范性系統本身,意味著法院面前的每一個案件都是獨特的,需要從頭做起。由于裁判沒有了拘束對象,錯誤難免而且成本很高,更無判決先例可言。如果說經濟分析和思維確實如科斯所主張的那樣,注重于總體的和邊際的,那么法學的分析和思維首要的是個體的和規范的。實際上,在具體分析權利界定和社會安排的時候,科斯本人非常注重于作為制度的法律對經濟分析的限制,“看來法院得了解和考慮其判決的經濟后果,只要不給法律本身帶來過多不確定性。”[1]19這段引句中的“只要”后面的內容,需要法律人細細品味。當然,除了法律本身的確定性,還有什么需要法院考慮的,就不是作為經濟學家的科斯所能給予我們的了。這是專業使然,更進一步是比較成本使然。
制度之于法學分析的第二個意義,是科斯所提倡的制度比較分析。一方面,當交易成本為正的時候,特別是隨著所涉利害關系人的人數和相關事項復雜性的增加,作為權利界定和保護的法院也會失靈,甚至會出現目標和制度之間的悖謬組合,對權利的最佳保護不是法院,反而可能是政治過程;法院的裁判也并不必然以權利和原則為裁判準據,更有可能是以政策為指導原則。[15]另一方面,權利界定的制度系統也不僅僅是法院,還可以是市場、政治過程以及行政命令等其它決策制度。在具體情境中,權利界定究竟在何種制度系統中進行,固然取決于當事人的選擇,但更取決于諸種制度系統之間的競爭。任何一個獨立完整的制度系統的運行都需要成本(包括當事人的參與成本),當成本的增加抵消了所替代制度系統的收益時,該制度系統界定權利的能力便得以確立。交易成本決定了權利界定的制度邊際。最終,權利界定的合適制度系統便是制度比較分析的結果。選擇的第三個“潘多拉之盒”終于也被打開。
五、結語
面對當時法學研究中充斥著的概念和形式主義,美國著名聯邦大法官霍姆斯在1897年曾預測到:“理性地研究法律,今天的主宰者或許還是法條主義者,但未來的法律從業者則屬于精通統計學和經濟學的人。”[16]令人遺憾的是,霍姆斯拋出的這一“繡球”,直到1960年才有人接到,但接球者不是法學學者,而是經濟學家科斯。按照科斯說法,他的“定理”并不是要傳遞給律師或法學學者,而是經濟學者,他試圖影響的不是法學而是經濟學。[17]科斯如何看待他對法學的影響,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人應該如何對待“科斯定理”,是作為定理,全盤毫無保留的接受;還是認為其為法學問題的分析提供了啟發性的思路。這也是個選擇的問題。
本文認為,科斯定理之于法學的意義是科斯能夠對權利界定難題給予某種分析思路上的啟發,這是由“社會成本的問題”中“選擇”這個分析問題的角度所提供的。從選擇的三個基本問題出發,本文分析了選擇對權利界定問題所可能具有的意義:(1)在權利沖突需要確立權利界限時,選擇的場域不應該局限在資源稀缺前提下的資源配置效率意義上的選擇,還應該將法學意義上的公共選擇納入分析者的視野;(2)權利界定的準則不應該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財富最大化,還應該將法學意義上作為一種獨立價值和善的選擇涵攝在權利界定的準則之中;(3)權利的界定需要在一定的制度系統內進行,權利的界定不是任何單一制度系統所能完成的,諸種權利界定的制度邊際,需要一種比較制度分析。關于權利界定問題的以上三個方面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參考文獻]
[1]Coase 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 (3).
[2][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M].張軍,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135-138.
[3]郝鐵川.權利沖突:一個不成為問題的問題[J].法學,2004,(9):2-6.
[4]范進學.權利概念論[J].中國法學,2003,(2):15-22.
[5]夏勇.權利哲學的基本問題[J].法學研究,2004,(3):3-26.
[6][英]約瑟夫·拉茲.自由的道德[M].孫曉春,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157.
[7][明]海瑞.興革條例[M]//[明]海瑞.陳義鐘,編校.海瑞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117.
[8]蘇力.“海瑞定理”的經濟學解讀[J].中國社會科學, 2006,(6):118.
[9]張五常.科學說需求[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15-118.
[10][印]阿馬蒂亞·森.理性與自由[M].李風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 2006:523-524.
[11][美]弗雷 R G.行為——功利主義、后果論與道德權利[M]//楊帆,譯.曹海軍,編.權利與功利之間.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136.
[12]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 Economica, 1937, (4):386-405.
[13][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理論的前沿[M].武欣,凌斌,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6.
[14]凌斌.界權成本問題:科斯定理及其推論的澄清與反思[J].中外法學,2010,(1):104-121.
[15][美]尼爾·K·考默薩.法律的限度——法治、權利的需求和供給[M].申衛星,王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187.
[16]Holmes O W. The Path of the Law[J]. Harvard Law Review, 1897, (8):469.
[17][美]羅納德·哈里·科斯﹒企業、市場與法律[M].盛洪,陳郁,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26-30.
〔責任編輯:馬琳〕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16)04-0111-06
[作者簡介]張洪新(1987-),男,山東臨沂人,博士研究生,從事法學方法論研究。
[收稿日期]2015-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