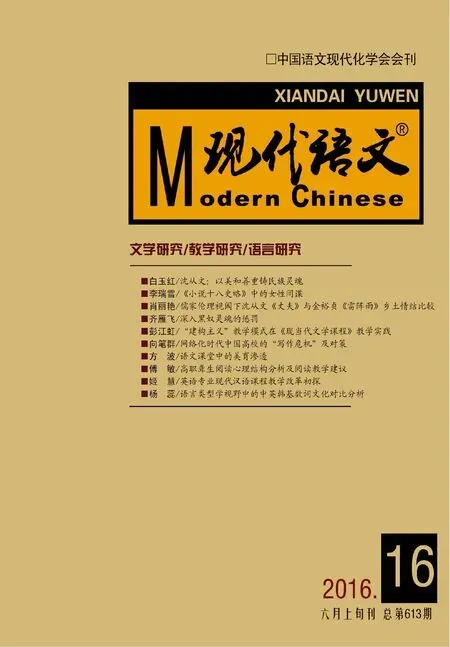文化生態學視閾下的艾米莉·狄金森詩歌賞析
○丁丹丹
?
文化生態學視閾下的艾米莉·狄金森詩歌賞析
○丁丹丹
摘 要:文化生態學是20世紀晚期的一種交叉學科式的研究方法,它著眼于研究文化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作用與相互關系,認為生態知識是在尋找心靈與自然、人類領域與非人類領域的“關聯模式”中產生的。艾米莉?狄金森被視為20世紀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驅之一,其詩歌所表現出的不合常規的與陌生性的審美話語模式,為文本的生態倫理力量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間,拓展了狄金森詩歌的文化內涵,為讀者深入了解狄金森及其詩歌提供了新的審美方向。
關鍵詞:文化生態學 狄金森詩歌 生態力量 審美
“作為文化生態學的文學”是當代生態批評與批評理論領域內的新概念。在這一概念中,文學被視為一種文化形式,通過它可以富有成效地探討文化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同時,立足于文學想象性文本進行的審美也豐富了我們對作家作品的文學解讀,并充分發揮其在文化話語系統中的生態力量。狄金森被視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驅之一,她的詩歌以其高度的反思性,奇特的表現形式以及個性化風格受到廣泛關注。其詩歌所表現出的不合常規的與陌生性的審美話語模式,也為文本的生態倫理力量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間。本文從狄金森作品中選擇了三首具有代表性的詩歌加以分析,嘗試從文化生態學的角度進行審美鑒賞,探討狄金森詩歌新的審美意蘊和文化內涵。
一、詩歌闡釋人與自然之間的反思互動性關聯
文化生態學開創者之一胡貝特曾指出,在以往文學情境中,文學文本已經立足于探索文化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并且在創造性的探索中,衍生出文學文本對文化創新或文化自我更新的特定力量。《自然正如我們所見》,是欣賞狄金森自然主題詩歌不可忽視的一首。在作者看來,自然是聲響、光影和色澤的有機融合,自然中一切人類與非人類存在都參與到人類主觀與客觀的有機聯系與統一認識中來。作者在詩歌中盡情表述大自然和諧共生這一有機生態自然觀的同時,也透露出她對人類文化認知的理解。這一理解在文本性審美上,通過作者結合概念與感知體驗、反思意識與復雜的動態自然的方式得以展現。
“自然就是我們看見的景象——/山巒——午后的風光——/松鼠——日月食——蜜蜂——/不——自然就是天堂——//自然是我們聽到的聲音——/長刺歌雀——海洋——/蟋蟀——雷霆——/不——自然就是和諧——//自然就是我們熟知的一切——/但又沒法予以說明——/對于她的單純/我們的學識何其無能。”[1](P668)
詩歌中連續出現的自然景象,山巒、風光、松鼠、蜜蜂、日月食,以及自然的聲響,歌雀鳴叫、海洋喧囂、蟋蟀低語,連同所有不為人類所知的自然界情調,一起構成了融洽共存的人世天堂。詩歌中,生物符號作為文學生成潛能的一部分被保留在文學創造中,成為連接文化與自然的研究對象。自然中的各種景觀成為“我們”觀察的對象存在于人類的生存之境,各種外在聲響也成為協調自然的曲調進入“我們”的生活空間。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在自然萬物和諧相融的運轉模式下進入到相互的動態發展領域。在此,我們不難發現詩人對自然的獨特理解除了有機的生態自然觀,還蘊含著自然對人類生命發展不可缺乏的調節力量。作者筆下的自然充滿靈性,宛若生命之母,賦予我們一切生命的形態和存在的可能。盡管人類文化與智慧的局限性使之無法完全揭示自然的淳樸和美麗,但是人類卻可以借助知覺感知與反思意識在對其熟知領域的體驗中獲得生命的自我更新。在這里,文學作為一種持續自我更新的媒介,使一些被忽視的生物能量找到一種表達方式,從而整合為更大的生態學的文化話語。文化生態學由此在詩歌中窺見一斑。
二、詩歌闡釋心靈與自然之間的反思互動性關聯
貝特森認為,文化與人類心靈并非相互封閉的實體,而是基于心靈與世界二者之間活生生的相互關系之上的“開放的動態系統”。其理論根據心靈與自然、精神過程與生物進化的互相依賴與互相闡發而將文化與自然聯系起來。心靈被放置在“自然歷史的正中心,被放在生命過程及其連續的、顯著變形的自我生成語法中”[2]。狄金森詩歌所展示的豐富的心靈圖景是一種更加開放且具有活力的生命圖景。自然中的一切生命和靜物都以其豐富的象征意義,被她放置在個人自我心理世界中,借以表達人類精神及其心靈狀態,體現文化內涵。請欣賞下面這首詩歌:
“一口井滲透著何等的神秘!/水生活的如此遙遠——/一個另一世界來的鄰居/居住在一個甕里面//甕的界限誰也未曾看見,/除了他的玻璃蓋子——/就像你每次盯著/一個深淵的臉面凝視!//草兒沒有害怕的樣子,/我常常詫異,他竟能/站的如此靠近,這般大膽地/注視我感到敬畏的情景。//它們或許有點關系,莎草伴著大海挺立——/在那里它沒有立腳之地/也沒有流露出任何膽怯//但大自然還是一名生客;/援引她最多的人們/從來沒有經過她鬧鬼的房子,/也沒有簡化她的鬼魂。//可憐那些不認識她的人/總受到這種悔恨的幫襯/認識她的人,了解她越少/便離她越近。”[3](P1400)
詩歌借一口井所產生的另一世界的鏡像來觀照人類與自然的相互關系。“我”代表自認為了解并洞悉一切的人類,凝視深淵的臉面,對井中另一世界的未知事物感到神秘且敬畏;而那極其普通為人所不屑的“草兒”,卻是大膽的注視讓我產生敬畏的神秘未知,不露任何膽怯。這里,敘述者與自然之間建立了一種相互關系。這種關系是詩歌在其隱喻與敘事融合過程中所顯示的作為世界中基本存在形式的熟悉性與陌生化。為人所熟悉的自然由于一口井滲透的神秘變的遙遠,使人產生了敬畏,轉而變的陌生。與此同時,草在人類文化領域里,一直是作為自然界渺小及無用的象征存在的,而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自然存在并不符合人類社會實用主義形式的秩序與意義,這是人類文明強加于被馴化的自然之上的東西。詩歌中卑微的小草面對強大且神秘的自然,膽怯本該是最合理的選擇,然而也是它力量的唯一來源。在這一強弱對抗的過程中,相較于我的敬畏之態,小草卑微的生命尤顯強大。這在無形之中也契合了這樣的人類思維悖論,渺小的存在融于強大者之中從而獲得了強大的品質。
此外,敘述者與草通過一口井被聯系在一起,人類自我在此由觀察者轉變為被觀察的對象,與自然之遠近頃刻間發生了空間上的置換。客觀自然也從一個被觀察的對象轉變成人類主體的自我反思。“認識她的人,了解她越少,便離她越近”,與大自然的接近或許只有極簡的心靈才能辦到。在這里,作者用象征的方式將人類對外部世界的體驗呈現出來,使自然中那些被文化割裂的東西在人類自我反思的象征中成為詩歌審美過程的焦點,從而反映出文化與自然之間的根本聯系。
三、詩歌闡釋文化與自然之間的反思互動性關聯
“人類的各種典型環境不僅有外部環境,而且還有內在環境、精神世界與心靈的各色景觀以及文化想象。文化想象編織了人類的生境,同時還編織了外在自然環境與物質環境。”[4]從這種文化生態學的視角出發,現代文化與意識所生成的內景觀對人類及其外在環境同樣重要。可以說,人類通過他們的根本天性,說明了他們不僅是動物本能的存在,而且還是文化的存在。狄金森一生離群索居的生存狀態從表面上看似乎使她隔絕了所處時代的外在干擾及侵襲,但是她退避外部世界,面向內在精神世界的這種生活方式,卻使她具備更加獨到的觀察社會的視角。并且,她所生活的時代與社會,以及她在早期閱讀中所攝入的文化養分,都在潛移默化中進入到她的詩歌寫作中來,使她的詩歌創作更加的深邃與奇特。她充滿悖論、超越邏輯、突破規范的詩歌直抵生活的真實,也因而具備了文化的多樣性。再來閱讀一首狄金森描寫鮮花的詩作:
“盛開——是結果——遇見鮮花/偶爾匆匆一瞥/幾乎不會令人思索/那不為人注意的境況/輔助光明事物/錯綜復雜/接著又主動呈現/恰似蝴蝶向著正午——//包藏花蕾——對抗蟲害——/獲取飲食露珠的權利——/調整熱量——躲避寒風——/逃遁偷襲的蜜蜂//大自然沒有令她失望/在那天恭候她/作為鮮花,深遠/責任——(P1058)”。[5]
狄金森對鮮花的贊美不同于同時代的許多作家,除了對愛情與美德的發現,她也將視角擴大到心理、情感、道德及思想等方面。本詩中的鮮花便承載了厚重的精神和道德含義,詩歌中,人們從低矮的鮮花那里學會謙遜與禮讓,堅韌與頑強的高貴品質。鮮花之于她成了自強自立的精神啟示,顯示了狄金森“從一個矛盾重重的少女發展為獨立女性的過程”[6],反映了詩人在生存領悟中所形成的高度社會責任感。在她看來,鮮花擁有的“一套審美體系——/遠比我的完美”(P137)。詩人用從自然之物中所獲取的有關精神和道德的啟示向我們展示了大自然溫柔完美的訓誡。她突破了十九世紀女作家在描繪花卉時往往強調鮮花作為禮品的感情價值的傳統文化的慣例,使詩歌反映出不一般的審美情趣和文化活動,闡發了她獨特的文學向往。詩歌中,詩人重視精神生態,不斷向內探索,她借助自然界擁有“天鵝絨的音節”“長毛絨的句子”和“紅寶石的深度”般的語言,倡導和歌頌人類精神凈化,并希望用這種精神力量制衡人性在物質誘惑面前的丑惡,努力達到精神十木的平衡。
此外,詩歌中蝴蝶和蜜蜂被作者用來表達鮮花綻放過程中所受到的誘惑和侵襲。其中蜜蜂是狄金森在她的許多詩歌中成功描繪的性暴力行為的施虐者的形象,它的再次出現,更可見當時的女性若要在強勢的男性本位社會里獲得獨立是何等的不易。在這里,作者借助豐富的文化想象、對詩歌加以文化創造,賦予詩歌新的文化內涵來反映她所處于其中的環境與社會。并通過對詩歌形象象征意義的再創造與設定,探尋著心靈內在景觀的豐富性及多樣性,從而使詩歌的想象、情感、以及詩人的內在文化承受共同構成了詩歌的多樣文化生態。
四、總結
艾米麗·狄金森一生看似簡單、孤獨,她的內心卻燃燒著不息的精神探索的火焰,她傾其一生在痛苦地進行心靈的探尋。她對自然的認識其實就是對人類社會的認識,她所體驗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實際上就是人與現實社會之間的關系。從她的詩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詩人的那種既拘囿于社會和文化,又超越社會和文化的矛盾生存狀態。[7]其詩歌所反映出來的人與自然,心靈與自然,文化與自然之間的反思互動性關聯為我們掌握文學中的文化生態提供了有力佐證。在相互牽涉的各種人類文化中,缺憾與不公促成了整個文化的完善與顛簸發展。文化從自然界中得到啟示與修復,自然界則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博大的實驗性基礎以及文化性反思。狄金森詩歌在其有意與無意中所體現出來的文化生態學思想為我們欣賞其文本提供了新的視角。
注 釋:
[1]蒲隆譯,艾米麗·狄金森:《狄金森詩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120頁。
[2]Gregory Bateson:Mind and Nature:A Necessary Unity,N.J.:Hampton,2004,p14.
[3]蒲隆譯,艾米麗·狄金森:《狄金森詩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149頁。
[4][德]胡貝特·察普夫:《作為近期生態批評方向的文化生態學》,生態美學研究,2015年,第1期,第143頁。
[5]劉守蘭:《狄金森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年6月版,第224頁。
[6]Wendy Martin:An American Triptych: Anne Bradstreet, Emily Dickinson, Adrienne Rich, Chapel Hill: U of North Carolina P,1984,p157.
[7]蘇煜:《埃米莉·迪金森詩歌中的自然》,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第139頁。
參考文獻:
[1]蒲隆譯,艾米麗·狄金森著.狄金森詩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120.
[2][德]胡貝特·察普夫.作為近期生態批評方向的文化生態學[J].生態美學研究,2015,(01):143.
[3]劉守蘭. 狄金森研究[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224.
[4]Wendy Martin.An American Triptych:Anne Bradstreet,Emily Dickinson, Adrienne Rich[M]. Chapel Hill:U of North Carolina P,1984:157.
(丁丹丹 湖北十堰 漢江師范學院外語系 442000)
基金項目:(本文系校級基金項目“艾米麗·狄金森詩歌研究”[項目編號:2011B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