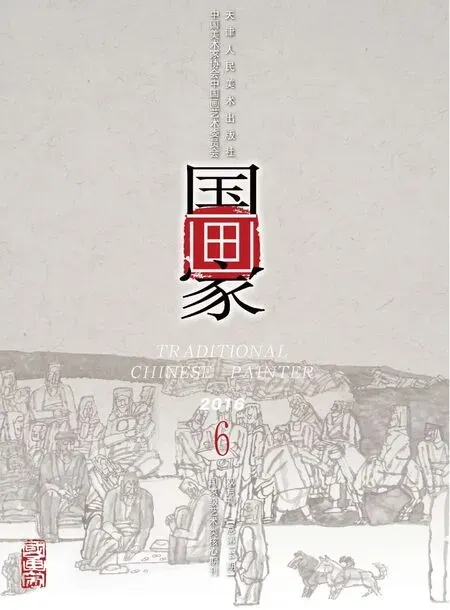私淑親炙與學院教育——中國畫兩種教學方式比較
舒士俊
私淑親炙與學院教育——中國畫兩種教學方式比較
舒士俊
中國畫的教學方式大體有兩種,一為舊時私淑親炙的帶徒方式,一為現代學校教育。這傳統與現代兩種教學方式,其實在中醫和戲曲中也同樣存在,究竟誰優誰劣?早在1988年,我曾寫過一篇《另一角度的探討》(見2002年出版的我個人論文集《探尋中國畫的奧秘》),指出:
“傳統的國粹就是如此:從局部看,無論中醫的一方一脈、武術的一招一式,還是京劇的一板一調、書畫的一點一畫,似乎都很死,很簡單;但從整體看,則往往都極講究氣、味之類虛冥玄奧的東西,其中經過參差變化,卻是微妙無窮。”“由于認為只有充分地深入局部并達到貫通,才有可能完全地把握全體,中國畫家課徒總是要求從一樹一石做起,從訓練用筆的質實感開始,以后再逐步爭取靈變。在中國畫論中有以‘呼吸’二字來論述筆墨氣息的,只有當每個局部的筆墨都達到氣息調暢醇和,也就是如黑格爾所說的‘在每一點表現和曲折上顯出整體的理念和靈魂’,全體才會達到一種氣象高華壯健的境界。”
對這種私淑親炙帶徒方式之優點,陸儼少曾說得很明白:
“作畫得名師親授,看其下筆順序,怎樣執筆,怎樣審勢,怎樣用筆、用墨、用水、用色,怎樣收拾,層層加染,以至完成。尤其作畫中間片言只語,點出關鍵,啟發甚多,銘記在心,歸后細細琢磨,回憶全過程,進益自多。如果僅得其畫稿,于此臨摹,雖然也能多少看到其用筆用墨之法,但先后不明,層次模糊,終屬隔了一層。甚至僅僅看到照片或印刷品,更屬霧里看花,難明真相。所以學畫起手最好有人指點、示范,而入手之后,老師的法則,將影響終身。”
齊白石曾說:“人知筆墨有氣韻,不知氣韻全在手中。”這按美學家朱光潛的說法便是:“各種藝術都要有全身筋肉的技巧。……要想學一門藝術,就要先學它的特殊的筋肉技巧。”對學習中國畫來講,作畫之際指腕筋肉的靈活度顯然亦是關鍵:若得名師親授,不但便于看清作畫先后技法過程,亦可使指腕筋肉運作受到靈活的啟示。時常見到有些畫家用筆很僵,毫無韻律可言,緣由便因缺乏名家親炙之啟蒙,其指腕筋肉板刻,又如何能夠隨意揮灑呢?
我在那篇文章中講了私淑親炙對學習中國畫特有“語言”韻律,亦即筋肉技巧之意義,因學習筋肉技巧韻律之周期相對漫長,傳統因此反對“求脫過早”;但亦正因反對“求脫過早”,卻使這場筆墨修煉的“馬拉松”中有許多人中途落荒而終無所成。
我那篇文章發表之時,陸儼少先生已受聘去杭州浙江美術學院(即今中國美院)任教山水課并帶研究生。使我意外驚喜的是,他讀到我以筆名發表的此文,打聽是我所寫,竟親自給我寫信,稱贊它“中間論述,深獲我心”。而我更為驚訝的是,陸老早年在上海,采用的是親炙帶徒方式;后來至杭州,他則取用現代學校教育方式,兩者竟大異其趣。
“文革”時陸儼少在上海,平日要到畫院監督勞動,弟子只能周日去他家親見他揮毫,隨后把畫稿帶回家臨摹(而今在拍場露臉的一些陸畫名作,那時陸老很隨便就讓學生帶回家去臨),臨完還會親自評點。“文革”之后陸老到杭州任教于美院,則不再要求學生對臨其親筆畫稿,而是在他指導之下直接臨摹宋元大家的山水。中國美院的山水畫教學正由于陸老這般倡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教學規范。而陸老教學方式的這種改變,竟使其前后兩撥學生呈現大不相同的面貌:以前在上海受他親炙的弟子,有的當年在筆墨學習中還曾受過陸老稱贊推許,但后來卻皆歸沉寂,在美術圈默默無聞;而陸老當年在美院帶出的研究生,畢業后卻很快嶄露頭角、聲名卓著,有的留在美院師承傳授,已撐起山水畫教學一片天,使中國美院山水教學之影響遍于全國。
為何兩種方式的教學效果竟會如此不同?美院研究生畢業所提供的機會當是重要因素,但值得關注的明顯差異還在于:陸老在美院帶出的研究生之卓越者,其個人風格面目已可辨別;而陸老當年私淑弟子之優秀者,臨習仿作雖筆墨頗佳,但卻仍無法出脫成自我面目。顯然,私淑帶徒偏重于筆墨語言之修持錘煉,但這手上功夫必是長期乃至終生致力才有所獲,絕非短期所能奏效。
看來陸老明白深入學習筆墨之路極其漫長,學校教育若亦以臨仿為主來孤軍深入,以求從局部到整體的氣韻貫通,那漫漫修煉長路,又哪能體現學校教育近期成果?因而必須有所變革,適當偏重學生整體藝術素養,啟發他們對格調圖式之體會與把握,這樣才能夠引導他們盡早尋找到自己所應追求的面目。
但凡卓越超俗的書畫作品,總是既重形體結構、圖式構成,以見其氣局,又重功力錘煉,以顯其筆墨韻味,因此卓絕的書畫之作,可謂紙上之“筆墨舞蹈”。一位杰出的中國畫畫家,應是既能當這“筆墨舞劇”中運籌帷幄的“編導”,來規劃其圖式格局,又要置身其中,能當姿態妙曼的“舞者”,以揮灑其筆墨韻味,如此一身而兼二任之卓絕難度,必然會淘洗掉大量畫家,而能通過這艱巨考驗,其人其畫才經得起歷史檢驗,才會被后人所認可。
由此來梳理從學校教學走出來的成功畫家,可以看到林風眠、李可染早年的用筆,其實亦并非極合規范的中國畫用筆,但他們在結構圖式的學習上很早便有卓異悟性,尤其李可染早年對于氣場構成之敏悟更是驚人,正由于這方面之優長,使林和李很早便在畫界脫穎而出。而早年在用筆上有所不足,他們自己心里亦是明白的,遂以幾十年乃至一生的時間,堅持孜孜苦練用筆以作彌補,致其后來之佳作,其圖式構成與筆墨韻味,達于絲絲入扣之審美趣旨。
在老一輩名家中,潘天壽最為看重圖式結構,這使其聲名超出同輩許多畫家,同時也對中國美院的中國畫教學產生了很久的影響。吳冠中在老輩名家中最欣賞潘天壽,便因為他們二位都非常看重形式構成。據我分析研究,在對氣場構成的感悟方面,吳還曾明顯受到李可染的啟示(可參見拙文《我對吳冠中的再辨識》)。盡管在當今國畫圈,在筆墨上對吳冠中有微言者仍不乏其人,但在去世之后他畢竟仍站住了,原因當然絕非他的筆墨有多牛,而在于他對氣脈構成之體察感悟超越常人,還有其造型概括能力及色彩修養卓異。畫意與寫意,其偏勝在于畫意。為何在中國畫的學校教學中,與西畫有所相關的形體結構、圖式構成,包括色彩修養,尤其是中國畫所特別應予講究的氣場構成(這卻是當代中國畫教學中被相當忽略的)能夠幫助畫家較早出成果呢?因為那些是可以通過相對較短時期的教學啟悟,便有可能捕捉到的形體軀殼。
而筆墨韻味,則應是中國畫本性深層的精神靈魂,它需長期修煉,隨人生從“嫩”變“老”,一起成長,絕非朝夕便可練就。筆墨內涵之精神靈魂非但修持不易,要捕捉和體悟亦難,為何不少仿制贗品能蒙混許多人的眼睛?其緣由即在于此。而這種蘊含精神靈魂的筆墨韻味,光靠一般性的學習體悟肯定還遠遠不夠,必要得有成就名家之私淑親炙,才有可能感受其氣運脈搏。如以上提到的林風眠和李可染,雖于圖式構成早有穎悟,但在筆墨精神氣息上,林與李皆曾受齊白石之啟悟,李則更受惠于黃賓虹。吳冠中看上去特立獨行,但他極喜石濤,與李可染亦時有過從。最有意思的是吳昌碩的弟子王個簃,其個人面目并不明顯,但卻筆墨修煉有素,程十發、林曦明、方增先三位皆曾先后向他求教筆墨。而正由于他的筆墨授受,亦因程、林、方三位各自在師承研習上竭盡努力,使王個簃的筆墨精神通過轉授而發酵,顯然增添了程、林、方他們各自圖式結構的內在活力,使他們各自的圖式風格得以升華。只可惜的是,像這樣筆墨揮寫自如,可以讓學生從揮寫中感受到從容氣息的中國畫名家,在過去老一輩中并不少見,而今卻已寥若晨星。中國畫私淑親炙的帶徒方式,在當今已明顯趨向式微。而這種狀況,又會給今后中國畫的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這亦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