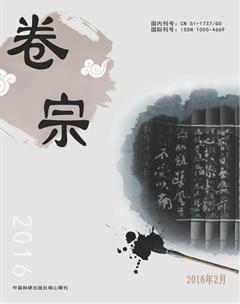論當前誘惑偵查立法中不足的完善途徑
許珂
摘 要:誘惑偵查主要分為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和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誘惑偵查作為一種具有雙面性的偵查手段,如果運用得當,會及時偵破犯罪,實現刑事訴訟及時追訴犯罪的任務;否則,會對公民的權利造成極大的威脅,損害偵查機關的形象,造成國家權力的濫用。
誘惑偵查在近年日益嚴峻的隱形化犯罪的挑戰中得到了更多的應用。盡管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的第151條的規定試圖提升此類偵查手段的法治化程度,但由于法律規定的寬泛與模糊、司法處斷原則的失當與片面,誘惑偵查適用過程中凸顯出執法無序與司法失范的弊端。完善途徑是,在法律解釋論層面,應當對適用范圍、法制化規范形式與內容予以明確;基于我國特有的查權規制現狀,采用控權最為嚴格的分離式混合模式,即無論是違反誘發他人產生犯意的主觀標準,還是僭越客觀標準,即偵查人員使用了過度且令普通人難以抵御的誘惑手法,均屬違法。
關鍵詞:誘惑偵查;立法;不足;完善途徑
1 誘惑偵查概述
(一)誘惑偵查概念
學術界對誘惑偵查的概念莫衷一是,眾說紛壇,其中不乏將誘惑偵查與相關的一些類似概念混淆,因此,我們有必要明晰誘惑偵查的概念。
觀點一:誘惑偵查,是指刑事偵查人員以實施某種行為有利可圖為誘餌,暗示或誘使偵查對象暴露其犯罪意圖并實施犯罪行為,待犯罪行為實施時或結果發生后,拘捕被誘惑者。
觀點二:所謂誘惑偵查,又稱警察圈套、偵查陷阱、偵查圈套,一般是指偵查機關在進行一段時間的初步偵查后,在已經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線索或證據,但尚缺乏足以定罪起訴的證據時,預先制定偵查計劃,由偵查人員經過化裝,促使犯罪嫌疑人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實施犯罪行為,待犯罪行為實施后,再對犯罪嫌疑人加以拘捕的偵查方法。
觀點三:誘餌偵查(又稱誘惑偵查、偵查陷阱、偵查圈套),泛指國家偵查人員或者受雇于國家追訴機關的人員特意設計某種誘發犯罪的情境或者為實施犯罪提供條件或機會,鼓動、誘使他人實施犯罪并進而偵破案件、拘捕犯罪人的偵查手段。
觀點一闡述的誘惑偵查概念中,將嫌疑人的犯罪原因僅限于“實施某種行為有利可圖”之中,這是不全面的。誘惑偵查包括警察示弱佯裝被害喪失行動能力的情境,警察利用感情、肉體等關系影響嫌疑人的情境,警察作出有意加入犯罪的意思表示的情境等,這個中情境并非全部誘因均是有利可圖,誘因包括物質利益或精神或感情利益等。因此觀點一說法不全面。
觀點二中認為“警察圈套、偵查陷阱、偵查圈套”和誘惑偵查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而事實上“偵查圈套、警察圈套和偵查陷阱”其表述已有了先入為主的違法意識,誘惑偵查是為達到偵破案件目的,偵查人員有意使用的技術策略,為嫌疑人設置特定犯罪情境,或為其提供犯罪契機從而誘使他人犯罪進而偵破案件的這一過程中并不能完全定性為違法行為,若使用誘惑偵查手段過當,才會轉變為警察圈套、偵查陷阱。
觀點三表述的概念完善了誘惑偵查的主體范圍,不僅限于偵查機關人員,而是國家偵查人員和受雇于國家追訴機關的人員。觀點三認為誘惑偵查包括兩方面:一是“設計某種誘發犯罪”的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二是“為實施犯罪提供條件或機會”的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在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151條第一款規定中可以看出,立法者意在禁止偵查人員誘使他人產生犯意,將主觀標準作為合法性的判斷標準。因此在誘惑偵查現為法律所承認的情況下,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手段是具有違法性,觀點三存在錯誤。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對誘惑偵查的合理解釋應是:偵查機關工作人員或國家追訴機關工作人員或偵查機關委派、協助人員,為查明案情,在擁有一定的犯罪證據和線索時,誘使已有犯罪傾向的偵查對象,暴露其犯罪意圖,在偵查人員控制下明顯地實施犯罪行為,在犯罪行為實施過程中,抓住時機逮捕嫌疑人的特殊偵查手段。
(二)誘惑偵查分類
學術界普遍用二分法將誘惑偵查區分為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和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指特意設計某種誘發犯罪的情境,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指根據犯罪活動的傾向提供其實施犯罪的條件和機會。
理論界普遍認為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不合理,其理由在上述概念評述中已提及,此處不再贅述。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通常承認其合理性。從實體法的角度看,因提供機會型誘惑偵查而被拘捕的犯罪分子,在誘惑偵查手段實施前已有犯罪行為,即使單看被誘惑之犯罪,其主動權也是掌握在犯罪分子手中,他可以以其自由意志決定是否進行犯罪行為和以什么樣的方式實施犯罪行為,誘惑者的參與在整個案件中不起主導作用,而僅是提供有利機會。從程序法角度看,提供機會型誘惑偵查一般大多是尋找犯罪嫌疑人的過程,基本上都是以確定的犯罪線索和特定的犯罪嫌疑目標為開始偵查的必備條件,即先有案件的發生,然后通過立案啟動偵查程序,所以偵查活動的進行仍遵循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三)誘惑偵查合法性的研究價值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各國對誘惑偵查的合法化認定都遭受著此類偵查手段是否正當合理的社會質疑。持否定觀點者認為,依賴于誘惑偵查的手段實質是一種欺騙行為,是損害社會信任度、降低偵查機關執法公信力的誘因,更是道德滑坡的公權力導火索。此處應將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和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分開討論。
1、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
在誘惑偵査過程中,偵查人員為偵破案件,會為被偵查對象設定特定的情境、提供犯罪機會,從實體法角度講,偵查人員也成為了犯罪的直接或間接參與者,若在司法實踐中,只追究被偵查對象的刑事責任而對偵查人員的刑事責任忽略不計,這對群眾實屬不公平,這是公權力對法律明知故犯的失當。
另一方面,從人性的弱點來說,,在一定的誘惑面前,任何人的意志都有可能產生動搖,產生沖動感,進而實施不恰當的行為。我們應允許或者相信任何人能夠通過自律加以改正。相反,如果利用人性的弱點而使其實施本來不會實施的犯罪,這就等同于引誘無辜的人去實施犯罪行為。因此,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無異于對被誘惑人員進行人格測試,若將此發揮及至,我們的社會可能成為一個膽戰心驚的社會。因此,否定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是有道理的。
2、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主動打擊、預防犯罪是警察的天職,而刑罰是懲治犯罪的應有之義,在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中,警察作為人民利益的捍衛者、維護國家正常運轉的代表力量,毋庸置疑不需要對偵查中的案件負有刑事責任。
其次,對于一些對毒品犯罪、白領犯罪、有組織犯罪和高智商犯罪案件等當下新形勢的隱性或無被害人犯罪,如果僅僅采用常規偵查手段確實難以奏效。在追懲犯罪的社會壓力下,完全忽視誘惑偵查的積極作用似乎過于片面。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是打擊隱藏性強的重大刑事案件的重要手段,其定性并不能認為是制造犯罪,否認其合法性、正當性,是與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不同的。
2 誘惑偵查的合法性之立法體現
(一)誘惑偵查的合法性立法現狀
在我國由于受實體正義訴訟價值觀念的影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只作了相當籠統的規定:如“偵查機關為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使用秘密的偵查手段”。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紀要通知》,對涉及到誘惑偵查的犯意引誘與犯罪數量、特情所獲證據的效力、特情介入的案件等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其適用范圍只限于毒品犯罪案件。公安部2012年發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62條規定,隱匿身份實施偵查時,不得使用促使他人產生犯罪意圖的方法誘使他人犯罪。
2012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151條第一款規定“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但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
(二)誘惑偵查的合法性立法中存在的問題
誘惑偵查可謂自古有之,但其擴大適用的趨勢,因偵查機關為應對隱形犯罪猖獗的趨勢,因此擴大其使用范圍。在司法實踐中日趨常態化的手段,其在立法上尋求合理正當性之路卻進程緩慢。2012年刑事訴訟法新增的第151條規定,看似對誘惑偵查進行了合法化授權,但法律規定仍顯模糊,誘惑偵查到底有無法律上的明文依據仍然存疑。誘惑偵査的合法界限、適用程序等法治化核心要素是否具備,也需要進一步通過解釋法律來加以明確。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看,2012年修改刑事訴訟法前后,針對誘惑偵查的司法審査普遍存在判斷標準不當、推理判斷方法欠缺的弊端。除了片面地提出“犯意引誘”與“機會提供”兩個概念外,司法人員對誘惑偵查的審核控制再無其他明確、可操作的憑據,司法失范狀態十分嚴重。立法缺位以及如今的立法規定模糊、司法處斷原則與判斷標準的失范,必然導致偵査執法實踐的無序:誘惑偵查手段的運用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在破案考核的壓力下設置圈套、炮制犯罪的濫用案例時有發生,這些都嚴重威脅著公正審判的實現與刑事司法體系的聲譽和公信力。基于此,全面檢視、分析誘惑偵查運用中存在的問題,分析這些問題的制度性緣由,就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該款首先將使用誘惑偵查手段限制在“必要的時候”,但未對何為“必要的時候”進行解釋;其次,對使用“誘惑偵查”的批準還是規定為“公安機關負責人”,這表明今后這種手段的使用還是內部人的監督,而實踐證明,由內部人進行監督,手段是乏力的,更無法監督官員。
刑事訴訟法第151條對于誘惑偵査可以適用的案件范圍以及審批、適用時限、監督等程序控制機制的規定比較簡單、初步。條文本身僅僅要求“為了查明案件,在必要的時候”即可采取誘惑偵查,批準主體則為“公安機關負責人”。與另外一類秘密偵査手段—技術偵査的條文相比,立法者對誘惑偵查的授權更為寬松,既不需要針對“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也不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
(三)立法建議
2012年修改刑事訴訟法過程中增加的第151條第1款,可以看作是誘惑偵査邁向法治軌道的開端。由于法律文本表述的寬泛與模糊,理論界與實務界亟需綜合運用各種解釋方法,對誘惑偵査的合法性判斷標準、適用對象、程序控制機制、法律后果等進行填補與完善,以真正達成授權加規制的雙重立法目的。
在適用范圍而言,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第151條第1款“査明案情”、“必要的時候”首先應當限于“采取其他偵査手段難以獲取犯罪證據”的案件。基于誘惑偵查擴張適用所針對的主要犯罪類型,其所適用的案件范圍應當限于交易型犯罪。這里的“交易型”是指犯罪人之間存在廣義上的利益交換關系,而不僅限于毒品、走私、文物倒賣犯罪等犯罪類型,還包括賄賂、國家秘密與國家安全類犯罪等。
就誘惑偵査法治化的規范形式而言,刑事訴訟法及其立法、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固然重要,但同時應當與司法判例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全面、細致規制誘惑偵查的任務。特別是誘惑偵查的合法性判斷標準及其適用,主要依賴司法判例的規范與指導,才能應對千差萬別、因案而異的引誘手法所引發的規制難題。
就誘惑偵查法治化的規范內容而言,合法性判斷標準是核心問題。現有的“犯意引誘”與“機會提供”二分的通說值得深人反思,其不僅邏輯上難以自洽,規范效果上也存在重大疏漏。這種二分法說到底僅僅關注了主觀意圖,采取了主觀標準的立場,而嚴重忽視了客觀方面偵査人員引誘手法的限度問題,拘泥于主觀意圖的證明這一難題,導致在實務運用中困難重重。筆者主張采用法治發達國家采用的分離式混合標準,即違反主觀標準或客觀標準其中之一,誘惑偵查即應當被判定為違法。這一標準是最嚴厲的合法性控制標準,在當前我國高度單向、集中的偵查權配置背景下,更符合法治精神;畢竟在我國對常規偵查方式的法治化與對秘密偵查方式的法治化,需要同步進行。
參考文獻
[1]龍宗智.上帝怎樣審判[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211-212.
[2]劉國清,劉晶.刑事證據規則實務[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71.
[3]吳宏耀.論我國誘餌偵查制度的立法構建[J].人民檢察,2001,(2):12.
[4]魏東.論誘惑偵查“有限適用”理論及其借鑒[J].四川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1):40.
[5]曹堅.在合理性與合法性之間:誘惑偵查的實踐困惑與理論出路.[J].北京人民警官學院學報,2004,(1):35.
[6]程雷.論誘惑偵查的程序控制[J].法學研究,2015,(1):154.
[7]吳丹紅、孫孝福.論誘惑偵查[J].法商研究,2001,(4):26.
[8]劉善春、畢玉謙、鄭旭:訴訟證據規則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216-217
[9]馬滔:誘惑偵查之合法性分析.[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0,(5):71
[10]熊秋紅:《秘密偵査之法治化》.[J].中外法學,2007,(2),143
[11]參見刑事訴訟法第148條對技術偵査措施適用范圍與批準手續的規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54條、第256條則分別進一步限制了技術偵査措施的適用案件范圍,明確了需經地市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方可適用技術偵查措施。但該解釋對誘惑偵查的適用范圍與審批程序,則基本上照抄了刑事訴訟法的寬泛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