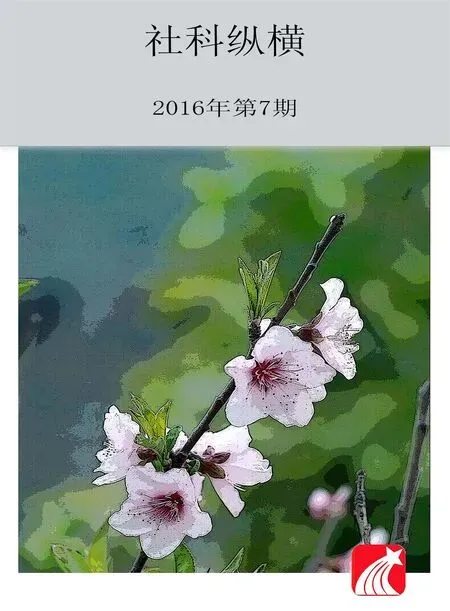基層政府主導農村法治發展面臨的困境
——基于湖南益陽15個鄉鎮的調查與思考
宋義云
(益陽廣播電視大學 湖南 益陽 413000)
基層政府主導農村法治發展面臨的困境
——基于湖南益陽15個鄉鎮的調查與思考
宋義云
(益陽廣播電視大學湖南益陽413000)
作為國家最基層政權的鄉鎮政府是農村法治發展的主導者,其主導法治之難不僅在于立法的缺陷與執法的尷尬,更在于要在一個有著濃厚倫理文化傳統的特定地域植入現代法治化治理機制,改變沿襲了幾千年的鄉村治理傳統。基層政府主導農村法治發展面臨的困境主要有:基層法治生態不健康,政府行政的法治化程度偏低;基層政府行政的法律權威面臨多重挑戰;基層政府行政與村民自治的沖突長期存在;基層干部的行政理念尚未完成法治化轉型。
基層政府主導農村法治困境
農村法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大背景下推進農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內容。作為國家最基層政權的鄉鎮政府是農村法治氛圍的營造著、農村基層矛盾的協調者、農村法治發展的主導者[1],其主導法治之難不僅在于立法的缺陷與執法的困惑,更在于要在一個有著濃厚倫理文化傳統的特定地域植入現代法治化治理機制,改變沿襲了幾千年的鄉村治理模式,改變農民祖祖輩輩傳承的思維定勢。自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我們深入湖南益陽的15個鄉鎮、20個行政村,采取問卷調查、個別走訪和與鄉(鎮)村干部座談的形式,深入了解目前農村法治發展現狀,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綜合分析,試圖了解基層政府推進農村法治發展面臨的困境,以探究破解路徑。
一、基層法治生態不健康,政府行政的法治化程度偏低
自黨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國方略以來,國家從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個維度全面推進法治發展,整體而言,法治建設成績斐然,但國家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總體體現為從中央到地方逐漸降低的態勢,高層的嚴格依法與基層的“靈活”用法同時并存,政府行政的法治化程度明顯偏低。
(一)基層政府的職能轉變尚未完成
按照職權法定的原則,鄉鎮職權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規定,從公民權利保障到執行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鄉鎮行使一級政府的所有職能。在我們走訪的22位鄉鎮主要領導干部中,有16人表示,鄉鎮最“頭痛”的是該條第七款“辦理上級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占72.7%。他們表示,作為基層政府和基層干部,自然應該服從上級的領導,但“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誰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其他事項”,各個部門都為鄉鎮劃分任務指標,總感覺有“完不成的任務交不完的差”。從宏觀環境和發展趨勢而言,要建構“小政府,大社會”的框架,而事實上,今天鄉村發生的所有事情、所有矛盾、所有任務,大至鄉鎮規劃,小至村民鄰里間雞毛蒜皮的小糾紛,都歸集到了鄉鎮政府,今天的鄉鎮仍然是一個“全能政府”而非“有限政府”,政府很難集中精力定規劃、謀發展。
(二)立法缺陷使基層行政面臨困境
鄉鎮政府是國家與農民群眾聯系的銜接樞紐,推動鄉鎮政府依法行政,是鄉村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基礎。自《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頒布以來,各級政府扎實推進依法行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總體而言,市縣以上政府推進依法行政的成效較明顯,而鄉鎮政府行政卻舉步維艱。
法治化治理的前提是有良好的法律。要求基層行政主體按照法定的權限和程序行政,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嚴格依法履行法定職責,就必須對其職權、職責和行為程序作出明確的法律規定。目前我國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時期,法律的“立、改、廢”略顯滯后,在客觀上造成了個別領域的法律空白或法律沖突。另外,分散在各個法律法規中的行政程序性規范,使得執法者不容易掌握執法程序,更使得老百姓無所適從。在我們的調查中,63.6%的鄉鎮執法人員表示,盡管法律規定了某些執法程序,但程序過于繁瑣,很少完整地按程序執法,基層行政程序的法治化程度普遍較低。事實上,在個別領域,法律程序的規定并未關注農村實際情況,農村的很多矛盾有別于城市,糾紛處理方式也有較大差別,基于城市考量的立法可能在農村會“水土不服”。農村執法在時間、空間上不同于城市,加之執法力量較弱,依傳統方式執法仍然較多。個別鄉鎮制定了一些內部程序,但由于缺乏正確的理念指導,這種內部行政程序中片面強調執法中的證據收集,相對忽視行政相對人權利,容易導致權力濫用。
傳統立法對農民權益保護不夠,法律缺乏親和力。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原有的封閉性被打破,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但農村立法卻相對滯后。傳統的農業、農村法律法規主要功能是實現國家、政府的意圖,注重規定農民對政府必須承擔的義務,農民的利益和權利在這些法律法規中往往被忽視甚至排斥。正因為農民在這些法律法規中感受不到利益,對其缺乏親近感,沒有用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基層政府主導鄉村法治建設缺乏共鳴,往往事與愿違。
個別現代農業法律法規則以超前意識引領農村城市化、農業產業化,卻也帶來了認同危機。在我們的調查中,95%的鄉村干部和92%的群眾對《土地承包法》中三十年不變的期限,即“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規定作出了否定性的評價。鄉村干部認為,承包土地的長期不變盡管對賦予農民財產權利給予了法律上的保障,但引發了太多的矛盾糾紛,依法調處很難讓當事人滿意。村民認為,以前集體承包田地調整頻繁,盡管麻煩,但是很公平,而現在,一部分家庭“人多地少”,另外一部分家庭“人少地多”,對新出生人口和新遷入人口實質是一種人為的排斥,這部分人的集體觀念明顯淡化。
二、基層政府行政的法律權威面臨多重挑戰
宗法傳統和宗族文化阻礙鄉村治理法治化。今天的農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傳統中國的縮影,在半開放性的農村社會,農民習慣性地運用沿襲的倫理規則調處矛盾,法律被視為執政者的“專利”,在農民的視野中,法律的觀念與現代法律原則完全不同,更多的是諸如權力本位、義務本位的觀念、宗法倫理觀念、等級觀念等。正如鄧小平曾指出的:“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較多,民主法制的傳統較少。”[2]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改革在農村的展開,農村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自主經營代替高度集權的集體經濟形式,使原來農村社會的組織功能減弱,此時,在農村曾一度減弱的宗法家族文化又迅速膨脹起來,并向社會各個領域滲透。基于血緣存在的宗法傳統和宗族文化使今天的農村社會仍然是一個熟人或者“辦熟人”社會,濃厚的宗親文化對基層政府推進現代法治構成嚴重威脅。對此,費孝通先生曾指出:“在這種社會中,一切普通的標準并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與自己什么關系之后,才能決定拿出什么標準來。”[3]
法律授權不夠,鄉鎮權小責大。鄉鎮政府作為依法行政的主體承擔著較多的責任與義務,而法律授予的權力明顯偏少,鄉鎮政府不可能真正實現完整意義上的“依法”行政。目前鄉鎮政府的工作主要有如下幾項:招商引資;辦理上級人民政府及各部門交辦的事項;組織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組織或協助行政村跑項目;處理上訪事件和突發事件,保證農村社會的穩定與和諧。事實上,國家法律的賦權一般只涉及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鄉鎮并非法律上的執法主體,更多的是委托執法,很不規范。實踐中,70%以上的鄉鎮工作都圍繞上級黨委政府或各部門的要求開展,行政依據主要是上級政府的文件。當文件與法律相沖突時,鄉鎮既不敢違背法律,更不能抵制文件,很多情況下不得不選擇規避法律。
三、基層政府行政與村民自治的沖突長期存在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條和第4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項。”[4]可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的鄉(鎮)與村民委員會關系是一種非強制性的指導和被指導關系,而非行政上的領導關系。
村民自治的實踐與制度設計存在差距,更多的僅僅是停留在法律文本的層面,鄉村關系陷入兩重困境:一方面,村民特別是以村干部為代表的村內精英要求落實法律規定的村民自治權;另一方面,基層政府為完成上級交辦的工作任務和維護地方穩定而不得不對村委會加以控制。基層政府總是力圖通過各種途徑實現對村民委員會的行政領導,把村民委員會變成基層人民政府的下級行政組織。我們的調查顯示,就認識而言,所有鄉鎮領導干部都知曉“鄉鎮不能干涉依法屬于村民自治的事項”,90.9%的鄉鎮領導干部認為“鄉鎮與村之間是指導關系,而不是領導關系”;58.3%的村干部不認為“鄉鎮不能干涉依法屬于村民自治的事項”,63.3%的村干部認為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可見。鄉鎮領導干部基于村民自治的政策、法律水平明顯高于村干部,村干部對鄉村關系的認識較多地沿襲了傳統觀念,服從意愿明顯。但是,在村民自治的實際運行中,出現了與觀念認識上的明顯背離,100%的鄉鎮領導表示,政府必須想方設法控制和領導村級組織,否則工作很難推進,諸多考核都無法完成,甚至公共設施建設都將無法推進,這些控制措施包括資金、項目、補貼名額等。另外,鄉鎮主要領導與村干部的“私人”關系成為了當前農村治理中極為重要的因素,鄉鎮的許多工作都需要村委會支持、配合,而事實上鄉鎮缺乏強制措施,這些工作的推進在很大程度上與鄉村干部間的關系融洽與否相聯系。
在現行政治體制框架下,作為基礎性的國家政權力量,基層政府除了“上傳下達”,還不得不完成來自上級政府的各種任務。與此同時,隨著農村開放性擴大,利益日趨多元化,農民的民主意識不斷強化,他們強烈要求重新界定國家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合理邊界,要求政府行為的規范化、理性化、透明化。這就使得基層政府行為很有可能要受到來自上級政府和農村社會兩方面的非難,這除了其自身存在的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鄉政府處于“鄉村自治”與“壓力型體制”①兩個不同的治理背景下。民主化的村民自治實踐與集權化的“壓力型體制”最終都指向基層,各種責難和矛盾匯聚于基層政府,政治權威時常面臨威脅。
四、基層干部的行政理念尚未完成法治化轉型
(一)基層干部的法治思維尚未形成
由“人治”向“法治”轉型、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是政府革命的一個重要載體。長期以來,基層干部觀念中積淀的控制、管理理念片面強調維護鄉村秩序和苛求農民承擔義務,行政的恣意和任性彰顯無遺,相對忽視了農民權利,弱化了政府服務職能,造成政府行政的越位、錯位、缺位。農村法治發展最基本的要求是基層干部能運用法治思維看待和處理農村社會發生的各種矛盾和糾紛。
基層政府工作人員的觀念和能力尚未完成法治轉型。在實施行政管理過程中,一些人沒有搞清楚依法行政與維護群眾利益的關系,把依法行政與依法治民等同起來,認為法律法規就是管“民”的,依法行政就是單純對“民”進行管理。[5]基層干部在農村治理過程中,面臨外部和內部雙重壓力,以“不出事”并能完成各種任務為邏輯起點,為實現農村基層穩定,往往采用各種“可能”的方式解決矛盾糾紛,即使處置方式缺乏的合法性,只要未“出事”,也無可厚非。在筆者對鄉鎮領導的走訪中,68.2%的人表示,農村治理過程中,依法處理矛盾糾紛應該是首先要考慮并堅持的原則性問題,但是工作實踐中,他們往往不得不放棄法治方式,因為傳統處置方式可能更適應農村社會發生的某些情況。
(二)基層政府運用法治方式處理糾紛尚未常態化
自服務型政府建設提出以來,益陽各級黨政機關堅持執政為民,著力轉變觀念,市縣一級的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穩步推進,但在鄉鎮一級,根深蒂固的傳統行政理念很難在短時間內消除,行政的手段、“靈活”的執法時常顯現,基層干部運用法治手段和法治方式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的能力仍有待提高。政府要樹立自身的威信,就必須重新審視其與社會、與市場、與企業、與農民的關系,必須用公共服務的理念重塑政府,實現治理理念、方式、方法的革新。而在今天農村法治化治理的過程中,最基礎的是要通過轉變理念更多地將傳統行政管理方式轉變為依法治理方式,其目標是讓法治應成為農村治理最基本的方式。
注釋:
①壓力型體制是指在中國政治體系中,地方政府為了加快本地社會經濟發展、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命令任務而構建的一套把行政命令與物質刺激結合起來的機制組合。
[1]宋義云.基層政府在農村法治發展中的定位[J].管理觀察,2016.01.
[2]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Z].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5]魏繼華.農村基層政府依法行政問題探析[J].甘肅政法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7(06).
D920.0
A
1007-9106(2016)07-0055-04
*本文為湖南廣播電視大學重點課題“基層政府主導農村法治發展的困境與對策”研究成果,課題編號:XDK2014—A—7。
*
宋義云(1975—),女,益陽廣播電視大學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農村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