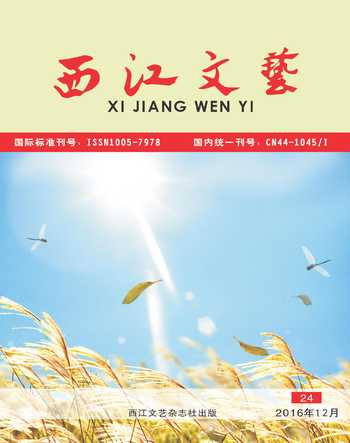阿赫瑪托娃的故土情結
田慧梓
【摘要】:阿赫瑪托娃作為俄羅斯二十世紀詩壇的代表人物,一生飽受磨難,苦難磨煉并賦予了她獨特的才華與感悟。其創作生涯中雖以愛情詩最為人稱道。然而她創作的愛國詩,同樣感情豐富、耐人尋味。其中故土及泥土衍生出的意向大量充斥于阿赫瑪托娃的愛國詩之中,承載著詩人對祖國熾熱、深沉的愛。本文選取詩歌《故土》進行解析,探究阿赫瑪托娃的故土情結以及其獨特的藝術手法。
【關鍵詞】:俄羅斯詩歌;故土情結;愛國情懷
阿赫瑪托娃——阿克梅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可謂是20世紀俄羅斯詩壇的一顆璀璨明星,其第一本詩集的出版便為她贏得盛譽。阿赫瑪托娃以獨特的女性視角,描繪了女性命運所觸及的諸多方面,抒情女主人公不為生活的瑣事所擾,卻又實實在在是生活化的女性。這樣獨特的創作特色使其飽負盛名,成為自己時代女性的最強音。茨維塔耶娃曾稱贊阿赫瑪托娃為“全俄羅斯才情卓越的安娜”,布羅茨基則說她是“哀泣的繆斯”,更有同時代的人認為“勃洛克去世后,俄羅斯詩人的第一把交椅當屬阿赫瑪托娃”。
阿赫瑪托娃原名阿尼婭·戈連科,因父親認為她所進行的詩歌創作會為自己的姓氏蒙羞,而改用了曾祖母——一個韃靼貴族的姓。然而正是這樣一位“才情卓越”的女詩人,一生中卻歷盡坎坷。她的第一任丈夫,同為阿克梅派著名人物的古米廖夫,被誣陷“參與反革命活動”而受逮捕,最終被槍決,阿赫瑪托娃及她與古米廖夫的孩子都因此備受牽連。后來,她的第二任丈夫普寧曾兩度被捕入獄,兒子列夫·古米廖夫也曾三次坐牢,終至流放。然而,生活給這位女詩人帶來的打擊還遠不及此,1946年,阿赫瑪托娃被點名批評是“反動文學的代表”,宣揚“資產階級的唯美主義和頹廢主義”。她甚至被人辱罵為“奔跑在閨房與教堂之間發狂的貴夫人”,“混合著淫聲與禱告的蕩婦和尼姑”。隨后,她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作品遭封殺,也從此失去了創作的權利,只能依靠翻譯外國作品掙取微薄的稿費維持生計。然而,在種種摧殘與打擊之下,有人建議她遠走他鄉,而“哀泣的繆斯”卻多次拒絕離開祖國,離開這片故土,她甚至宣稱“永不生存在異國的天底下,也不茍活在他人的憐憫中”。就是這樣一位意志力非凡、揮灑血與淚書寫自由篇章的女詩人,集生活經歷種種與藝術想象力于創作之中,才會為我們帶來如此獨特的閱讀體驗。
素來以愛情詩著名的阿赫瑪托娃也繼承了俄羅斯詩人歌頌祖國的傳統,其詩中可見泥土及泥土衍生出的“土地”、“墳墓”等一系列意向,作為承載詩人感情的實體,《故土》是其中較有影響力的詩篇。這一作品中出現了兩個日期:1922年和1961年,1922年出現在詩的開頭。1921年,古米廖夫被槍決,阿赫瑪托娃和她的孩子列夫·古米廖夫因被牽連而備受迫害,有人勸她離開俄羅斯,而女詩人毅然決然的拒絕了這一建議,堅決留在故土,其愛國之情可見一斑。面對生活種種打擊與不幸,詩人仍然坦然寫道:“世上沒有人比我們更豁達,沒有人比我們更傲岸、樸質。”這段標題下所引用的詩句來自詩人《拋棄國土,任敵人蹂躪……》這篇作品的最后兩行。而1961年是《故土》完成的時間,此時詩人已近暮年,在列寧格勒的醫院里靠口述創作了這首詩歌。詩人回顧一生,不僅沒有怨恨過去,反而對祖國的熱愛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故土一詞為一語雙關,既指代故鄉的泥土、土地,也指代祖國。詩人著眼于祖國,卻又從泥土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具體意象入手,借此以表達對祖國的真摯之情。阿赫瑪托娃以故土一詞指代祖國,以平凡的意向反映出非尋常的情感,折射出詩人對祖國的珍貴情誼。詩人不去謳歌祖國的遼闊疆域,也不去祖國描繪的悲慘命運,而是從個人的角度,描寫自己心中的故土,抒發了自己對祖國的異樣情感。詩中時常出現各種日常生活的場景和意象,能使讀者產生共鳴,從細節更好地捕捉詩人情感的波動。《故土》是一首形式獨特的莎士比亞式的十四行詩,全詩可分為兩個部分來看,前八行是第一節,為陳述性部分。后六行為第二部分與第一部分相呼應,并對前面的陳述做出回答,其中最后兩句點明全詩主旨。第一部分詩人寫道:
“我們并不把它珍藏在胸前的護身香囊中,
也不聲淚俱下為它賦詩吟誦,
它從不攪亂我們悲苦的夢,
也不像是供我們遨游的天國瓊宮。
在我們的內心深處,
從不把它當作買賣之物,
也不認為它有祛病消災的神通,
即使貧病交困也想不到向它乞靈訴訟。”
在這一部分詩人描繪了“我們”與“它”的關系,但又并沒有交代“它”是什么。兩者的關系看似若即若離,卻又能體會到“它”對于抒情主人公的重要性。這一部分多次運用了否定形式,看似在對“它”進行控訴,實則含蓄的透露出了對“它”的深沉之情。“我們并不把它珍藏在胸前的護身香囊中,也不聲淚俱下為它賦詩吟誦。”“它”之于“我們”十分珍貴,主人公可以把“它”牢記在心,也可以用實際行動去愛護“它”,卻不需故作姿態的情感。“它從不攪亂我們悲苦的夢,也不像是供我們遨游的天國瓊宮”。“它”實實在在存在于“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卻又好似沒有過多交集。“它”從不驚擾“我們”的煩惱,似乎也不能給予“我們”快樂。“它”似乎平凡的“一無是處”,沒有買賣價值,也無法向它有所訴求,但“它”卻是卻無處不在,甚至“我們”也是“它”的一部分。這一部分中許多日常生活中的場景、意向穿插在“它”與“我們”之間。在此,阿赫瑪托娃想縱情謳歌故土的可貴,抒發詩人的強烈情感,卻又十分克制,極言它的平淡,道出了詩人對故土的態度,也為第二部分感情的抒發做了鋪墊。接著詩人寫道:
“是啊,它是粘在我們套鞋上的泥土,
是粘在牙齒上喀擦作響的沙粒。
我們將它踐踏、捻碎、蹂躪,
使它成為塵埃,一無所用。
然而我們都將躺進它的懷里,化作泥土,
所以才把它叫做故土,叫的那么隨便輕松。”
在此,前四句詩對第一部分作出回應,為我們揭示了“它”的真實面目。“它”是備受漠視和踐踏的泥土、沙粒。然而“它”不僅默默承受,不計前嫌地包容一切,還將擁抱“我們”。讓“我們”都將躺入“它”的懷里,成為“它”的一部分。泥土、砂礫都是極為普通的意象,而詩人在這里通過對這一日常意象的刻畫描寫,為讀者揭示了泥土的雙重性:既卑微又博大,既渺小又深沉,既輕賤又厚重。當阿赫瑪托娃遭遇劫難的時候,支撐她的正是這片故土,即使身處困境的她仍拒絕離開祖國。當詩人恢復名譽之時,她滿懷激情的對這片默默包容并擁抱她的土地表達了無盡的感激。最后的兩行正是全詩的主旨所在,突出表現了詩人始終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氣魄,起到升華感情的作用。前面將祖國描寫為一系列微小的意向,最后話鋒一轉,并與第一部分的“控訴”形成對比。然而即便“它”渺小卑微,“它”都將以偉大包容的姿態迎接一切。而“我們”都將落葉歸根,至死眷戀著這一方故土。不禁讓人想起“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這一詩句。無論貧窮亦或富有,不論高貴或是卑微,不管身處故土,還是遠游他鄉。祖國,故土,永遠都是最終的歸屬。
阿赫瑪托娃運用內心獨白的創作方法,并借以普通意向抒發對祖國深沉的情感,這種以小見大的手法不僅容易為讀者接受,更以熟悉的意象和自我獨白使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從而更好的理解詩人所見所感。其作品充分體現了阿克梅派的創作原則與特點,并將外部事物與內心情感完美融合,以質樸精練的語言抒發情懷,在不經意間流露出綿延不絕、感人至深的情思。正是這樣一些優秀的作品,表達了詩人對于祖國超乎尋常的愛與敬意,同時也反映出了作者獨特的美學追求。
參考文獻:
[1]阿格諾索夫,凌建侯等譯,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2]阿赫瑪托娃詩選,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