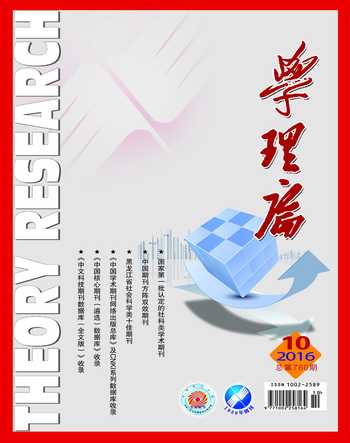梁啟超對權利義務關系的認知與闡釋
梁光晨
摘 要: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最有影響力的政治活動家、文學家、史學家和啟蒙思想家之一。他敏銳地觀察到了中華民族的個體人文素質這一影響中華民族建設現代強盛國家的重要問題,率先提出了新民塑造這一命題。對于如何塑造新民,梁啟超認為,除了健全公德心、確立國家思想,敢于進取冒險之外,最為重要的就是權利與義務觀念的確立。認為要真正保障權利義務的實現,關鍵的制度設計和治理方式是良法善治。梁啟超所倡導的新民塑造,關鍵與核心的內容在于倡導和塑造中華民族國民個體的思想自由。他認為,思想自由,也就是國民個體的思想自由,還應該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使之最終凝結為國家的自由,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整體的自由。
關鍵詞:梁啟超;權利義務關系;認知;闡釋
中圖分類號:K256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10-0154-03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最有影響力的政治活動家、文學家、史學家和啟蒙思想家之一。他一生學術成就斐然,對后世與后人的影響極大。一般人較為重視的是他在文學與史學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服膺于他在這些領域的巨匠地位。但較少有人注意到他從近代法治觀念的角度,對人、社會及國家所進行的探討、分析,特別是所得出的獨特結論,這其實是很不應該的。在清末民初那個特殊的時代,梁啟超曾以飽滿的激情,深邃的眼光,將深刻的思考變成文字,感染和影響了許多人,對近代中國的法治觀念的變革與進步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本文就梁啟超對法治觀念中權利與義務關系的認知與闡釋問題,做一個初步的討論。
一、新民塑造:權利與義務的承載主體
痛心于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落后挨打的現狀,出于“救亡圖存”,追求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崇高目的,許多仁人志士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與努力,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主張。梁啟超則敏銳地觀察到了中華民族的個體人文素質這一影響著中華民族建設現代強盛國家的重要問題,率先提出了新民塑造這一命題。他認為:新民塑造為當時中國的第一急務,再沒有什么問題比這一問題顯得更為重要。他寫道:“吾今欲極言新民的當務之急,其主論之根柢有二,一曰關于內治者,一曰關于外交者”[1]8。關于國家內政,即國家的建設與治理,梁啟超指出:“天下之論政術者多矣,動曰:某甲誤國,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機,某之制度官史之溺職……若是者,吾固不敢謂為非然也。雖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豈非來自民間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國民之一體耶?久矣夫,聚群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以若事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又奚尤?”[1]8也就是說,梁啟超認為,中國國民素質,當然主要是人文素質低下,才造成了出自民間的官吏也無法達到稱職的要求。進而才會出現了這些官吏所組成的政府處置事件時失機,建構具體制度時溺職。在這里,梁啟超在用了三個形象的比喻,哪怕聚集一群聾子,也不能成為一個音樂家;哪怕聚集一群瞎子,也不能成為一個遠望者;哪怕聚集一群膽小鬼,也不能成為一名大力勇士。他認為之所以出現誤國殃民的現象,存在官員失機和溺職這些表現,只是國民個體素質普遍低下所帶來的必然后果。
梁啟超認為,在國民個體素質普遍低下的情況下,一國在對眾多列強的外交領域所面對的問題則更加突出。他針對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指出:“而今天東方大陸,有最大的之國,最腴之壤,最腐敗之政府,最散弱之國民,彼族一旦窺破內情,于是移其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如群蟻之附■,如萬矢之向的。”[1]11他所說的,恰恰是當時中國倍受列強欺凌的悲慘的現實。
就此,中華民族的國民個體人文素質問題,即梁啟超所稱的國民性問題,已經凸顯了出來。他認為,答案其實很簡單:“然則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1]8對于那些不從中華民族的國民個體人文素質,即國民性上去考慮問題的思路,他認為都沒有抓住根本。他是這樣批評的:“無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月易一人,東涂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1]8面對來勢洶洶的外患,梁啟超認為根本的解決辦法只能是:“然則為中國今日計,必非恃一時之賢君相而可以弭亂,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圖成,必其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相埒,則外自不能為患。”[1]12在這里,他提出了徹底消除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外患的唯一途徑就是從根本上塑造四萬萬民德、民智、民力都已經得到了提升的新民。
那么,應當如何塑造新民呢?梁啟超認為,除了健全公德心、確立國家思想,敢于進取冒險之外,最為重要的就是權利與義務觀念的確立。因為新民,即具有近現代人文素質的個體國民,才是權利義務的承載主體。梁啟超指出:“人人對于人而有當盡之責任,人人對于我而有當盡之責任。”[1]71這里講的是社會關系中自我與他人的關系,他突出的是個人應承擔的責任,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義務的歸屬問題。對于權利思想的本原,梁啟超是這樣講的,“藉欲得之,藉欲保之,則權利思想,實為之原。”[1]73對于沒有權利思想的人,他是這樣尖銳評價的:“故無權利思想者,雖謂之麻木不仁,可也。”[1]73對于權利思想的內涵,梁啟超是這樣分析的:“權利思想者,非徒我對于我應盡之義務而已。實亦一私人對于一公群應盡之義務也。”[1]78即權利與義務之間的關聯性就表現形式而言不僅是個人對個人之義務,而且更重要的是個體對群體的義務。在這里,他道出了權利義務觀的真正本質——國民個體對國家所承擔的義務才是享有權利的前提條件。也就是說,具有自覺地對國家承擔義務觀念的國民才能稱為新民。
權利義務觀對于新民如此重要,那又當如何確立并予以保障呢?梁啟超的結論是必須建立健全法律制度體系。他指出:“權利競爭不已,而確立之保障之者厥恃法律。故有權利思想者,必以爭立法權為第一要義……強于權利思想之國民,其法律必屢屢變更,而日進于善。”[1]79也就是說,只有健全的法律體系可以保障權利得到實現。健全法律體系的關鍵在于立法。法律體系還應當與時俱進,以確保權利的實現。
二、國家意識:權利義務的實現前提
梁啟超在探討如何塑造新民時,極為重視對新民進行現代國家意識的培養,他本人一再強調的國家思想,講的就是這個問題。
在解釋什么是現代國家的形成過程時,梁啟超用了兩個推導步驟。第一個步是從文明與野蠻的分界點這一角度去討論,他認為:“人群之初級者,有部民而無國民。由部民而進為國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與國民之異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風俗者,謂之部民;有國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謂之國民。天下未有無國民而可以成國者也。”[1]43第二個步驟是從國民個體對國家的認知角度去探討國家思想,即現代國家意識的形成問題。他認為:“國家思想者何?一曰對于一身而知有國家,二曰對于朝廷而知有國家,三曰對于外族而知有國家,四曰對于世界而知有國家。”[1]43這既是國民個體對國家的四種認知模式,也表征著國家意識的逐步完善過程。對于中華民族國民個體國家意識的缺失,梁啟超感到極為痛心。他指出:“耗矣哀哉!吾中國人之無國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榮瘁是問;其上焉者,則高談哲理以乖實用也。”[1]46梁啟超認為,造成中華民族國民個體的國家意識缺失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國特殊的與外界隔絕的地理因素的先天影響;二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落后成分的后天缺陷。其最終的結果是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度極低。他指出:“吾推其所以必然之故,厥有二端,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一已而不知有國家。”[1]49即國民只知道屬于皇家的天下,只知道屬于自己的私利,唯獨不知道屬于國民共同體的國家。
梁啟超認為,只有基于所有國民個體的國家意識,才能建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而建構起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才能確保權利義務的實現。所以,國家意識才是國民個體權利義務的實現前提。梁啟超對這一個問題是這樣論述的:“國家之立,由于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僅恃一身之不可,而別求彼我相團結、相補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團結永不散,補助永不虧、捍救永不誤,利益永不窮,則必從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發一慮,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其所謂一身以上者。”[1]44也就是說,梁啟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家的成立是迫不得已的。人們之所以要建構國家,其原因就在于人作為單獨的個體,如果不與他人相聯系,則無法實現其權利,甚至無法生存。而單獨個體的個人在互相聯系時,沒有共同信守的規則,沒有作為共同規則守護者的國家存在,人們就不可能實現“相團結、互補助、相捍救、相利益”的目的,個人的權利當然也就無從實現。在這一觀點上,梁啟超明顯借鑒和吸收了西方啟蒙思想家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觀點。
在任何現代國家中,人都不可能只享有權利而不承擔義務。梁啟超認為。提高中華民族國民素質的關鍵并不是從權利的建構及實現路徑著手。應當關注的恰恰是國民個人對國家義務的認知培養。他寫道:“人非父母無自生,非國家無自存,孝于親,忠于國,皆報恩之大義,而非為一姓之家奴走狗所能冒也。”[1]47他還認為:“視諸往,他日全球勢利中心點之所在,那四萬萬忠臣中心點之所在也,而特不知國于此焉者誰與立也。”[1]52這里的勢,是世界大勢;這里的利,是民族之利。四萬萬人一起關注世界大勢,關注民族之利,是他為我們描繪出的中華民族走向國家強盛的美好愿景。為實現這一目標,他大聲疾呼:“吾非敢望我同胞所懷之利己主義劃除凈盡,吾惟望其擴充此主義,鞏固之主義,求如何而后能真利己,如何而后能保己之利使永不失,則非養成國家思想不能為功也。”[1]52在這里,梁啟超的觀點表述得十分清晰:只有國民養成國家意識,確立起對國家的義務觀念,全民協力,實現國家的強盛,才能真正保護和實現自己的權利。這才是根本的前提。
三、良法善治:權利與義務的保障方式
梁啟超認為,要真正保障權利義務的實現,關鍵的制度設計和治理方式是良法善治。他認為:“且中國風俗,他事或不如人,至于規行矩步,繩尺束縛,正中國人受用最慣受病最深之處。”[1]106即中國國民的觀念,固然有許多落后之處,有許多不如別人的地方。但梁啟超認為,法治觀念淡漠,規則意識缺失,才是中華民族國民個體長久以來的真正病根所在。對于法律制度及其延伸出來的法治觀念,規則意識的重要性,梁啟超是這樣論述的:“夫能使其一身起居動作如機器者,正其天君活潑自由之極者也。軍隊之形式專制也,而有其精神焉。一群如一軍隊,其軍隊之將帥,則群中人人之良心所結成的法律是也。故制則制矣,而不可謂之專,以其法律者出自眾人,非出自一人。”[1]106-107在這里,梁啟超不但充分論述了法律對于一個由人所構成的群體,也就是國家的重要性,還直接涉及了良法之治的觀念。的確,只有當法律是由眾人在良知上共同認可并心甘情愿地遵守的良法,善治才能實現。
對他本人目及所至的中國國民,梁啟超是這樣認識的:“今吾中國四萬萬人,皆無法律之人也;群四萬萬無法律之人而能立國。吾未之前聞。然則豈待與西人相遇于硝云彈雨之中,而后知道其勝敗之數也。”[1]108也就是說,當時所有中國國民都是沒有法治觀念,沒有規則意識的人,縱有四萬萬之數,也不可能建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也就不可能抵御并戰勝西方列強的侵略。
梁啟超理想中的良法善治模式應該是,通過徹底的自治來實現法律的作用。他這里所說的自治,更準確地說就是通過良法進行善治。他認為:“國有憲法,國民之自治也;州郡鄉市有議會,地方之自治也。凡善良之政體,未有不從自治來也。”[1]108也就是說,他認為良好的政治秩序、社會秩序,都來源于良好的治理機制。而最良好的治理機制就是徹底的自治。在這一點上,梁啟超的認識明顯要比同時代的其他人高明許多。
梁啟超認為,國民個人權利與義務的實現過程,就是自下而上的社會自治機制的形成、完善并發揮出作用的過程。并且,這一過程事關國民個人的權利、自由與平等。他指出:“而吾民將來能享民權、自由、平等之福與否,能行立憲、議會、分治之制與否,一視其自治力之大小強弱定不定以為差。”[1]109也就是說,他認為中華民族國民自下而上的自治能力的養成,事關國民能否享有民主、自由與平等。為此,他苦口婆心地告誡國人:“吾民乎!吾民乎!勿以此為細碎,勿以此為迂腐,勿徒以之責望諸團體,而先以之責望諸個人。吾試失舉吾身而自治焉。試合身而與身為一小群而自治焉,更合群與群為一大群而自治焉,更合大群與大群為更大之群而自治焉,則一完全高尚之自由國、平等國、獨立國、自主國出焉。而不然者,則自亂而己矣。”[1]109-110在這里,他希望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從自己及身邊的小群體的自我治理做起,并使之逐漸擴展,最終構建一個嶄新的自由、平等、獨立、自主的中國。
四、自由精神:權利與義務的理性結晶
梁啟超所倡導的新民塑造,關鍵與核心的內容在于倡導和塑造中華民族國民個體的思想自由。他認為,思想自由,也就是國民個體的思想自由,還應該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使之最終疑結為國家的自由,以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整體的自由。他認為:“自由之義,適用于今日之中國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適用也。” ? ? ?[1]88
自由對于新民的塑造既然如此重要,那什么才是梁啟超認知的自由呢?他是這樣講的:“自由者,奴隸之對待也。綜觀歐美自由發達史,其所爭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計上之自由。”[1]89即他首先定義了人自由的對立面就是人被其他人奴役,這當然就是非自由。其次,他將人的自由分為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民族自由和生計自由四類。對這四類自由,他是這樣闡釋的:“政治上之自由者,人民對于政府而保其自由也。宗教上之自由者,教徒對于教會而保其自由也。民族上之自由者,本國對于外國而保其自由也。生計上之自由者,資本家與勞動者相互保其自由也。”[1]89他的這種分析,雖然與我們今天對自由的認知相比有些膚淺。但放在當時的語境下,不能不說是大抵是科學而且具有進步意義的。
梁啟超對自由的概念準確內涵也進行了分析。他指出:“自由之界說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入人之自由為界。夫既不許侵人自由,則其不自由亦甚矣。而顧謂此為自由之極則者,何也?自由云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野蠻時代個人之自由勝利,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由減。”[1]93這里,他一方面強調了自由應當在基本內容中包含不侵奪他人自由的內在規定性,指出了自由走向極端反而會導致非自由。同時,他還區分了個人自由和團體自由兩個概念。顯然,他更為推崇和認可的是文明時代的團體的自由。
梁啟超認為,自由是有邊界的。即自由這個概念是可以界定出其準確邊界的。他是這樣分析的:“夫自何以有界;譬之有兩人于此,各務求勝,各務為優者,各擴充已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其力線各向外伸張,伸張不已,則兩線相遇,而兩力各不相下,于是界出焉。故自由之有界也,自人人自由始也。”[2]49也就是說,他認為自由這一概念從產生之日起就有著人們可以辯識的邊界。當個人的自由已經與他人的自由發生沖突時,這時就已經達到了自由的邊界。
梁啟超特別重視反對以自由之名,行破壞自由之實的利己主義行為,并對其進行了堅決的批判。他指出:“今世少年,莫不囂囂。言自由矣、其言之者,因自謂有文明思想矣,曾不審夫泰西之所謂自由者,在前此之諸大問題,無一役非為團體公益計。而決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驁者所可以藏身也。今不用之向上以求憲法,不用之排外以伸國權,而徒耳食一二學說之半面,取便私圖,破壞公德,自返于野蠻之野蠻,有規語之者,猶敢■然抗說曰:‘吾自由、吾自由,吾甚懼乎‘自由二字,不徒為專制黨之口實,而實為中國前途之公敵也。”[1]84-85他要告誡我們的是,借個人自由之名而追求一己之私利,掩飾其破壞公共道德的行為,甚至踐踏他人的應有權利,對中華民族的前途有著莫大的危害性。因此,必須對這類行為予以高度警惕。
五、結語
梁啟超作為中國近代最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之一,第一次提出了新民塑造這一命題。對于塑造新民,他認為最為重要的就是民眾權利與義務觀念的確立。因為新民才能成為權利義務的承載主體。他認為塑造新民的過程就是對民眾進行現代國家意識的培養過程。他認為,要真正保障權利義務的實現,關鍵的制度設計和治理方式就是立良法、行善治。他所倡導的新民塑造,關鍵與核心的內容在于倡導和塑造中華民族國民個體的思想自由。他認為,思想自由,應該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使之最終疑結為國家的自由,以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整體的自由。他的這些觀點,直到今天對我們還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1]梁啟超.新民說.[M].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2]梁啟超.自由書[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