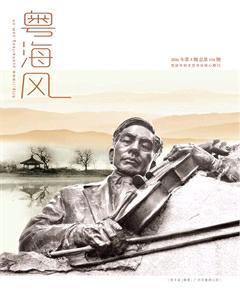章太炎的癡狂瘋癲
胡龍霞
中華上下五千年的各種文字介紹(真假不論)的歷史人物里(只算著名的),學(xué)問大的人成千上萬,影響社會變化的人多如牛毛,學(xué)問大又影響社會變化的人也不少見,癡狂癲瘋的人更比比皆是,可是,癡狂癲瘋的、學(xué)問大的、影響社會變化的人,除了章太炎,或許再也難以尋出第二個。
一百多年來,章太炎的癡狂癲瘋始終為大家津津樂道,都限于介紹他如何罵人、如何行為乖張、如何處事怪誕,對他為什么是這樣則避而不談,偶有所見,也是只言片語,例如:
乃蒙在《章太炎的講學(xué)》一文中寫道:“他是狂傲的人,一切是自私的,以自己為中心的。在演講臺上,他將聽眾幻成一種意象,以為這意象是他的獲得,他的生命之某種關(guān)聯(lián),而這意象是陌生的,于是以眼光,以笑臉,去粘住它,把它位置在某種精神生活上。這里,我仿佛看見章先生心靈的凄獨!”(1936年8月《宇宙風(fēng)》)
章門弟子陳存仁在《閱世品人錄》里說:“他壯年時富于革命精神,激烈的言論,被人家當(dāng)做瘋子是可能的”,“晚年時,對世俗看不慣,或者寫一篇憤世嫉俗的文章是有的,寫一副蓋棺定論坦直的挽聯(lián)也是有的,說他是瘋子,實在不是瘋,不過有些文人的狂放豪氣”。 “說章師狀似神神經(jīng)經(jīng)是可以的,說他患過羊癇風(fēng)則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幼時即使有羊癇風(fēng)的話,也與成年后的腦神經(jīng)沒有關(guān)系。”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dāng)屬2010年10月19日的百家講壇臺詞《為政治而狂為國家而癲的章太炎》里面的一句話:“其喜怒莫測,好惡多變,確實讓人看不懂。”
有鑒于此,本文分:起居癡呆、文章狂傲、言行瘋癲,對章太炎癡狂癲瘋的原因進行初步探討。
起居癡呆
章太炎起居癡呆的故事很多,諸如章太炎經(jīng)常不知道自己家地址、給弟子5元去買一包香煙也給女兒5元去買一棟房子、不講衛(wèi)生隨地吐痰、不洗澡、不修指甲、一年四季只穿固定幾套衣服、只知道蒸蛋糕和蒸火腿兩道菜名、難分皮鞋左右而堅決不穿、衣袖常常沾滿口水鼻涕、吃相讓同桌難以下咽、買套不值1萬的房開價1.5萬他還價成1.7萬、爬上演講臺不走臺階……其起居癡呆之狀,常令人哭笑不得,不一一列舉。
那么,章太炎為什么起居癡呆到如此不堪?
我們都知道,人的大腦功能相當(dāng)強大,同時,也有相當(dāng)大的限度。一個人的大腦無論多么發(fā)達(dá),受時間限制,不可能同時思考兩個及其以上的問題,而人的活動是靠大腦指揮的,也使得一個人不可能同時從事兩項及以上的活動,加之人一生的時間相對固定,一個人將這個時間用在了這個事情上,那個事情就要么用那個時間去處理,要么,耽擱掉。
章太炎的大腦相比其他人,顯然是屬于相當(dāng)發(fā)達(dá)的一個,可無論多么發(fā)達(dá),還是人的大腦,還是得受時間的限制,也不可能在同一個時間思考、處理兩個及其以上的問題。
問題是,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的大腦注意力首先是放在自己的感受、欲望、愿望方面,普羅大眾就不用說了,絕大多數(shù)大學(xué)者、大文豪,特別是大富翁、大官僚等大人物,他們說起來也許只為民眾著想,只為大家奔波,其實,他們也一樣首先是滿足自己的感受、欲望、需求,也就是想吃什么穿什么想要什么之類,因此,對住得這樣,怎樣出行,是否安全、衛(wèi)生、體面之類心里清楚得很,即使這些小事有專人為之服務(wù)、打理,一旦吃的東西不可口、坐的睡的感到不舒服,穿的讓人笑話,就會給人臉色看,甚至大發(fā)雷霆,所以,斷斷不至于忘記自己家住哪里,斷斷不至于不清楚自己喜歡吃什么穿什么。
章太炎顯然不是將日常起居放在第一位的人,特別是30歲以后,日常起居就不是放不放在第一位的問題,而是他完全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注意日常起居。
章太炎出生的時候,他家僅田地就有700多畝,這要是放在今天就是我們所說的土豪之家,他父親、兄長還都是公務(wù)員,父親任余杭縣學(xué)訓(xùn)導(dǎo),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縣教育局官員,兩兄長也都是教育官員,三份薪水加上700畝田地的收入,章太炎家顯然是當(dāng)?shù)卮髴簟.?dāng)然不是富可敵國那種,一家人卻足以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絕不用為生計而擔(dān)憂。所以,章太炎自小就不用自己考慮日常起居,吃什么穿什么顯然都有人細(xì)心照料,自己只管玩兒就是了。普通人家的孩子,即便不算貧窮的人家,從小就得惦記吃的穿的玩的,即使長大后成為巨富高官大學(xué)者,這些起居問題有人照顧,自己也不會掉以輕心。章太炎這種家庭的孩子就不同了,小時候不用惦記吃穿,甚至比較排斥,不想吃的時候大人要喂給吃,不想穿的時候大人要強迫穿,搞得人很煩,偶爾故意同大人唱反調(diào)也不奇怪。
9歲以后的章太炎由外祖父專門開館教授,一教4年,這架勢與普通人家的孩子就不同了,外祖父著有《讀書隨筆》《雙桂軒集》,放現(xiàn)在也是大學(xué)教授級別的人物,最不濟也是中學(xué)校長,專門開館教授一個孩子,顯然是當(dāng)作未來的大人物培養(yǎng),章太炎說自己“課讀四年,稍知經(jīng)訓(xùn)”。也知道了許多歷史人物、故事,到13歲的時候,實際上可以說到16歲之前,章太炎雖然也圍繞科舉范圍閱讀、學(xué)習(xí),但一定比同年的人讀書多很多,知道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也多很多。而且,可以認(rèn)定,這期間的章太炎還是同小時候一樣,用不著自己考慮衣食住行,只管讀書、思考、記憶就行了,最多也就是讀書、聽課之余自己玩兒。從他自己回憶的讀書單就可以看出,這時候的章太炎,其閱讀范圍已經(jīng)相當(dāng)于時下的文學(xué)、史學(xué)碩士,甚至超出,比如,時下的文學(xué)、史學(xué)博士也不一定讀過顧炎武的《音學(xué)五書》、王引之的《經(jīng)義述聞》、郝懿行的《爾雅義疏》、阮元的《學(xué)海堂經(jīng)解》及續(xù)編,包括許多博導(dǎo)也不定就讀過,讀過也不一定讀得懂,但章太炎16歲時已經(jīng)將它們讀得比較熟,僅僅這一點,就足以說明章太炎并非尋常人物,不僅大腦功能強大到少有人可比,其自幼所受的經(jīng)義原理熏陶也非一般專家學(xué)者能夠匹敵。
章太炎16歲的時候成功躲過科舉考試,這次躲避科舉考試行為本身也證明章太炎異于常人,常人對科舉考試無外乎恐懼、敬畏、崇拜交加,它涉及一個人的貧富、榮辱問題,不可小覷,但在章太炎眼里,它形同兒戲。我們現(xiàn)在難以找到確切說法,一說是癲癇突發(fā),一說是他大放厥詞,無論是沒有參加考試還是考試時候搗亂,總之是章太炎無意科舉。若按照他家在當(dāng)?shù)氐穆曂貏e是他的學(xué)識功底和文章才華,只要考試就可能被錄取,即使真是癲癇突發(fā),家人也當(dāng)會逼迫他繼續(xù)應(yīng)考,可他顯然以夸張的行為表示了自己的決心,使得父親默許了他的決定,同意他從此在家自學(xué),不再科舉。到23歲進入詁經(jīng)精舍, 7年時間專事經(jīng)學(xué)。不用像常人一樣將注意力放到所謂功名方面,只用將自己的注意力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上。這樣,章太炎16歲后其注意力就轉(zhuǎn)到了學(xué)術(shù)方面,并且主要不是學(xué)習(xí)別人的學(xué)術(shù),而是在學(xué)習(xí)的同時,形成自己的學(xué)術(shù)創(chuàng)造,通俗地說,形成自己獨到的見解。這一點,從他日后的一生言行中都可以找到足夠的證據(jù)。
由于章太炎所在的社會環(huán)境,他不可能像愛迪生、比爾·蓋茨、達(dá)爾文等人一樣,從事個人性的發(fā)明、發(fā)現(xiàn)、創(chuàng)造事業(yè),只能沿襲幾千年來的中國人唯一知道也唯一能做的事,那就是經(jīng)義解釋或社會(現(xiàn)象、國家大計之類)解讀,大多數(shù)智慧超群、見識深廣的中國學(xué)者、文人、社會活動家從事其中一項已經(jīng)非常厲害了,章太炎則把兩項都當(dāng)成自己一生從事的事業(yè),前面說過,時間對于任何人的大腦功能都有限定,章太炎要同時進行經(jīng)義解釋和社會解讀,加上當(dāng)時的中國社會非常復(fù)雜,那么,他的時間和注意力就只能全部投放進去,至于日常生活,就徹底沒有了時間和注意力,于是,他就只能表現(xiàn)為起居癡呆了,何況,他多數(shù)時間也用不著自己處理日常生活方面的事情。
說通俗一點,章太炎就是個只思考自身以外的事情的人,自身的必備的日常生活也不在他的思考范圍。可是,衣食住行又是每天都必然發(fā)生的事情,于是,他就常常笑話百出。
文章狂傲
1900年8月,章太炎將《解發(fā)辮說》《請嚴(yán)據(jù)滿蒙人入國會狀》兩稿寄給當(dāng)時的香港《中國旬報》,總編陳少白刊登時加上評語: “霹靂半天,壯者失色。長槍大戟,一往無前。有清以來,文字之痛,當(dāng)推此為第一。”這并非章太炎的文章第一次得到“狂烈”的贊賞。
章太炎走出校門的第一份工是《時務(wù)報》撰述,那是1897年,章太炎28歲,到職第一個月就發(fā)了兩篇時政文章:《論亞洲宜為唇齒》《論學(xué)會有大益于黃人亟宜保護》。雖然章太炎在詁經(jīng)精舍書院的時候就已經(jīng)寫有《膏蘭室札記》《春秋左傳讀》兩個書稿,那時候還沒正式出版,社會上也就并不知道章太炎的學(xué)問如何。《時務(wù)報》上的兩篇文章是公開發(fā)行的,盡管觀點新穎,但文辭比較古奧,加上章太炎的名字初現(xiàn)報端,也就并沒有產(chǎn)生多大的反響。不過,兩篇文章都是直接針對當(dāng)時的朝廷政策,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章太炎的文章風(fēng)格,特別是,中國社會歷來推崇背書、歌唱文章,只要是與朝廷唱反調(diào)的文章,沒什么反響還好,若有一定反響,那就非常危險。《時務(wù)報》內(nèi)部就為章太炎的文章感到心驚膽戰(zhàn),加上章太炎不善看人眼色,被勸告的時候還打了主編梁啟超一耳光,自己也被康門弟子一頓好揍,任職才一個多月,章太炎只能收拾行李走人。好在,他的文章已經(jīng)在報界有所認(rèn)識。
離開《時務(wù)報》后的大半年時間里,章太炎先后加盟了《經(jīng)世報》《實學(xué)報》《譯書公會報》,發(fā)表了《變法箴言》、《讀〈管子〉書后》、《后圣》、《儒道》系列、《異術(shù)》等十多篇時政文章,這些文章不僅表現(xiàn)出章太炎見解獨到、用語尖刻、文辭精美的特點,也讓章太炎在報界、學(xué)界、政界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大家都對他的文章功夫刮目相看。比如,他在文章中提出的“以消費實現(xiàn)生產(chǎn)”“諸學(xué)并存”等認(rèn)識,與朝廷、主流的提倡節(jié)儉、獨尊儒術(shù)等唱反調(diào),卻是真知灼見,讓許多人感同身受,倍感痛快。
1898年8月,章太炎出任《昌言報》筆政,大約相當(dāng)于時下的編輯部主任,當(dāng)戊戌六君子血濺菜市口的消息傳到上海,章太炎憤怒了,寫成《書漢以來革政之獄》《蒙古盛衰論》《回教盛衰論》。篇篇針對滿清政權(quán),字字直指朝廷暴政。這時候,章太炎的文章之狂傲終于引起朝廷注意,他第一次當(dāng)上了朝廷通緝犯。盡管章太炎不得不流亡臺灣、日本,但他在流亡途中發(fā)表的《書清慈禧太后事》《祭維新六賢文》《黨碑誤鑿》三篇文章,則在像利劍刺向腐朽王權(quán)的同時,樹立起了章太炎文章狂傲無以匹敵的地位,從此,章太炎的文章在學(xué)界、政界以及大眾中名聲響亮,為大家爭相傳誦。
實際上,從離開詁經(jīng)精舍書院開始,只要是當(dāng)時中國的社會事件,大到國家行為,小到個人行為,章太炎幾乎有事必文,而且,他的文章總是獨樹一幟,不講虛套,只講事實和正理,于是,在他的文章里,中國社會最為習(xí)慣的那種人情世故不見蹤影,相反,尖刻、一針見血、認(rèn)理不認(rèn)人,加上他用語果斷,遣詞精當(dāng),特別是毫無商量余地的語言風(fēng)格,就讓習(xí)慣于中庸的人們覺得夸張、武斷,于是,章太炎的文章就得到了狂傲標(biāo)簽。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章太炎的《鄒容〈革命軍〉序》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在大多數(shù)眼里,特別是文人學(xué)者高官富豪們,鄒容不到20歲的小伙子的文章,情緒激烈罷了;康有為則老沉持重,他所說的社會平和不要流血革命確實也是每個人的愿望。可章太炎筆下,鄒容的《革命軍》為“今日國民教育之一教科書”。康有為則“舞詞弄札,眩惑天下”。值得深思的是,人們一邊說章太炎的文章“狂傲”,另一邊,當(dāng)時的《蘇報》銷售慘淡,幾近關(guān)閉,章太炎的文章一出,《蘇報》立馬起死回生,從租界小報一躍成為上海頭號大報,《革命軍》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僅在一月之內(nèi)就重印二十多次,賣出一百多萬份。
可見,章太炎的文章狂傲,主要是行文特點,并不在于文章言事、說理偏激,不然,就不會得到那么多人的喜歡、擁躉。
中國歷代大學(xué)者、大文豪中,熟讀古籍經(jīng)書無不從被動科舉(應(yīng)考)然后主動科舉(主考),章太炎是個例外,他就是熟讀古籍經(jīng)書,完全沒有科舉的羈絆,于是他所讀古籍經(jīng)書比任何時代的科舉范圍都更加廣泛、全面。比如,他從古籍經(jīng)書中發(fā)現(xiàn)了第一個到達(dá)美洲大陸的人是一個中國法顯和尚,第一個發(fā)現(xiàn)圓周率小數(shù)點后七位的人是南北朝的祖沖之,他還隨口能夠用漢代語言朗誦漢詩,用唐代語言朗誦唐詩,用明代語言朗誦文天祥的《正氣歌》,中國漢唐以來的文人中就找不出第二個人來,盡管所謂小學(xué)(語言學(xué))功底深厚的大學(xué)者多的是。
眾所周知,幾千年以來,中國社會在愚昧?xí)r代形成的個人價值觀始終不曾改變,那就是熟讀經(jīng)書,指點江山,占有江山,所謂最高成就,稱帝稱王,次之是拜相入侯,最不濟則屬混成鄉(xiāng)紳,至于鄉(xiāng)紳也混不上者,叫老百姓,供養(yǎng)別人,被別人使喚,這些人當(dāng)然就是讀書不行。
章太炎也并不曾超離中國社會這個意識框架,盡管他對稱帝稱王毫無興趣,堅決不干,但他熟讀經(jīng)書用于指點江山則比別人更加積極,所以,只要是在中國范圍內(nèi)的人或事,甭管是來自朝廷還是民間,章太炎都隨口可以列舉無數(shù)上至三皇五帝,下到當(dāng)朝的文字進行解讀、評判,一些個人性的就發(fā)電報、打電話、寫信,如果與全社會有較大關(guān)系,那就寫成文章。
文章這個東西,可不是說想做成什么樣就能夠做成什么樣,它取決于做文章的人的性情、見識、腦力、語言功底、知識結(jié)構(gòu)、道德水平、責(zé)任感等等各方面的個人的素質(zhì)、能力和寫作狀態(tài),任何一丁點的變化都導(dǎo)致出來的文章不同。
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見過章太炎后的感覺是“寒冷”,因為他的眼鏡背后的眼神非常犀利、遙遠(yuǎn),芥川龍之介之所以感覺到寒冷,大略是因為章太炎當(dāng)時已經(jīng)將推翻滿清、恢復(fù)漢宗作為自己的人生使命。當(dāng)一個人將自己的生死榮辱置之度外,滿腦子就籌劃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生存樣式,這種樣式又并非自己的行為能夠決定,于是,自己的意愿和主張就必須通過無數(shù)種方式去實現(xiàn),寫文章就是其中的一種方式,此外還要演說、游說,四處奔波,這種背景下的章太炎,其內(nèi)心當(dāng)然無限忙碌、也無限堅定,當(dāng)然就讓別人感到寒冷了,他不可能對面前的一個局外人有太多熱情,除非他身系當(dāng)時四萬萬中華同胞的生死榮辱。
這正是章太炎的文章給人狂傲印象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的文章不是出于自己的生計問題,不是為了自己靠文章取得名望,甚至不是為了抒發(fā)自己的情緒,發(fā)表自己的見解,也不在于用文章表示自己的存在,這些所有世俗的文章用途都不是章太炎寫文章的目的,特別是,絕非用文章蒙騙他人獲取私利,而靠文章蒙騙他人獲取私利又幾乎是中國幾千年來最常見、最普遍的現(xiàn)象,也許,除了章太炎的文章之外,我們很難找到其他不屬于蒙騙他人謀取私利的文章,章太炎寫文章因此無所顧忌,只要與他心目中的“漢宗”有所沖突,他決不在乎是朋友還是前輩晚輩,反擊起來毫不留情,所謂心底無私天地寬,說的就是章太炎這種境界。
言行瘋癲
章瘋、章瘋子、大瘋子、章神經(jīng)等名頭當(dāng)然不是輕易得到的,可以說是他多年積積攢攢的成果,如與老師絕交;勸鄒容坐牢;同黃興打架;羞辱載湉(清皇帝);攻擊嚴(yán)復(fù);誤會唐才常;痛批康有為;駁詰蔡元培;對罵吳稚暉;冷對胡適;怪罪孫中山;臭罵袁世凱;強撐黎元洪;指責(zé)蔣介石;訓(xùn)斥張學(xué)良;調(diào)侃劉半農(nóng);譏諷毛澤東……章太炎指名道姓開罵的這些都是些赫赫有名的公眾人物,這些人物中,像嚴(yán)復(fù)、蔡元培、胡適等有良好教養(yǎng)的文人一旦遭罵則據(jù)理力爭,與章太炎吵得不可開交,結(jié)果或分勝負(fù),或不了了之,即使用“瘋癲”回敬,并不乏對章太炎的尊重與欣賞。另一些就不同了,他們都是些靠勢力、武力說話的人,或自知理虧,或別有用心,絕不站出來為自己遭罵作辯解,不過,這些人有權(quán)有勢,溜須拍馬者多,他們就背后用“瘋子”“神經(jīng)”反擊,聊且保留一點自己的臉面。章太炎瘋癲之名大略就從他們的嘴里漸漸流傳出來。不過,真正導(dǎo)致章太炎瘋癲廣為流傳的應(yīng)當(dāng)說是上海張園演說和日本東京演說兩次。
從1897年到1913年,在上海張園有據(jù)可查的大型集會至少有39次,被譽為當(dāng)時國民的思想啟蒙與解放、覺醒與吶喊的中國“海德公園”。1900年,章太炎參加在張園舉行的“中國議會”(中國國會),8月,章太炎當(dāng)眾“宣言脫社,割辮與絕”,那時候,割辮不留頭,在場眾人無不膽戰(zhàn)心驚,倒抽冷氣。1903年,章太炎擔(dān)任愛國學(xué)社國文教員,與他的學(xué)生鄒容、張繼和章士釗(當(dāng)時《蘇報》主筆)4人結(jié)為兄弟,當(dāng)時愛國學(xué)社每周到張園舉行一次演講會,章太炎幾乎從不缺席,他的即興演講與他在課堂上講學(xué)的風(fēng)格完全不同,講課時,他旁征博引,深入淺出,“詼諧間作,妙語解頤”(弟子許壽裳語),演講的章太炎則一反常態(tài),每次都是三言兩語,畫龍點睛,聽得下面群情激奮。一次,蔡元培演說完,請章太炎上臺,他竟不走演說臺旁邊的臺階,從演講臺正面翻身爬上講臺,高聲說了“必須革命、不可不革命”就又翻下演講臺。蔡元培并不覺得奇怪,臺下則愣了半刻,隨即歡呼聲一片,驚天動地。當(dāng)時,上海張園是私人花園,但對公眾開放,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公園,買張門票就可以在里面游玩一整天,有吃有喝有玩,章太炎他們的演說活動面對的也就是這些普通市民。因此,一傳十,十傳百,章太炎瘋張的演說也就廣為人知。
1906年7月,章太炎從上海西牢出獄,第三次流亡日本,中國同盟會總部在東京舉行了盛大歡迎會,章太炎作了長篇演說。“兄弟自己承認(rèn)有神經(jīng)病,也愿諸位同志,個個人人,都有一兩分的神經(jīng)病。”“譬如思想是個貨物,神經(jīng)病是個汽船,沒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經(jīng)病,必?zé)o實際。沒有神經(jīng)病,這思想可能自動的嗎?”這次演說的聽眾,主要是在日本的中國留學(xué)生,二千多人。章太炎不僅不忌諱自己“神經(jīng)病”,而且邀請大家都和他一樣有點神經(jīng)病。但大家都很清楚,章太炎所說的神經(jīng)病,其實不過是說一個人要有主見,要有思想,要對國家、民族有所擔(dān)當(dāng)。
這兩次演說,章太炎給自己戴上了瘋癲的頭銜,形象生動,受眾廣泛,現(xiàn)場人們無不對章太炎瘋癲印象深刻,確實也怪不得別人。
我們且用章太炎在國家政權(quán)一事的處理上來具體分析他瘋癲的行為。
中國人治學(xué)一般不用從客觀現(xiàn)實世界中去尋找、發(fā)現(xiàn),那比較困難,還容易犯事,只用鉆進書堆里,書堆則越是古老久遠(yuǎn)越好,把書鉆研多了,用來對客觀現(xiàn)實指手畫腳,或自娛自樂,教書育人,或馴化民眾,直至救國。大體如是,至今依舊。章太炎也沒有脫離這個中國定律,他書讀多了,就開始救國。
救國的事情同治學(xué)不一樣,治學(xué)只用和古老的書籍打交道,把自己關(guān)在書房里就可以,救國則不同,要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非常麻煩,章太炎在救國過程中就表現(xiàn)得非同常人,讓章太炎深信不疑的是,中國下至貧民百姓上至高官文豪,幾千年以來,誰都對國家大權(quán)夢寐以求,而一旦國家大權(quán)落入囊中,卻沒見一個不是效法先王,大發(fā)淫威,魚肉百姓,作踐中華,不知多少次多少人為搶奪國家大權(quán),使得中華大地尸橫遍地,赤野千里,他們毫不足惜,相反,樂此不疲,引以為豪。
一百多年來,關(guān)于章太炎的救國理念、方略、實踐有過成千上萬的解讀、介紹,但無不建立在中央集權(quán)這個前提之下,所以,不客氣地說,都是牛頭不對馬嘴。
章太炎救國首先是對滿清政權(quán)的當(dāng)權(quán)者不滿,當(dāng)他明白更換當(dāng)權(quán)者無濟于事的時候,他徹底否定了滿清政權(quán),1900年,他上書李鴻章、劉坤一,并發(fā)表《藩鎮(zhèn)論》《分鎮(zhèn)》兩文,明確提出了他的“分權(quán)獨立”主張,十多年后,他又提出南北分權(quán)主張,1920年,他更明確提出“各省自治、虛置中央”是救國的唯一良策。
章太炎很清楚,那些可能占有國家大權(quán)的人里面,沒有一個愿意接受他的主張,但他并不在乎這種明顯的自討沒趣,而是拖著自己病懨懨的身軀,先是跑到廣州肇慶游說兩廣都司令岑春煊,要求他收回成命,保留護國軍軍務(wù)院,這樣才能讓南方政權(quán)與北方政權(quán)相抗衡,避免中央大權(quán)獨攬,結(jié)果,岑春煊并不買賬。當(dāng)孫中山在廣州重新成立臨時政府的時候,章太炎自告奮勇地跑到香港去游說廣東督軍龍濟光,希望他助孫中山一臂之力,讓當(dāng)時的西南各勢力擁護廣州軍政府,結(jié)果,龍濟光并無主張。章太炎又直接跑到昆明去找唐繼堯,唐繼堯很聽章太炎的話,聘了他為聯(lián)軍總參議,向四川、兩湖用兵,占領(lǐng)了重慶、瀘州,然后沒有了下文,孫中山也從廣州臨時政府退出,南北開始和談,把章太炎氣得要死。1920年,奔波了三年的“自治”沒有結(jié)果,章太炎并未罷休,正好湖南譚延闿通電全國,宣告自治,章太炎給予了高度評價,并親臨長沙,全力支持。11月,廣東陳炯明響應(yīng)章太炎也宣布自治。可是,好景不長,幾個月后,孫中山廣州臨時政府成立,宣布北伐。章太炎的自治主張終成夢想,中華大地依舊上演著章太炎最不想看到的幾千年不斷重復(fù)的故事,權(quán)力戰(zhàn)爭。
“各省自治、虛置中央”這事最典型地表現(xiàn)了章太炎處事瘋癲的特征,籠統(tǒng)地說,就是別人都知道不可能做到,也都不想去做,但章太炎卻不顧一切地去做,而且,體面不體面的方式都敢用上。恰如當(dāng)初袁世凱稱帝,我們都被告知全國上下一片欷歔聲,而實際上,若非老天照應(yīng),袁世凱繼續(xù)活著,全國上下必然三呼萬歲。章太炎則四處演說、發(fā)文,直接跑去找袁世凱當(dāng)面質(zhì)責(zé),拿個鞋底,騙人家說與袁世凱有約定,見了鞋底他就知道是誰也一定召見,結(jié)果,人沒見著,被袁世凱軟禁了起來。
由此可見,章太炎處事瘋癲的背后,首先是他所行之事,同時代的人們聞所未聞,他必須傾盡全力去做,而且必須使用一些極端方式,否則就難以讓別人接受。
大智大勇之人行事,特別是在毫無私心的前提下,往往行為極端,因為他深知非極端難以見效,而時間、精力、機會難得,必須使用極端方式才能夠事半功倍,可況他所思所想,別人并無知覺,更需要極端才有可能取得別人的認(rèn)可。
遺憾的是,前文說過,幾乎每個中國人都夢寐以求國家大權(quán)在握,但像章太炎這樣只為民族生靈著想的人,幾千年來,我們被告知有很多,卻并不曾見到幾個真的。
更遺憾的是,章太炎一生做過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情,然而,似乎大都不了了之,并非他想做的事情錯了,現(xiàn)在看來,錯的并非他的主張、他的行為,而是,一個民族的命運。
當(dāng)我們分析章太炎的瘋癲言論,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每一句出格的話,其實不過是道出了大家都不敢出聲的事實。人們之所以說他瘋癲,實際的目的要么是避嫌,如張之洞就是害怕禍及自己;要么是自嘲,如袁世凱就是自己難以下臺;要么,并不清楚事實,隨聲附和,并不認(rèn)識章太炎的人們大都如是。
附:
章太炎并未反對白話文和甲骨文
關(guān)于章太炎反對白話文的說法很常見,奇怪的是,無論是他自己的文字還是別人介紹他的文字里面都找不出來確鑿的證據(jù)進行證明,比如,最常見的說法是胡適、魯迅、劉半農(nóng)認(rèn)為章太炎反對白話文,不過,這些人何時何地如何“認(rèn)為”卻閉口不談。與章太炎反對白話文類似的還有他反對甲骨文的說法,也是找不出證據(jù)。相反,章太炎對白話文和甲骨文都曾經(jīng)有過直接的議論,只不過,他沒有將他的議論形諸文章,從他人的記載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實際上,章太炎不僅不反對白話文和甲骨文,而且,他對白話文和甲骨文的認(rèn)識比迄今幾乎所有人的認(rèn)識都更加高明,如果他的認(rèn)識更加高明的說法成立,那么,這種反對白話文和甲骨文的說法也許就是別有用心,也許就是一種拉大旗作虎皮,愚弄讀者,以便渾水摸魚,很不堪的文痞行為。
查閱有關(guān)資料,章太炎反對白話文和甲骨文的說法其實只有四條蛛絲馬跡,我們逐條分析如下:
第一條:胡適將自己的《中國哲學(xué)史大綱》送章太炎,章太炎見胡適在題字上畫了條線,說:“何物胡適,膽敢在我的名字上胡抹亂畫。”又見只有上冊,就說:“胡適著作未見下冊,著作監(jiān)也。”這條成為章太炎對胡適不感冒,針對胡適白話文的唯一證據(jù)。
章太炎長胡適27歲,胡適在北京大學(xué)任教的時候還是個20多歲的小伙子,章太炎已經(jīng)是50多歲了,無論是講年紀(jì)、社會聲望還是學(xué)術(shù)成就,在章太炎面前,胡適都是晚輩身份。盡管我們找不出更多材料,用我們的人生經(jīng)驗去分析這條人云亦云的描述,也不難發(fā)現(xiàn),這條實在夠不上章太炎反對胡適更別說反對白話文了,相反,包含有章太炎對胡適的愛護之心。首先,章太炎接受了胡適的贈送,而且,罵過之后發(fā)現(xiàn)胡適的名字下也有線條,還自嘲說:這還差不多,扯平了。一個扯平,章太炎把自己放在與胡適平等的身份,這不可能是對胡適不滿的表現(xiàn)。其次,章太炎罵胡適著作監(jiān),話是難聽,但也說明,章太炎在意胡適著作的下冊,是對他只寫了上冊表示不滿,并非因此侮辱胡適,說刺激胡適也許更加恰當(dāng),終究章太炎是長輩,對晚輩的學(xué)業(yè)成就感到心急,出口過激也是人之常情。他真要是對胡適反感,就不可能接受他的著作,更不可能自嘲扯平,要么拒絕,要么沉默,但他沒有,所以,說“著作監(jiān)”更大的可能是等候、催促胡適寫出下冊。
第二條:魯迅有兩句話:“但一到攻擊現(xiàn)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后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便不敢去見他了。”前一句是魯迅針對章太炎提出的“白話必須從小學(xué)中尋出本字”而言,后一句是魯迅說自己長時間不去看望章太炎的原因。
魯迅的前一句話涉及語言問題,其內(nèi)容正好與第三條完全一樣,我們將它放到第三條進行分析,這里只說魯迅的后一句。學(xué)生長時間不去看望老師,理由是因為自己主張白話,就被用來作為章太炎反對白話的證據(jù),似乎過于牽強。假設(shè)章太炎確實反對白話,并因此也會反對主張的人,那么,比魯迅主張白話更加積極的是錢玄同,和魯迅主張白話的勁頭不相上下的是他的兄弟周作人和另兩個同班同學(xué)許壽裳、朱希祖,他們幾個,除了周作人因老師投壺事件與老師絕交,其他學(xué)生不僅沒有中斷過看望老師,像錢玄同、許壽裳很多時間還天天進出章太炎身邊,若按魯迅的說法,錢玄同和許壽裳豈不天天遭章太炎的白眼?若考慮章太炎的習(xí)性,他們倆應(yīng)當(dāng)被章太炎打得哭爹喊娘,事實卻不是,因此,魯迅自己不去看望老師,只是他自己的原因,主張白話只是魯迅自己尋出來的一個最為冠冕堂皇的理由,與章太炎是否反對白話并不存在必然聯(lián)系。
第三條:陳存仁《章太炎面折劉半農(nóng)》。
與其他資料相比,陳存仁的這篇文章最為詳細(xì)、明確,最為清楚地介紹了章太炎對于白話文的見解和態(tài)度。文章開頭用大段介紹劉半農(nóng)訪問章太炎的背景,字里行間,陳存仁對劉半農(nóng)的蔑視非常明顯。關(guān)于章太炎如何看待白話文,文章里記述“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我國的《毛詩》就是白話詩。歷代以來,有白話性的小說,都是以當(dāng)時的言語寫出來的,寫得最好的是《水滸》《老殘游記》等,甚至用蘇州話寫的《海上花列傳》”。文章介紹了章太炎問劉半農(nóng)關(guān)于白話文的標(biāo)準(zhǔn),白話的讀音構(gòu)成,介紹了不同時代的白話樣式(讀音),以及高麗話、日本話與中國話的關(guān)系,等等。還順便提到“甲骨文沒有多大的考證價值”。
陳存仁用了“一句也插不上嘴”“呆若木雞”“面有難色”等描述劉半農(nóng),但在他記述的章太炎關(guān)于白話文的講話里,沒有一句表明章太炎反對白話文。相反,章太炎非常清楚,用當(dāng)時的言語寫成的文章(詩、小說)就叫白話文,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章太炎對白話文的認(rèn)識并非外行,再聯(lián)系魯迅介紹的“白話必須從小學(xué)中尋出本字”就更清楚了,白話文必須表現(xiàn)為文字,一個文字在不同時代的意義不一定相同,當(dāng)它被用來指稱話語的時候,那么,如何保證這個字與當(dāng)時的話語基本對應(yīng)?也就是說,話語不能不管文字,文字不能不顧話語,既然我們用文字表示現(xiàn)在的話語,那么,當(dāng)然得用“這句話”所對應(yīng)的“這些文字”,也就是章太炎所說的“本字”,而魯迅則以為“牛頭不對馬嘴”,可見,若非魯迅的語言知識比較差,就只能說魯迅說這話沒動腦子,也或者,別有用心。
劉半農(nóng)也許真的被章太炎“面折”,因為看上去他沒有章太炎對白話文的認(rèn)識清楚,而從頭到尾,我們看不出章太炎有反對白話文的意思,只看出章太炎比較惱火,而且主要是惱火劉半農(nóng)搞不清楚漢語的構(gòu)成。這一點,公道地說,章太炎是強人所難,或者說,拿自己之長戳劉半農(nóng)之短,根據(jù)陳存仁的介紹,劉半農(nóng)當(dāng)時做的應(yīng)當(dāng)屬于田野調(diào)查,就是當(dāng)時的人們所使用的口語,而章太炎拿漢朝、唐朝、高麗、日本來批判這種田野調(diào)查,這個才真是牛頭不對馬嘴,恰如指責(zé)做時事新聞報道的記者不知道《史記》里有同樣的事情記錄,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說章太炎反對白話文,只能說,章太炎對白話文的認(rèn)識更深刻,他有自己的白話文標(biāo)準(zhǔn),并因此對當(dāng)時提倡的白話文,包括人,恨鐵不成鋼,提倡白話文,怎么能不清楚白話文的歷史和基本要求呢?
第四條:也就是上條已經(jīng)介紹的,章太炎說:“甲骨文沒有多大的考證價值。”
章太炎弟子王仲犖也寫有一篇《太炎先生二三事》,他說,我二十多歲時,一次到他家去,見他從抽屜里取出兩三片甲骨片撫摸著說:這大概不會是假的吧。他并不是說甲骨文都是假的,是說有的甲骨片是假的,太炎先生懷疑的是這類假的甲骨文,對真正的甲骨文并不懷疑。
至于章太炎說“甲骨文沒有多大的考證價值”。這句話也不能用來表示他反對甲骨文。要知道,即使到今天為止,據(jù)說甲骨片成千上萬,統(tǒng)計出來的甲骨文單字就有4500~4600個,而考據(jù)(認(rèn))出來的文字只有200多個,這還在其次。自從秦朝統(tǒng)一漢字之后,我們閱讀、研究所依靠的書面語言就統(tǒng)一為能夠認(rèn)識的漢字,先是篆體,后發(fā)展為隸書、楷體、宋體,現(xiàn)在中國大陸是簡化字,臺灣、香港是繁體字,甲骨文盡管是最早的漢字,但因為后來的人不認(rèn)識,研究來研究去也就是早就知道的“最早的漢字”“殷商卜辭”,此外就沒有了。如此說來,研究甲骨文的價值早已經(jīng)實現(xiàn),繼續(xù)研究,也只知道是“最早的漢字”“殷商卜辭”,確實沒有多大的考證價值,章太炎的話很在理。不過,這也不證明章太炎反對甲骨文。
章太炎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應(yīng)該說就是愛發(fā)表議論文章,只要是他所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談?wù)劦氖虑椋土ⅠR寫成文章。而白話文、甲骨文在當(dāng)時都是很大的事情,章太炎偏偏沒有文章談起,這也證明,章太炎并不反對白話文和甲骨文,何況,他自己有過許多白話文。因此,只能說,章太炎對白話文和甲骨文未進行深入研究,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