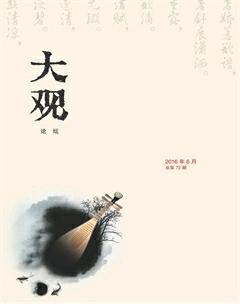《子夜歌》題目考
摘要:《子夜歌》是南朝民歌中的一顆璀璨明珠,當前學術界對《子夜歌》這個題目存在多種爭議,其關鍵在于對“子夜”的理解。為了弄清楚《子夜歌》這個題目的真正含義,本文會例舉文籍的記載,并根據文本對當前學界兩種較為主流的說法提出質疑:“子夜”是人名;“子夜”指時間。指出這兩種說法的不合理之后,本文會根據史實提出自己的觀點:《子夜歌》與它的和聲“子夜來”密切相關,并作進一步的證明。
關鍵詞:子夜歌;和聲;民歌;子夜來
南朝民歌大部分都被保存在宋郭茂倩所編的《樂府詩集·清商曲辭》里,主要有吳歌與西曲兩類,《子夜歌》便是屬于吳歌這一類。《子夜歌》共四十二首,在南朝民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毫無疑問,它是南朝民歌史上的一朵奇葩,可是除了少數的幾本書對它有記載之外,其他關于《子夜歌》的記載寥寥無幾,因此造成了學術界的爭議,這尤其體現在對“子夜”的理解上。
《宋書·樂志》:“《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瑯玡王珂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
《晉書.樂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瑯玡王珂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
《舊唐書·音樂志》曰:“《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晉日常有鬼歌之。”
這幾段史料讓部分學者認為《子夜歌》就是晉代叫”子夜“的女子所作,例如學者錢仲聯在《中外愛情詩鑒賞辭典》里就說《子夜歌》是晉代一位叫“子夜”的女子所寫,但也有很多學者提出了質疑,魯迅在《門外文談》里說《子夜歌》是無名氏所作,當代學者王乃英、林杰等則認為“子夜”應該指的是時間。
我認為《子夜歌》這個曲調名稱應與它的的和聲“子夜來”相關,對南北朝樂府研究較深的學者王運熙也是持此觀點。
下面我將對“名字說”,“時間說”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時也會對我的觀點做出一些解釋。
一
《子夜歌》是晉代叫“子夜”的女子所寫,這里就有兩種理解:《子夜歌》42首全部由“子夜”一人所寫,另一種說法就是晉女子“子夜”寫了一部分,其后的女子模仿它寫了很多首,由此湊成了42首。我認為這兩種說法都是經不住推敲的。
第一種說法認為《子夜歌》42首全部由一位名叫“子夜”的女子所寫,從內容上看,這種說法是不可信的。《子夜歌》塑造了一個個遭遇不同且性格迥異的女子,有相戀時惹人憐愛、婉麗的女子,如“宿昔不梳頭,絲發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還有相思時癡情堅貞的女子,如“別后涕流連,相思情悲滿。憶子腹糜爛,肝腸尺寸斷。”對待被棄,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做法,有自怨自艾,滿腔怨憤的,“遣信歡不來,自往復不出。金銅作芙蓉,蓮子何能食。”也有毅然決然的劃清界限,表明自己對負心男的不屑的,如“常慮有貳意,歡今果不齊。枯魚就濁水,常與清流乖。”《子夜歌》前后敘事,塑造形象的矛盾這一點就證實了它不可能是一個人所寫。另外,假設《子夜歌》是一個人所寫,那么在史籍或文籍上對于“子夜”這個有才情的女子應該或多或少會有一些記載,但我們只知道她是晉人,叫“子夜”。歷史上最有名的女才人應該是宋代的李清照,即便是如此有名的女詞人給我們也不過留下了50余首詞和一些詩歌,散文等,遠在宋代以前的晉女子“子夜”一個人就寫了42首詩,并且為后世文人所津津樂道或者模仿,可是關于這個女才人的記載寥寥無幾,這樣的說法似乎并不可信。
還有人認為“子夜”是人名,只不過她只是作了部分詩,其余的是其它人作的。這種說法也是存在問題的。首先《宋書·樂志》的那段史料記載本身是有問題的,之后的《晉書》、《舊唐書》的記載當然也是錯誤的。最早的關于《子夜歌》的記載應該是南朝宋劉敬書的《異苑》(卷六):“晉孝武太元中,瑯玡王珂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章郡,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宋書》是南朝梁沈約所作,那么《宋書》中的記載應該是源自《異苑》,可是我們發現劉敬書的《異苑》并沒有提及《子夜歌》的作者,那么《宋書》中說《子夜歌》是晉女子“子夜”所作說法不可信。從另一方面講,女子的名字叫做“子夜”也確實有點奇怪,因此,《子夜歌》中的“子夜”應該不是指名字。
二
有部分學者例如王乃英、林杰等認為“子夜”應該指的是時間,如果“子夜”指的是時間的話,那么這個時間非常特殊而且很具體,就是夜里的23點到凌晨1點。對于這種說法,我們可以根據《子夜歌》的內容加以駁斥。《子夜歌》共42首,具體寫是在夜里的只有七、八首,還有一些是寫傍晚或白天,不過更多的是沒有告訴我們時間的,例如“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歡行白日心,朝東暮還西。”像這樣的詩我們無法判斷它所指的時間,而且這樣的詩占據了絕大多數,就算寫明是在夜里,例如“夜覺百思纏,憂嘆涕流襟。”它是發生在夜里,但一定是“子夜”嗎?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再者,學者王乃英于1996年在《北京教育學院學報》上發表的《<子夜歌>作者考》里面的論證本身存在漏洞。他用《讀曲歌》之六的一首詩來論證“子夜”指的是時間:
打壞木棲床,誰能坐相思。
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悲。
按照他的觀點“子夜”是指時間,那么后兩句的斷句應為: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悲。很明顯,這樣的斷句與詩句的意思是不相符的,正確的斷句應為: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悲。這里的“子”代指“你”,“夜”表示在夜里,這兩個字都是有含義的,并不是合起來表示一個具體的時間。因此王乃英的論證存在漏洞,不足以支持“子夜”是表示時間的說法。
還有很多學者用《子夜歌》的變曲來考察“子夜”的含義,所謂“變曲”就是指曲子的變化,從舊有曲調中變化出來的新聲,這些變曲多為《子夜歌》以后的人所做,用它來考察“子夜”的含義未免不太嚴謹。endprint
三
我的觀點是《子夜歌》這個曲調名稱與它的和聲“子夜來”有關,“子夜來”也就是《子夜歌》的主要聲調。女子企盼男子夜里能來與自己相會,這個解釋與《子夜歌》的內容是相吻合的。下面我將作更深一步的論證。“《樂府詩集》(卷二十六)于論述《相和歌辭》時說:‘諸曲調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后,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我們知道吳聲西曲是能夠配合曲子唱的,“送聲的位置,應在全篇末尾,……至于前面的和聲……它的位置,應該在每句之末尾。”《南史》(二十二)王儉傳:“齊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效技藝:褚彥回彈琵琶,……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這里的“子夜來”就是《子夜歌》的和聲,以“來”字作為和聲結尾有很多,根據《舊唐書.音樂志》的記載,《烏夜啼》的和聲是“夜夜望郎來”,《古今樂錄》中記載《襄陽樂》的和聲是“襄陽來”,《三洲歌》的和聲是“歡將樂共來”,因此“子夜來”作為《子夜歌》的和聲是有跡可循的。除此之外,吳聲西曲的曲調名稱與它的和送聲相關這種說法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的。《阿子歌》送聲云:“阿子汝聞不?”《歡聞歌》送聲云:“歡聞不?”《丁督護歌》的和聲是“丁督護”,《阿子歌》的和聲是“阿子聞”,《歡聞歌》的和聲是“歡聞”,《團扇歌》的和聲是“白團扇”,《女兒子》的和聲是“女兒”,我們可以發現和送聲與題目及內容是有一定關系的,學界對《子夜歌》題目的諸多誤解是因為對吳聲西曲中的和送聲關注較少。
綜上,《子夜歌》的正確理解應該與它的和聲“子夜來”相關,這種解釋也讓我們對《子夜歌》的內容有了全新的理解,它哀婉的情調打動了無數人,那一聲聲“子夜來”的深情呼喚,如此動聽,喚醒了我們對愛情的向往和期待。
【參考文獻】
[1]王運熙.六朝樂府與民歌[M]上海;古典文獻出版社,1957:109.
[2](宋)郭茂倩.樂府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
[3]王乃英.子夜歌作者考[J]北京教育學院學報,1996,(3):37-39.
[4]王運熙.樂府詩述論增補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清)王謨.古今樂錄(卷首)[Z]//漢魏遺書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影印本).
作者簡介:羅芮,出生年份:1995,女,漢族。籍貫:湖北省武漢市。湖北大學本科生,專業:漢語言文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