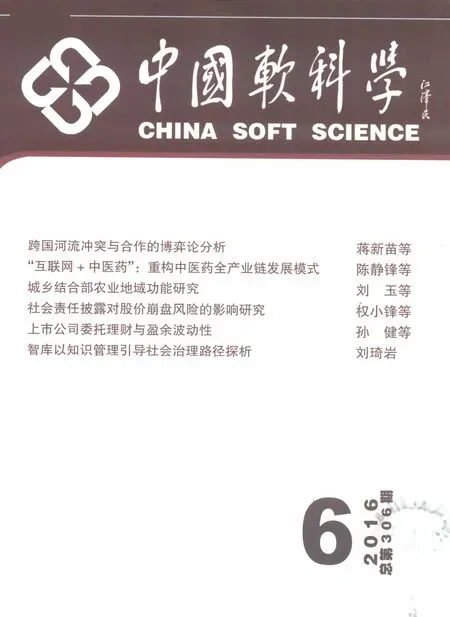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研究
劉 玉,馮 健
(1. 中國人民大學 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北京 100872; 2.北京大學 城市與環境學院,北京 100871)
?
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研究
劉玉1,馮健2
(1. 中國人民大學 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北京 100872; 2.北京大學 城市與環境學院,北京 100871)
摘要:快速城鎮化背景下,城鄉結合部大量農田被征用開發,農業及其支撐部門的發展受到嚴重沖擊,農業從業人員的生產生活發生重大變化,城鄉經濟、社會、生態系統受到顯著影響。論文在梳理農業區位與功能演變、城市生態安全與食品安全、城鄉結合部地域功能,以及新型城鎮化等相關理論基礎上,構建了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體系。認為城鄉結合部農業具有:優化城鄉生態、加強城鄉聯系、提升城鄉發展和協調城鄉關系等多方面功能,尤其在構筑生態緩沖帶保護城鄉生態環境、降低城市邊緣區發展壓力,滿足城鎮居民日益增長的食品安全與休閑、娛樂消費需求,促進新增城鎮化人口就業安置,以及加強城鄉間產業互動與要素交流,緩解城鄉矛盾沖突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的最終實現,需要創新生產經營模式。對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實現程度的初步分析表明,我國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整體上未被充分認識與得到應有的發揮,此方面理論與現實研究均需要進一步加強。
關鍵詞: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農業區位;新型城鎮化
一、問題的提出
城鄉結合部被認為是目前全球范圍內LUCC(土地覆被/土地利用)最劇烈、人地系統矛盾最尖銳的地區[1]。城鎮化使城鄉結合部大量優質農田被破壞,農業發展受到嚴重沖擊。20世紀中后期,美國每年因城鎮化而失去的優質農田在39萬-76萬英畝(約15.8萬-30.8萬公頃)之間[2],近年中國快速城鎮化背景下形勢更為嚴峻。例如,第二次土地調查資料顯示,1996-2009年,北京耕地凈減11.67萬公頃,離全市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標僅1.24萬公頃[3]。
盡管城鎮化某種程度上給城鄉結合部農業發展帶來了一些新的機遇,但在我國以城市經濟、空間擴張為主導的傳統城鎮化模式下,城鄉結合部農業用地和農業的價值被嚴重貶低與忽視。農業用地急劇減少,并且被分割成分散的小片土地,無法再通過與周邊的農地分享信息,以及建立正式非正式的商業聯系而獲得規模效益[4],包括投入供給部門、產品加工部門和流通服務部門等在內的各種農業支撐部門的發展都受到顯著影響,農業從業人員的生產生活也因此發生巨大變化。城鄉結合部作為城市擴張與蔓延的前沿地區,范圍不斷擴大,有些地方逐漸變成建成區,然后在外緣又形成新的城鄉結合部空間。在此循環往復的過程中,城市周邊的農地、農業、農村、農民經歷全面轉型,城鄉結合部人口構成、居住、就業、收入、產業形態以及社會利益關系等發生顯著變化,城市食品安全、景觀、生態、空間結構等也面臨重要挑戰,城市與鄉村經濟、社會、生態系統均受到嚴重影響。
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的傳統、低層次發展及其“非生產性行業”定位使其脫離于現代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軌道,并且在思考與塑造產業關系、區域關系時被忽略。城鄉統籌、三產互動等新型城鎮化視角下,運用現代化經營管理模式下的農業,不僅產值、附加值可以大幅提升,而且其拉動就業的功能,維護和修復生態的功能,拉動前向、后向、側向聯系的功能和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功能都是顯著的。城鄉結合部農業由于其位于城市邊緣地區的特殊區位,地域功能更為顯著與多元。
早期,西方國家的規劃者曾一度忽視城鄉結合部農業的價值與功能,基于農業產生的噪聲、垃圾處理和動物傳染疾病等原因不斷將農業向城市外緣推進[5], 政府通常會禁止城市周邊農業企業的一些發展行為,如建設牲畜圈舍等[6]。但近來開始重新審視城鄉結合部農業的價值與功能,認為其可以提供生態服務、野生生物棲息地、良好的視野以及農產品[5],在倡導“本地食品”消費,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和緩解城市氣候變化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7]。同時,研究者們開始關注并運用各種模型、參數測度城鎮化對城鄉結合部農業土地價值、價格及農業發展的影響[8-10];剖析城鄉結合部地區農業用地不斷減少的因素[11];分析城鄉結合部農業適應這種不利局面的能力[12-13];揭示農業企業積極面對的潛力,尤其是社會游說、修訂立法和提供有力的理論基礎等[6,14]。有學者從城市政治生態視角探討了城鄉結合部農業保護問題,指出農業與房地產業土地利用之間的矛盾不是根本,政策決策過程的失誤會導致失敗的后果[7];有研究提出在城市發展的壓力下應保留城鄉結合部的農業活動[15];也有研究指出找到獲得更多收入的機會是讓城鄉結合部農業得以維持的最主要動力[16];完備的土地利用規劃體系及劃定城市增長邊界對保護城市周邊農業和林業用地具有重要的意義[17];以及運用享樂成本估價模型(multilevel hedonic pricing model)定量分析城鄉結合部農業用地保護政策在減輕城市發展壓力和保護農業用地方面發揮的作用[18]等。
城鄉結合部農業兼具都市農業和城郊農業的部分特征。國內多個學科圍繞此主題展開了研究。概括而言,農學對其的研究主要立足于農業生產、農業環境、農業經濟的發展與變化;土地科學主要圍繞農業用地規模、價值、價格的變化及影響因素等展開;環境科學主要針對農業的生態、景觀功能及開發;規劃領域主要關注農業發展與城市規劃的結合;地理學則相對綜合地從農業特征、空間布局等角度加以探討。具體研究如:用系統論的思想融合多種理論分析現代城郊農業區發展的機理[19];界定都市農業的內涵特征與評價標準[20];梳理都市農業與城郊農業的理論體系[21-23];揭示城市化與都市農業功能之間密切而錯綜復雜的耦合關系[24-25];用投入—產出法測算改革開放以來不同階段都市農業與城市經濟之間的關系[26];探討都市農業空間分布格局、發展模式與發展路徑[27-28];論證將都市農業納入城市規劃中的必要性[29],指出大城市農業地域功能要服從城市總體規劃需要[30]。認為城郊農業功能定位與純農業有顯著區別[31],將城郊農業的功能界定為生產服務功能、生態保育功能和景觀文化功能,并估算了北京城郊農業各種功能的經濟價值量[32]等。
已有研究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城鄉結合部農業發展的相關問題,但對中國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與價值的研究還不多。本文將緊密結合我國城市生態安全、食品安全、居民消費、新增城鎮化人口就業、城市邊緣地區農業與相關衍生產業發展,以及城鄉經濟社會融合等核心問題,探討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旨在為城鄉結合部農業的合理發展和地域功能的有效實現提供借鑒支撐。
二、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理論基礎
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疊加了農業產業功能與城鄉結合部地域功能,因此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農業。其理論基礎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業區位論與食品安全理論
1826年,德國農業經濟學家杜能(J.H.Thünen)在《孤立國》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農業區位論,為農業區位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意義不僅在于闡明市場距離對于農業生產集約程度和土地利用類型(農業類型)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首次確立了土地利用方式(或農業類型)的區位存在著客觀規律性和優勢區位的相對性。其中易腐難運的食品應在距離城市最近處生產,該圈層的大小由城市人口規模所決定[33]。
食品安全理論的范疇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得到拓展,其中本地食品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盡管現代交通、運輸、儲存等技術的發展,使得食品供給的空間范圍日益擴大,作為消費中心的城市食品供給來源地不斷增多,空間距離不斷拉大,但是從食品安全的角度,消費者食用當地當季食物才是更安全的,不僅因為本地食物營養構成及生長環境最符合本地居民健康需求,而且許多食物,如葉類蔬菜在運輸的過程中營養價值極易流失。另外,從環保角度,本地食物供給率的提高有利于減少運輸和儲存食物過程中大量化石能源的消耗。2005年世界環境日首次引入一個新名詞——本地食客志愿團(Locavore),由美國舊金山地區的一群志愿者創造,是一個自發組織起來成立的食客群體,只吃距離自己家100英里以內出產的食品,目前歐美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這一群體[34]。
(二)城市生態安全與精明增長理論
快速城市化和生態安全背景下,城市生態安全問題研究成為城市學與生態學研究的重點之一[35]。城市生態安全相關理論認為:城市的發展不應阻礙所在區域的自然進程的發展,城市的發展需要圍繞著自然生態的完整來進行[36-37]。城市生態安全格局是城市自然生命支持系統的關鍵性格局,它維護城市生態系統結構和過程健康與完整,維護區域與城市生態安全,是實現精明保護與精明增長的剛性格局,也是城市及其居民持續地獲得綜合生態系統服務的基本保障[38-39]。
20世紀90年代末,包括“吃掉”城市周邊大量農田等城市蔓延帶來的諸多負面影響引起了美國規劃界與學者的廣泛關注,精明增長(Smart Growth)理論應運而生。該理論倡導將城市發展融入區域整體生態體系和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目標中,不僅要提高城市內部土地利用效率,也要降低城市邊緣區的發展壓力,保護農田和生態脆弱區[40]。
(三)農業多功能理論
20 世紀80、90 年代,源于日本“稻米文化”的農業多功能性提法逐漸得到國際相關組織認可與推廣,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21 世紀議程》、世界糧食首腦會議通過的《羅馬宣言和行動計劃》和聯合國糧農組織召開的國際農業和土地多功能性會議等都明確提出與涉及農業多功能問題[41]。農業的多功能包括:經濟功能、社會功能、政治功能、生態功能和文化功能[42]。
農業多功能理論拓展了農業生產以外的其他功能,也有助于人們從更廣闊的視角和更深層次去思考與挖掘農業對社會的貢獻,提高人們對農業地位與價值的認識,并促進包括有機農業、生態農業、能源農業、旅游農業、文化農業等在內的農業多元化經營與發展模式興起。
(四)城鄉結合部地域功能理論
作為城市與鄉村地域之間的過渡地帶,城鄉結合部具有重要的地域功能[43]。首先,城鄉結合部承擔與分擔著城市的部分功能,如作為維持城市正常運轉所必需的大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基地;城市對外交通樞紐;分流城市經濟要素與經濟活動,減輕城市壓力;為城市及城市居民提供景觀、生態與休閑娛樂空間[44-47]。其次,城鄉結合部是經濟要素從區域中心(城市)向外圍體系擴散過程中的重要路徑[48-49]。其經濟空間形態及演化影響甚至決定著區域經濟空間向一體化為特征的高水平穩定平衡階段演化的進程。再者,城鄉結合部還是許多國家和地區人口增長的主要區域,聯系城鄉發展的重要紐帶[50]。
現階段,城鄉結合部的多功能屬性日益得到廣泛認識。城鄉結合部具有巨大的潛力用于發展多功能土地利用[51]。除了經濟功能外,城鄉結合部基于農業景觀之上的生態、休閑、娛樂與美學等功能越來越受到關注[52]。此理念的影響下,歐洲一些國家從原來較注重城鄉結合部單一的景觀功能轉向將城鄉結合部視為多功能區加以規劃[53]。
(五)新型城鎮化理論
新型城鎮化是一種“集約、智能、綠色、低碳、協調、以人為本”的城鎮化道路。其核心理論內涵包括:建立良好生態環境支撐下的城鎮化發展,變城市“外延式擴張”為“內涵式發展”,保護城市周邊農業用地;實行城鄉統籌的城鎮化發展,加強城市與鄉村在產業上的互動和要素間的合理流動;促進以人為本的城鎮化,讓城鎮居民、新增城鎮化人口和農村人口的合法權益均能得到有效的保障,積極創造就業與發展機會等。
相對于傳統城鎮化,新型城鎮化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是在實現城鎮化的過程中積極調動一切有利因素,切實解決各種問題,讓各個主體、各種區域、各類關系都能得到妥善安置,獲得應有的利益。過去以犧牲農村、農業、農民、農地利益換取城鎮化快速發展,以犧牲生態、社會效益換取經濟效益的模式將得到徹底改變。

圖1 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理論基礎
上述農業區位與功能演變、城市生態安全與食品安全、城鄉結合部地域功能以及新型城鎮化等相關理論,為探討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圖1)。
三、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體系
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對目前我國城鎮化進程中促進人與區域良性發展問題的深入思考也為構建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具有多元化、深層次的特點,具體包括:
(一)保護城鄉生態功能——營建城市邊緣區生態緩沖帶
生態狀況與用地類型密切相關,建立在自然資源與景觀開發利用基礎上的城鄉結合部農業活動有利于保護城市周邊自然生態系統,并進而對維護整個城市與鄉村生態具有積極作用。
一方面,農業景觀自身具有強大的生態功能。以綠色植物和水體等為主的農業生產載體或產品可以涵養水源、凈化空氣,保持水土,緩解現代城市經濟社會活動造成的多種生態負面效應,對保護自然環境和人類身心健康極具益處。另一方面,保留適度的農業用地及其農業經濟活動,可以在城市與鄉村地域之間營造一個有效的生態緩沖帶,約束城市邊界的無限擴張,防止城市過度蔓延,促進城市精明增長,并防止城市發展過度侵蝕鄉村地域系統,避免形成“似城似鄉、非城非鄉”的普遍性景觀怪象。
(二)加強城鄉聯系功能——加快產業融合與保障消費需求
城鄉結合部農業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城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城市消費者對農產品的要求不僅僅是普通的產品,更注重農產品的生態環保價值、食品安全貢獻,以及精細與多元化的加工手段;對農業的消費需求也不僅限于農產品購買,還包括觀光、體驗、求知、休閑娛樂等服務性產品的購買。即使農業生產是城鄉結合部地區最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但它依然是附近城市的放松空間[54]。城市地區的參觀者會用一種非正式的方式來利用城鄉結合部景觀,如享受公共空間活動[55],他們很看重城鄉結合部農業所具有的休閑娛樂價值。因此城鄉結合部農業可以是高端農產品生產、多元化深加工與現代服務的集合。
城鄉結合部農業因臨近城區,在發展過程中便于從發達的城市二、三產業得到資金、設備、技術、信息、人才和市場等方面強有力的支撐,有效融入現代城市產業體系,也便于將農業相關經濟活動,如農業會展、農業科技、農業教育、農業文化、農業旅游與農業物流等與城市現代二、三產業有機結合起來,并通過這些建立起城鄉之間、農業和非農產業之間的交流與聯系,促進城鄉融合與區域一體化發展。在現代都市農業發展的基礎上促進城鎮化對鄉村地區的輻射與帶動。
(三)提升城鄉發展功能——促進新增城鎮化人口就業與發展
特殊的區位與功能決定了城鄉結合部農業區別于傳統的鄉村農業。城鄉結合部農業高端、精細、產品多元化、產業鏈長,與非農產業的融合更深入、更廣泛,能創造的就業崗位自然也比大宗農業生產更多。城鄉結合部地區由于處于城鎮化的前沿,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大量失地農民,外部涌入的鄉村農業轉移人口也主要分布在城鄉結合部地區。而無論是被征地的城郊農民還是鄉村農業轉移人口都具有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對農業相關部門的就業適應性更強。據作者之前對城鄉結合部的深入調查,因缺乏就業競爭力,城鄉結合部地區存在著非常嚴重的本地失地轉居人員和外來人口的非正規就業問題,并由此引發一系列經濟、社會與環境問題。城鄉結合部農業及其衍生的相關產業部門對于我國現階段安置無資金、無技能、無就業出路的傳統農業轉移人口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協調城鄉關系功能——互相利用優勢資源與保護文化景觀
城鄉結合部地區是城鄉要素融合的重要陣地,但也存在著激烈的城鄉沖突與矛盾。除了城市擴張帶來的農用地減少與破壞,農業經濟被非農經濟所替代外,農業發展質量上也會因城市三廢排放等受到生態污染及其他問題而出現顯著下降。而事實上,城鄉結合部農業可以利用鄰近城市的區位優勢,充分利用城鄉資源優勢,促進城鄉關系協調發展。例如,城市廚余垃圾回收利用、人口糞便資源開發等對農業經濟生態的影響,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城鄉結合部農業生產效率,改善農產品品質,另一方面,又有助于解決城市生活廢棄物處理的巨大難題[56]。而且農業是與當地自然生態環境結合最緊密的人類經濟開發活動之一,區域特色顯著,城鄉結合部農業的適當保留與發展有利于保護并延伸區域特色文化與景觀,減少因城市侵蝕對鄉村文化與景觀的破壞,真正實現“記得住鄉愁”的城鎮化。

圖2 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體系
四、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實現途徑——創新生產經營模式
相對于鄉村地區,城鄉結合部農業用地的資源稀缺性更加顯著、價值更高、擔負的職能也更多。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是多元的,但是各項功能之間并非單純并列關系,而是相互協調、共同促進。因此,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應注重各項功能的匹配與協調,以便于最大程度地實現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
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的最終實現,需要創新生產經營模式。綜合循環農業、生態農業、觀光農業、科技農業、文化農業、會展農業等生產特點,建立一種具有更高層次、更豐富內涵的新型城郊農業生產模式(圖3)。城鄉結合部農業生產的對象是高端、精細、營養、創新型農產品,消費者目標群聚集為城市中高收入階層,并通過與休閑、旅游、文化、教育、科技、會展、信息、物流配送、現代制造等產業深度融合顯著提升產品附加值。從而使城鄉結合部農業超越于傳統意義上單純的食品供給和生態屏障價值,成為城鄉和三次產業間有機融合的重要紐帶和吸納新增城鎮化人口就業的重要載體。不僅有利于避免與緩解目前普遍困擾城市的城鄉結合部“臟、亂、差”問題,還有利于通過產業鏈延伸和新業態興起拓展城市現代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空間。
現代化農業企業應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農戶通過不同的形式加入其中或者進行合作,具有農業技能的鄉村轉移人口和失地農民可以以新型農業產業工人等身份參與到城鄉結合部農業的發展之中。而且,對大多數城鄉結合部農業工作者而言,他們的身份可以是兼職的,即農業并非其唯一的工作領域。
五、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實現程度初步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城鎮化進程,僅用22年(1981-2003年)就將城鎮化率從20%提高到40%,而英國完成這一過程用了120年,法國100年,德國80 年,美國40 年[57]。如此快速的城鎮化主要是建立在城市空間擴張基礎之上。1978-2011年,上海、北京、廣州、天津、南京、杭州、重慶、西安等特大城市建成區面積分別擴大了8.0、6.5、14.5、7.8、8.1、15.3、17.8和4.1倍[58],2001-2010 年,地級以上大中城市建成區面積平均增長85%-90%[59]。在此背景下,我國中等規模以上城市普遍出現城鄉結合部農用地被改變用途,農業發展遭受重創的現象。而規模較大城市由于要素高度集聚,城市空間擴張更為迅速,更突出反映了城鄉結合部農業發展中的問題及演化趨勢。本文將選擇北京、長沙、成都等大型城市的相關數據對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實現程度加以分析。

圖3 基于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
(一)生態約束與保護功能實現程度
近年,在日趨嚴峻的生態形勢下,城市綠化建設越來越受到重視,而城鄉結合部地區作為中心城區的外圍屏障自然成為綠化建設的主要陣地。例如,北京在城鄉結合部地區建設兩道綠化隔離帶,林木覆蓋率呈上升趨勢。此外,針對城鄉結合部地區的生態治理與環境建設也發揮了一定的生態約束與保護功能。如成都城鄉結合部的機投橋街道成立環保科、配備環保專職人員和環保設備,并推行多層次立體化環保網絡化管理,以加強結合部地區的環保治理、宣傳與保護等[60]。但是,城鄉結合部綠化與環保政策實施難度很大,收效遠不及預期。北京規劃2004年之前建成的第一條綠化隔離帶至2007年底共實施綠地約110.4km2,僅占規劃綠地的66%。而且,盡管城市綠化建設使林地總面積有所增加,但原有天然次生林或成熟人工林的大幅減少所導致負面影響不容忽視[61]。
另外,在城鄉結合部居住用地、建設用地和工礦用地增長迅猛,農用地嚴重萎縮背景下,農業本應發揮的生態約束與保護功能難以實現。如長沙城鄉結合部東岸鄉多數村子農業用地僅10%左右,有些村子甚至已幾乎沒有耕地[62]。而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世界城市不僅在工業發展、城市擴張對土地需求巨大的背景下,仍保留著廣闊的農業空間,而且在強化生態管理和多功能開發的過程中,非常強調農業的生產功能并不斷創新農業生產形式。如巴黎11963平方公里的都市近郊和遠郊土地,農業用地依然占50%,而且在農業用地中,各類農作物用地占97%,草地、果園和花卉用地占3%[63]。
(二)就業拉動與滿足消費需求功能實現程度
首先,城鄉結合部農產品供給能力普遍下降。例如,目前國內大城市蔬菜自給率不足30%,北京本地蔬菜的供給率約20%,最低時僅10%,而早期在規劃部門確定的城鄉結合部地帶,蔬菜基地生產的本地市場供應率曾達30%-40%[64]。
其次,城鄉結合部農業休閑、娛樂功能與需求匹配程度有待提高。有些城市的城鄉結合部地區,如成都三圣“五朵金花”休閑觀光農業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不僅滿足本地城鎮居民的休閑娛樂需要,還吸引了大量國內外游客,發展成國家4A級風景名勝區,顯著提升了成都市旅游總體實力,并拉動本地區經濟快速發展。近年年均接待游客900萬人次左右,年產值達1.8億元,村集體收入超3000萬元,解決近萬個農民就業安置[65]。但在其他更多城市,城鄉結合部觀光、休閑農業功能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出現減弱。如北京2008-2014年城鄉結合部農業觀光園累計減少62個,高峰期從業人員數量波動減少,農業觀光、休閑接待能力持續下降。與此同時,城鎮居民到城市邊緣區進行農業觀光與休閑消費的需求卻在急劇上升。調查顯示,95%的市民希望到郊區旅游、觀光和度假,近1/3市民愿意將雙休日用于郊區旅游,休閑農業已成為城市居民常規化、周期性調節生活方式的重要選擇之一[66]。
再者,城鄉結合部農業就業拉動能力顯著不足。伴隨著農業用地的減少,城鄉結合部農業從業人員數量大幅減少,除了部分年輕人轉向非農產業就業外,許多失地農民實際陷入隱形失業狀態。此外,快速城鎮化背景下大量鄉村轉移人口進入城市,其中多數落腳城鄉結合部地區。據作者在北京海淀區城鄉結合部的實地調研,本地失地農民中,超過50%的人員沒有就業,以房租為主要收入,外來人口中非正規就業比重高達35%-56%[67]。城鄉結合部農業及其相關產業的發展未能成為安置新增城鎮化人口就業的有效途徑之一。
(三)產業融合與經濟聯系功能實現程度
截至目前,多數城鄉結合部在升級改造過程中,農業被擠壓在很小的空間,大量農村資源遭到破壞和浪費,城鄉產業融合十分有限,與城市消費和現代產業關系密切的農業部門未能得到很好的發展。如近十年來,北京城鄉結合部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僅為2%左右。觀光農業、民俗旅游等與休閑農業相關的經濟活動普遍存在產品單一、經營趨同、附加值低等問題,2014年人均消費僅為167.7元,不及同期全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人均消費水平的1/2。
值得肯定的是,近來有些地區開始注重這方面的探索。如地處北京東北五環的崔各莊鄉未來幾年將落地三大項目——鄉鄰小鎮樣板、創新創業孵化基地、世界級農業公園,打造城鄉融合、生態發展、智慧城鎮的典范,使世界上頂尖農業科技、農業成果、農業創意匯聚至此,并導入生態環保產業、旅游服務產業、文化教育產業、健康養生產業和生態農業產業,吸引更多的城市人到鄉村創業,到鄉村消費[68]。
(四)資源利用與文化保護功能實現程度
目前,我國城市廢棄物在城鄉結合部農業中的利用率非常低。據科學測試,化學肥料的無節制使用導致每年2%的耕地失去耕作能力[69]。而與此同時,城市廢棄物處理形勢嚴峻,2011年,657個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率為91.1%,其中20.1%為直接堆放或簡易填埋。以當年城市垃圾清運量1.64億噸計算,當年已堆積未處理的垃圾近5000萬噸[70]。實際上可以利用卻被浪費掉的城市資源還有很多,目前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尤其未能實現與城鄉結合部農業生產的對接。
由于目前城鄉結合部改造的總體思路是促進其完全城市化,農業及其相關經濟活動未能得到應有的保護,鄉村經濟、文化、社會景觀也逐漸消失,被缺少特色的現代化城市景觀所取代。
六、結論與討論
有學者指出,對城鄉結合部的“低價值判斷”及其“被動整治”策略是該區域產生與遺留諸多問題的根源。應重新審視城鄉結合部的綜合價值,“以功能帶動價值,以價值帶動整治”,在“發展”中解決問題[71]。
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城鎮化水平已非常高,但是其城市、非農產業的發展與農村、農業和諧共存、交融分布,發展的一體化程度很高。而我國卻存在著較嚴重的“城市偏向”,快速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鄉村,尤其城鄉結合部農業、農地、農民的利益受到嚴重沖擊,反過來又制約了工業化、城鎮化的健康持續發展。
城市邊緣區農地通常具有土地肥沃、地勢平坦、灌溉便利、生產科技含量高、經營手段現代、鄰近消費市場等突出優勢。農業與城鄉結合部地域雙重功能作用下,城鄉結合部農業具有豐富、多元及深層次的地域功能,我國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更是在生態文明、以人為本、城鄉統籌、協調發展方面具有積極的意義。深入研究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論證保障城鄉結合部農業適度發展的必要性,并探討有效發揮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的途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本文認為,現階段,我國城鄉結合部農業在約束城市邊界擴張、降低城市發展對鄉村地域侵蝕破壞、保護城鄉生態;滿足城鎮居民食品安全與高層次休閑文化消費需求;促進失地農民與外來人口就業安置與長期發展;加強城市與周邊鄉村產業融合與要素流動;實現城鄉資源交互利用與文化保護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域功能。現實資料與統計分析表明,我國城鄉結合部農地流失迅速,農業地域功能被嚴重低估與忽視,價值遠未得到應有的發揮,潛在的不良影響較為嚴重。充分認識城鄉結合部農業的地域功能是保護大城市邊緣農業用地的重要依據與驅動力,而促進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的實現又是落實新型城鎮化和科學發展觀理念的重要途徑之一。
由于研究階段與篇幅限制,本文著重論述了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的理論基礎、核心內涵與構成體系與實現價值等,對我國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的實現程度僅停留在案例描述和統計分析層面。接下來,作者擬構建城鄉結合部農業發展指數并進行測算,一方面為定量衡量與判斷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實現程度提供支撐,另一方面將揭示并對比我國不同規模、不同地區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的實現水平,更準確地把握態勢、發現問題,并最終為增強對城鄉結合部農業價值的認識及其地域功能的有效實現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Chen Y Q. Discussion on land use mode in rural-urban fringe [J]. China Land Science, 1997,11(4): 32-36.
[2]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potential croplands study [M]. Washington, D.C., 1975.
[3]王立彬.中國為大城市擴張劃出紅線 [DB]. 新華網,2014-11-03.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03/c_1113094804.htm.
[4]Wu J J, Fisher M, Pascual U. Urbanization and the Viability of Local Agricultural Economies [J].Land Economics,2011,87 (1): 109-125.
[5]Brinkley C. Evaluating the benefits of peri-urban agriculture [J].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012, 27(3):259-269.
[6]Henderson S R. Agricultural adaptation to real regulation on the urban fringe: the chicken meat industry’s response to land-use conflict in the western port region of Victoria, Australia [J]. Australian Geographical Studies, 2003,41(2):156-170.
[7]Sarah W J. Protecting Sydney’s peri-urban agriculture: moving beyond a housing/farming dichotomy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52(4): 377-386.
[8]Benoit A D, Todd H K, Al Lochen G S, Bills N L, Boisvert R N. Estimating agricultural use values in New York State [J].Land Economics, 1978,54(1): 50-63.
[9]Shi Y J, Phipps T T, Colyer D. Agricultural land values under urbanizing influences [J]. Land Economics, 1997, 73(1): 90-100.
[10]Benoit A D, Todd H K, Allison M B. Identifying the extent of the urban fringe and its impact on agricultural land values [J]. Land Economics, 2014, 90(4): 587-600.
[11]Coughlin R E. Farming on the urban fringe [J]. Environment, 1980, 22(3): 33-40.
[12]Bryant C R. Agriculture and urban development [C]. In Pacione, M. (ed.) Progress in Agricultural Geography. Croom Helm, London, 1986: 167-194.
[13]Bryant C R. The role of local actors in transforming the urban fringe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1, 1995,255-267.
[14]Moran W, Blunden G, Workman M. and Bradly A. Family farmers, real regulation,and the experience of food regimes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6, 12: 245-258.
[15]Berry D, Plaut T. Retaining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under pressures: a review of land use conflicts and policies [J]. Policy Sciences, 1978, 9:153-178.
[16]Adrianto D W, Aprildahani B R, Subagiyo A. Trackling the sprawl, protecting the parcels: an insight into the community’s preference on peri-urban agricultural preservation [J]. Space and Flow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Extra Urban Studies, 2013, 3: 115-125.
[17]Jaeger W K, Plantinga A J, Grout C. How has oregon’s land use planning system affected property values? [J].Land Use Policy, 2012,29 (1): 62-72.
[18]Eagle A J, Eagle D E, Stobbe T E, Kooten G C. Farmland protection and agricultural land values at the urban-rural fringe: British Columbia’s Agricultural Land Reserve [J]. Amer. J. Agr. Econ. 2014,97(1): 282-298.
[19]李洪慶,劉黎明.現代城郊農業的功能定位與評價研究[J]. 生態環境學報,2010,19(6):1428-1433.
[20]孟召將. 生態城市建設與城郊農業功能拓展研究——兼析從化模式[J]. 城市觀察,2012(2):138-149.
[21]宋志軍,劉黎明. 我國現代城郊農業區的功能演變及規劃方法研究[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0,15(6):120-126.
[22]韓士元. 都市農業的內涵特征和評價標準[J]. 天津社會科學,2002(2):85-87.
[23]方志權,吳方衛,王威. 中國都市農業理論研究若干爭議問題綜述[J]. 中國農學通報,2008,24(8): 521-525.
[24]劉穎,許為. 都市農業理論研究進展[J]. 江漢論壇,2008(6): 69-71.
[25]齊愛榮,周忠學,劉歡. 西安市城市化與都市農業發展耦合關系研究[J]. 地理研究,2013,32(11):2133-2142.
[26]Yang Z S, Cai J M, Dunford M, Wedster D. Rethink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the “urban” economy in Beijing: an input-output approach [J]. Technological &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y, 2014, 20 (4):624-647.
[27]毋青松. 城市化進程中都市農業發展路徑創新[J]. 農業經濟問題,2013(9):34-37.
[28]謝杰. 大城市農業區域農業生產及空間結構演化發展趨勢[J]. 地域研究與開發,1996,15(1): 28-31.
[29]蔡建明,羅彬怡. 從國際趨勢看將都市農業納入到城市規劃中來[J]. 城市規劃,2004,2(9):22-25.
[30]楊衛麗,李同昇.西安都市圈都市農業發展及空間格局研究[J].經濟地理,2011,31(1):124-128.
[31]孫宏濱,孫世芳,喬敬圖,唐丙元. 城郊農業與都市農業的理論綜述[J]. 農業經濟,2001(4):37-41.
[32]馮海建,周忠學. 城市化與都市農業功能交互耦合關系及時空特征分析[J]. 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14,30(6): 57-62.
[33][德]約翰.馮.杜能 著,吳衡康 譯,謝鐘準 校. 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34]“本地食客志愿團”:倡議改變消費習慣[N]. 新華每日電訊,2007-07-03(3).
[35]楊波,生態安全視域下城市空間格局研究評述與展望[J].生態經濟,2014,30(3):67-71.
[36]McHarg L. Design with nature:garden city [M].New York:The Natural History Press,1969.
[37]McHarg L. Human planning at Pennsylvania [J].Landscape Planning, 1981, 8(2): 109-120.
[38]俞孔堅,王思思,李迪華,等. 北京市生態安全格局及城市增長預景[J]. 生態學報,2009,29(3):1189-1204.
[39]俞孔堅,王思思,李迪華,等. 北京城市擴張的生態底線——基本生態系統服務及其安全格局[J]. 城市規劃,2010,34(2):19-24.
[40]儲大建,劉冬華. 管理城市成長:精明增長理論及對中國的啟示[J]. 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17(4):22-28.
[41]陶陶, 羅其友. 農業的多功能性與農業功能分區[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 2004, 25(1): 45-49.
[42]Jordan N, Warner K D. Enhancing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US agriculture. [J] BioScience, 2010,60(1): 60-67.
[43]劉玉,鄭國楠.城鄉結合部功能定位與規劃管理的國際經驗[J].國際城市規劃,2014(4):33-37,51.
[44]Whitehand J W R. Fringe belts: a neglected aspect of urban geography[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67, 41: 223-233.
[45]Whitehand J W R. Urban fringe belts: development of an idea[J]. Planning Perspectives, 1988, 3(1):47 -58.
[46]Whitehand J W R,Morton N. Fringe belts and the recycling of urban land: An academic concept and planning practice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03, 30(6): 819 - 839.
[47]Kaika M,Swyngedouw E. Fetishizing the modern city: The phantasmagoria of urban technological network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0, 24(1), 120-138.
[48]陸大道.區位論及區域研究方法[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8.
[49]陸大道.區域發展及其空間結構[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
[50]McKenzie, F. Beyond the suburbs: 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major exurban regions of Australia[M]. AGPS, Canberra,1996.
[51]Wood R,Ravetz J. Recasting the urban fringe[J].Landscape Design, 2000, 294(10) :13-17.
[52]Brandt J, Tress B,Tress G.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landscape,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C]. Conference material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s, Centre for Landscape Research, University of Roskilde, Denmark, 2000 October, 18-21.
[53]Gallent N. 2006. The Rural-urban fringe: a new priority for planning policy? [J].Planning, Practice & Research, 21(3): 383-393.
[54]Bryant C R, Johnston T R R. Agriculture in the city’s countryside[M]. London: Belhaven Press,1992.
[55]Agger P. Access to the post-productivist landscape: the case of Denmark[C]. I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ublic Access to Natural, Agricultural Forest Areas”, Clemont-Ferrant, France, 2001. September 24-26.
[56]谷繼建,殷朝華. 關于城市人口糞便排放的資源開發對農業經濟生態影響研究—— 一種循環經濟理論的思索[J]. 中國軟科學,2010(10):57-68.
[57]陸大道,姚士謀,劉慧,等.中國區域發展報告(北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58]姚士謀,李廣宇,燕月 等.我國特大城市協調性發展的創新模式探討[J].人文地理,2012(5):48-53.
[59]姚士謀 等.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與實踐問題[J].地理科學,2014,34(6):641-647.
[60]中共成都市委黨校課題組. 城鄉結合部如何推進綠色發展——成都市上武侯區機投橋街道的實踐探索[J].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學報,2016(1):75-78.
[61]黃寶榮,張慧智,王學志. 城市擴張對北京市城鄉結合部自然和農業景觀的影響——以昌平區三鎮為例[J].生態學報,2014,34(22):6576-6766.
[62]沈欣,黃運湘,唐倩 等.城鄉結合部生態環境調查與對策研究——以長沙市芙蓉區東岸鄉為例[J].湖南農業科學,2012(10):28-30.
[63]劉娟,張一帆.倫敦、紐約、巴黎、東京四大世界城市的農業啥模樣[J].科技潮,2011(10):32-39.
[64]劉楊. “城鄉結合部”你的界度在哪里[J].中國土地,1995(10):12-14.
[65]佚名. 觀光休閑農業的標桿——成都“五朵金花”[J]. 中國鄉鎮企業,2012(4):26-31.
[66]何忠偉,曹暕. 北京休閑農業發展現狀、問題及政策建議[J]. 北京農業,2015(7):16-19.
[67]劉玉,馮健. 城鄉結合部居民經濟行為特征及空間效應研究[J]. 城市發展研究,2015,22(4):19-27.
[68]童曙泉. 崔各莊打造“最美城鄉結合部”[N]. 北京日報,2016-02-03(9).
[69]李佳霖. 全國城市垃圾堆存累計侵占土地超過5億平方米[N]. 經濟日報,2014-12-16.
[70]王聰聰. 我國超1/3城市遭垃圾圍城 侵占土地75萬畝[N]. 中國青年報,2013-07-19(8).
[71]孫心亮. 城鄉結合部問題的根源與發展策略的轉變——以北京地區為例[J]. 經濟地理,2012,32(3):132-137.
(本文責編:王延芳)
收稿日期:2016-01-25修回日期:2016-05-25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城鄉結合部農業地域功能與實現機制”(項目編號:41571160);武漢市創新崗位特聘專家資助項目。
作者簡介:劉玉(1975-),女,江蘇豐縣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城市邊緣區經濟。
中圖分類號:F2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9753(2016)06-0062-11
Regional Functions of Agriculture at Rural-Urban Fringe
LIU Yu1,FENG Jian2
(1.InstituteofUrbanAndRegionalEconomic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2.CollegeofUrbanandEnvironmentalSciences,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a large amount of farmland at rural-urban fringe disappeared.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elated sectors, and the life styles of farmers are impacted, even the whole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 of city and countryside chang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ories of agricultural location, food security, and urban ecological security, analyzes the regional functions of rural-urban fringe and the connotation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then builds a regional func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e at rural-urban fringe. The paper thinks that the agriculture of rural-urban fringe has great effec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y, countryside and fringe, especially on relieving development pressure of urban edge, meeting high-level consumer demands of urban popul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 Practice analysis shows that in China, the regional functions of agriculture at rural-urban fringe have not been recognized and realized fully. It is time for us to take time and effort to stud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gional functions of agriculture at rural-urban fringe, so that we can protect farmland and agriculture at the fringe effectively, and let it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rural-urban fringe; regional functions of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location; new-type urb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