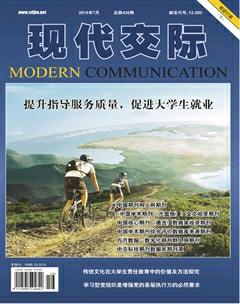淺議古羅馬共和憲政下監察官制度及其啟示
連佳
[摘要]現代政治文明發源于古希臘與古羅馬,古希臘留下了燦爛的哲學思想,而古羅馬曾靠武力與法律征服世界。在古羅馬共和國“混合憲政”下,并沒有形成古代中國從上至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而是一種分權制衡的政治架構。共和國官僚體制的逐漸發展與完善最能體現、最能反映古羅馬共和國的發展。監察官無疑是古羅馬共和國憲政中最具特色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通過對共和國時期監察官的產生、選任、職責等方面的考察,可以發現在共和國官職中監察官的神圣性,這種神圣性體現在其在權力架構中的獨特地位。雖然后來伴隨著古羅馬帝制的到來,監察官走向了消亡,但是這并不影響我們從中得到某種意義上的啟示。
[關鍵詞]羅馬共和國 憲政 監察官 啟示
[中圖分類號]DF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4-0030-02
誠如徐國棟教授所言:“古羅馬共和國通過一系列的戰爭不斷對外擴張,使古羅馬的疆域空前廣袤,其之所以崛起為當時的超級大國與其內生的良好的混合憲政緊密相關。”[1]在人類政治文明的長河中,羅馬共和國開啟了權力制衡的濫觴,元老院、執政官、公民大會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受到普遍關注。另外,執政官、獨裁官、保民官等重要官職也成為學者對古羅馬憲政研究中的重點對象。監察官作為傳統禮教的化身具有神圣色彩,它成為古羅馬共和時期比較特殊的官職,但其被研究得并不充分,實際上其產生、職權伴隨著平民和貴族的長期斗爭,其所擁有的權力對其他官職起著很大的制衡作用,從而推動著古羅馬共和憲政的平衡與發展。
一、監察官的產生
就監察官的產生而言,它首先體現了古羅馬時期平民與貴族之間的政治斗爭。公元前509年,塔克文遭到貴族聯合平民的驅逐,古羅馬從王政時期轉入共和時期。但是貴族基于自身的利益幾乎壟斷國家權力,平民的利益被冷落和忽視。但是,古羅馬的平民并沒有放棄,他們為爭取參政權從始至終不斷地與貴族進行著抗爭。貴族為了確保壟斷人口普查權,把原屬于“具有執政官權力的軍事保民官”的該項權力設法賦予了新設的監察官,并于公元前443年任命了最早的兩名監察官。
另外,監察官的產生最初可能與宗教有關,其權力是由贖罪獻祭的宗教權力逐漸轉變為政治權力。相較于其他官職,只有監察官死亡后埋葬時必須用紫色長袍包裹尸體,享受著過去王室成員才享有的特權,加之十分顯赫的地位,因此被稱為共和國時期最神圣的長官。
監察官產生之后,伴隨著平民與貴族的繼續斗爭,在公元前351年,貴族對監察官的壟斷被打破。另外,公元前339年,一項《關于建立平民監察官的普布利利亞和菲羅尼法》規定兩位監察官之一必須為平民,從此平民獲得了擔任監察官的法定地位。[2]監察官雖不具有最高統治權,但仍位列牙座,受到高度尊重。
二、監察官職權
監察官從產生之時,就具備調查人口和財產狀況的原始職能。由于人口和財產普查涉及全體民眾,所以至少每個家庭的家長都必須參加普查大會。這種普查有著嚴格的程序要求,占卜儀式結束后,每個家長說明自己身份和宣告其家庭成員以及通報所擁有的財產價值。監察官則予以評估,最后根據統計內容造成兩個花名冊,其中一個是征兵和參加公民大會的依據,另外一個是日后征稅的依據。由此可見,這雖然是監察官的一項起初看似并不重要的職權,卻關乎整個共和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基礎,對古羅馬共和國舉足輕重。
隨著共和國歷史的發展,監察官基于實踐的需要其權力不斷擴大,他們后來負責監督社會道德風尚和進行道德指導。在掌握人口和財產普查權基礎上,監察官可以對公民進行評注,凡是兩個監察官認為有違道德的行為都可記錄在案并且說明理由。監察官的這種評注和記錄影響極大,公民可能因自己的行為不檢點被懲處“喪失名譽”,還有可能被懲處降低公民等級,被排除公民大會之外。這一方面說明古羅馬共和國公民對于傳統道德的推崇和重視,另一方面說明了監察官所擁有的道德監督權在古羅馬共和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到,由于缺乏明確的規定,造成了監察官在實踐中具有較強的隨意性和主觀色彩。
公元前312年,監察官又獲得了遴選元老之權,可以修改并確認元老的名單。這集中體現在監察官將作為共和國權力中樞的元老納入監察的范圍,可以把不合格的元老從元老院中清除出去甚至取消候選人入選元老院的資格。另外,監察官依據占據主導地位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而非法律去行使此項職權,由于這種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有時并不明確,監察官可以自由解釋,他人并不得干涉,無權申訴,保民官的否定權也無效。后來,根據一項平民大會的決議,監察官也有權從平民和貴族兩個階層中為元老院選拔最優秀的市民成為元老。這足以充分反映出監察官在道德領域的特殊權威,以及在古羅馬人眼中他們作為道德導師令人生畏的崇高地位。除上述權力之外,監察官還具有經濟領域方面的職責。為增加國家收入,他們可以將土地和資源出租給私人。另外,監察官有權采取項目承包的方式動用國庫資金興建公共工程。不過,監察官把稅收征收權也承包出去的做法似乎比較奇特。商人是逐利的,由他們負責國家稅收的征收必然會導致很多糾紛,而這些糾紛又由監察官自己處理,如果私人間發生經濟糾紛,監察官可委派審理員和仲裁人進行處理。[3]這就形成了監察官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的局面。
從上述監察官所擁有的職權及其職權的發展可以看出,其權力呈現不斷擴張性,而這種擴張恰好與平民與貴族的斗爭以及貴族和平民聯合組成新貴族的鞏固相吻合。從最初的人口和財產調查權,到后來的公民道德監督權,再發展到元老遴選權,監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顯赫。
三、監察官制度評析
古羅馬從一個小城邦擴展到后來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的龐大國家,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共和國時期穩定的憲政制度和社會經濟的繁榮為其四處征服奠定了基礎。在共和國憲政發展過程中,監察官作為羅馬官制中的一個奇特存在是古羅馬政治體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同時對羅馬共和國的憲政架構影響深遠,因此,監察官制度在古羅馬共和憲政中的角色、其權力和其他權力之間的關系很值得我們思考。
在古羅馬共和國,沒有絕對的權力,監察官也沒有例外,其具有的某種意義上的神圣權威并不意味著其權力的絕對性。就像有的學者所說,對監察官活動的唯一限制可能就在于他們的同僚制,也就是說監察官彼此之間相互有權干預同僚所進行的任何一種行為。[4]雖然這種說法有些夸張,但是在描述監察官崇高地位的同時也指出了它必須受到同僚制的約束。同僚制下,監察官不是由某一個人獨享,而由偶數個組成(一般是兩個),他們當中的每一個都是完整的擁有并行使監察官的權力,同僚之間互相平等、互相具有否決權,這就決定了他們在行使權力時,彼此之間必須得到一致認可,這種內部的橫向制約關系就決定了監察官權力的行使無法絕對。如果兩個監察官分別行事,各自制定出兩份市民名冊或者兩份元老院元老名單,并且如果這兩份名單之間是有一定差異的,那么顯而易見的是兩份名單都是無效的,從這里也看得出羅馬共和國憲制下協商的必要性。
雖然監察官作為最神圣的長官,權力和地位很顯赫,但是他們沒有被賦予治權。因此,監察官在執法的時候,他們的強制權一定程度上僅僅局限于罰金等財產方面。另外,在行使公民道德監督權的時候,監察官由于缺乏治權,并不能完全有效地實現這種對公民有時近乎嚴苛的道德監督,一定程度上要靠公民自身的道德水平。
就監察官與元老院和公民大會的關系上,前文已經提到監察官可以遴選元老和修改元老名單,監察官也可以通過行使道德監督權把認為道德敗壞的公民排除在公民等級之外而無法參加相應的公民大會。這是監察官對元老院和公民大會的制約和影響。但是,我們不能忽視元老院和公民大會對監察官的制約,比如在行使管理經濟領域的職責之時就只能根據元老院發布的命令從國庫中支取資金用于公共工程的建設。另外,監察官也實行選舉制,由公民大會選舉產生。
由上可以看出監察官集神圣、權威、崇高和受限制于一體,集中體現了古羅馬共和國政治制度下的憲政平衡理念。無論是體現出的神圣、權威或崇高,還是自身和外在的限制都不絕對,這些不同的品性雜糅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分權制衡下的特殊官制。
四、反思與啟示
縱覽中國上下幾千年的政治史,我們歷史上所存在的監察制度與羅馬共和國時期的監察官制度是迥異的。中國古代的監察官(如御史大夫)是帝王的御用工具、皇權的附庸、朝廷耳目,他對權力絕對服從而毫無獨立性可言,相反,古羅馬共和國的監察官卻獨立擁有如此重要而眾多的權力。中國古代的監察官員通常位卑權重,擁有較大的彈劾權但品級很低,而古羅馬共和國的監察官地位卻十分崇高和神圣。古代中國的監察官員通過察舉、科舉等方式被任命,毫無民意和民主基礎,而古羅馬共和國的監察官是由代表民意的公民大會通過投票選舉產生,沒有所謂“上意”的影響。
也許有人質疑這種不同政治環境下的對比意義何在,本文也認可在東西方兩種歷史背景中各自不同的監察制度的合理存在,古羅馬的監察官不也只存在于羅馬共和國期間,到了帝國時期就基本消亡了嗎?不過,通過簡單的對比,我們不僅能很明顯地發現兩種政治制度表象的不同,也可以反思其背后迥異的政治文化。
我們往往強調從外部監督出發加強對權力的控制和約束,有時候卻忽視了作為第一道防線的行政系統內部的有效制約。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形式上比較系統和全面的行政監督體制,雖然對遏制腐敗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仍存在很多問題。首先,由于我國很多情況下把行政監督主體放在行政機關內部,并且地位較低,缺乏權威性和獨立性,造成了監督主體依附于監督客體的局面,作用很難發揮;其次,我國現行的行政監督體制與黨委、司法機關、人大等外部監督制度之間的銜接和融合還不夠;最后,在行政監督方面的立法和相關制度很是不足,例如學者和社會呼吁很久的“官員財產申報和公開”方面的立法和制度一直處于空白階段。因此,為了增加行政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應該針對現行的行政監督體系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改革。第一,把現在行政監察機關雙重領導制改為垂直領導制,下級只對上級負責,地方直屬中央,這樣可以增強監察機關的獨立性。第二,加強行政監督立法,盡快出臺“官員財產申報和公開”等方面法律法規,并且對《行政監察法》中不符合實踐要求的內容進行刪改。第三,為改變內部行政監督逐漸虛無化的趨勢,一方面要明確自身的定位,立法上可以適當擴大監察機關的權力,另一方面是注意與黨委對黨員干部的監督制度、檢察機關和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公務人員監督制度的銜接,做到相關案件內部發揮作用、外部及時移交等。
【參考文獻】
[1]徐國棟.羅馬共和混合憲法諸元論[J].北大法律評論,2013,14(02):287.
[2]李陽華.古羅馬監察制度及其評析[J].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08(04).
[3]陳可風.羅馬共和憲政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8-80.
[4]弗朗切斯科·德·馬爾蒂諾(著),薛軍(譯).羅馬憲政史(第二卷)[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