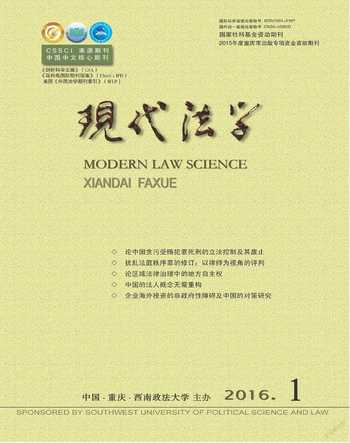企業海外投資的非政府性障礙及中國的對策研究
張曉君 孫南翔
摘要:
除來自東道國政府的各種政治、法律和經濟障礙之外,近年來中資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也遭遇過大量非政府性障礙,其中,環境責任、勞工標準、文化保護、當地“經濟貢獻”和正當行政程序為其主要表現形式。東道國投資環境寬松、我國海外投資管理模式落后、中資企業逐利本性是產生非政府性障礙的主要原因。投資母國防范海外投資非政府性障礙風險的關鍵在于系統和靈活運用國際與國內兩套規則,注重法律保護,我國在新簽訂或修訂的雙邊或多邊投資協定中應增加投資標準條款,督促東道國政府承擔保護的責任,并通過構建企業海外信息披露制度,促使投資母國與當地民眾、非政府組織實行“共同管制”,此外,還要激勵中資企業自覺遵守社會責任,進而在東道國樹立起負責任的中資企業形象。
關鍵詞:非政府性障礙;中資企業;海外投資;風險防范
中圖分類號:DF96
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1.13
引 言
2014年11月,迫于國內壓力,墨西哥總統培尼亞·涅托宣布取消由中國鐵建公司牽頭中標的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羅的高速鐵路項目(以下簡稱墨西哥高鐵項目)。在該項目被取消前,墨西哥通訊與交通部部長埃斯帕扎公開強調該招標程序符合法律要求。墨西哥高鐵項目事件在我國國內引起軒然大波,然而該情形并非個例。2011年9月,根據當地民眾的意愿,緬甸政府表示在本屆政府任內擱置興建伊洛瓦底江密松水電站項目(以下簡稱密松水電站項目)。根據中緬政府簽署的《關于合作開辟緬甸水電資本的框架協定》,密松水電站由中國電力投資集團以BOT模式投資建立。自從密松水電站開工建設以來,當地民眾、非政府組織的抗議活動持續不斷,迫于壓力,緬甸政府緊急叫停密松水電站建設。除此之外,還有多起事件發生,如柬埔寨暫停中國公司承建的西南部地區水壩工程,緬甸北部蒙育瓦鎮當地人抗議中緬合資的萊比塘銅礦,厄瓜多爾當地民眾抗議中資礦業公司的商業行為,以上事件的發生與發酵已然構成中資企業新型的海外投資障礙。
上述類型的海外投資障礙可被歸為“非政府性障礙”。“非政府性障礙”是指除當地法律政策規定與政府管制外的其他投資障礙,主要是由于超越法律之上的原因,東道國公民或非政府組織排斥、反對外國企業投資與運營的現象
其他概念包括“非法律政策障礙”、“超越法律的障礙”、“法律外的障礙”(extra-legal barriers)等。“非政府性障礙”并非是“法律之外的障礙”,其不包括由東道國政府施加的非法律障礙,例如東道國政府實施的隱性環保標準、投資認證標準等。(參見:盧進勇,李鋒,溫麗琴.中資企業對外投資遭遇的非政策法律障礙分析[J].國際貿易,2012(9):11-12;周林彬, 何朝丹.試論“超越法律”的企業社會責任[J].現代法學,2008(2):37;Jeffrey N. Lavine. Foreign Investment in Japan: Understanding the Japanese System and Its Legal and Cultural Barriers to Entry[J].Bos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91(9): 161-165.)。例如,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受到緬甸政府的歡迎和邀請而投資密松水電站項目,然而,當地民眾和非政府組織對投資企業、東道國投資事項等產生強烈的不安心理,進而通過抗議等方式迫使緬甸政府主動違約,以尊重國內的“民意”。與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民族企業利益訴求、國家安全等東道國政府對投資者施加的投資障礙不同,近期中資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障礙主要源于企業與當地民眾及非政府組織之間的緊張和矛盾關系,這是典型的非政府因素
在對發達國家的投資中,中資企業面臨的障礙主要是企業的身份認同。發達國家政府部門經常對我國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身份問題百般糾纏,實為貿易保護,主要體現為東道國政府與企業的矛盾;在發展中國家,當地民眾對我國投資企業的信任感缺失,主要表現為當地民眾與中資企業之間的矛盾關系。。鑒于此,下文擬以近期中資企業海外投資遭遇的非政府性障礙分析為出發點,探尋中資企業遭受非政府性障礙的主要成因,批判性地借鑒投資母國防范企業非政府性障礙風險的國際經驗,最終提出保障海外投資者
合法利益的應對之策。
一、中資企業海外投資非政府性障礙的表現形式
海外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自進入21世紀以來,中資企業積極主動地開展對外投資活動。2014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就高達1160億美元[1]
,其中,絕大多數流向發展中國家。然而,在海外投資蓬勃發展的同時,中資企業遭遇當地民眾抗議的情形不時發生。根據當前的客觀實踐,造成非政府性投資障礙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五種:
(一)環境問題引發的非政府性障礙
環境保護的中心價值要求盡可能地減少使用自然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2]。自然資源開發具有高收益、環境敏感和經濟利益沖突等特點,甚至在一些非洲國家,自然資源還曾引發國內戰爭或武裝沖突[3]。自2010年7月起,我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國[4]
。相應地,我國經濟對原材料需求旺盛,眾多中資企業在世界范圍內以獲取資源為目的尋找合適的廠址,其所獲資源多數直接服務于我國經濟發展。我國投資者在發展中國家遭遇的抗議也集中反映在能源投資領域。具言之,遭抗議的投資領域主要分布在水利工程、采礦業、制造業和基礎工程建設等行業。部分東道國民眾認定中資企業開采資源的行為是為了轉嫁污染和環境治理成本,并對當地的生態環境構成威脅。環境保護威脅是引發中資企業非政府性障礙的主要形式。
(二)勞工關系引發的非政府性障礙
由于我國勞工制度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勞工制度存在差異,中資企業在海外投資中不擅長應對和解決海外投資中的勞工問題[5]。因此,勞工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資企業與東道國當地民眾間的矛盾。少數中資企業與當地勞動者之間的勞動爭議時有發生,稍有差池,極易導致群體性行為,如罷工、游行等。國外的工會組織大多能夠影響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甚至在勞動者罷工、抗議活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多數中資企業未能搭建起與當地工會等組織有效溝通的平臺。同時,國外的非政府組織經常在各大抗議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而中資企業也鮮少與相關的非政府組織溝通。在實踐中,簡單的勞工糾紛時常演變為具有巨大影響的抗議事件。
(三)文化沖突引發的非政府性障礙
文化差異向來被視為投資領域法律外障礙的重要因素。由于語言障礙,我國海外投資者鮮少能全面了解東道國的文化傳統。以緬甸水電站項目為例,克欽人將密松視為文明發祥地,“二水環山”的密松河曲形象在當地民眾內心具有崇高的地位。當地民眾反對密松水電站開工建設的理由包括項目建設將摧毀克欽本地文化、改變緬甸民眾與河流相伴而生的傳統文化[6]。文化與民眾日常生活休戚相關,在宗教國家中,相當一部分人還將宗教文化視為畢生的信仰。在海外投資過程中,中資企業由于缺乏對當地傳統文化的關注和重視,不僅導致當地民眾的內心反感,更直接引發民眾對企業的抗議行動。
(四)當地“經濟貢獻”引發的非政府性障礙
由于投資活動的跨國性以及設立企業的形式各異,當地民眾對他國投資者的認同感普遍較低。若投資企業未能有力地推動地方經濟發展,促進當地居民的就業,在貿易保護主義思想的鼓動下,民眾經常會認為外國投資者搶奪本國資源,外國人搶占本國人的工作崗位。我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多是從事能源開發和基礎建設工程承包等項目,主要輸出資本和技術,屬于資源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由于產業特性,當地民眾的從業人員覆蓋面較窄。同時,在海外投資中,中資企業多組成國內項目團,由多家國內企業共同控股,而較少與當地企業進行聯合[7]
。例如,在墨西哥高鐵投標中,中鐵建公司牽頭數家中資企業遠赴墨西哥建設高鐵。當地“經濟貢獻”不足易引發民眾滋生對企業的不滿情緒。
(五)正當行政程序引發的非政府性障礙
借由經濟全球化風潮,西方國家的“正當程序”概念和憲政文化觀念傳播至世界各地。在此背景下,發展中國家民眾的“公民意識”不斷覺醒。行政法層面的正當程序原則導出避免偏私、行政參與和行政公開三項基本內容[8]
。當前,多數發展中國家處于逐步政治轉型階段,由于缺乏西方文化的長期熏陶和完善的制度基礎,在西方觀念的沖擊下,民眾容易產生對東道國政府的信任危機,進而將負面情緒轉嫁至與當地政府關系密切的海外投資企業。該情形主要表現為:在缺乏公眾參與、透明度等機制的背景下,當地民眾不信任政府的環境評估報告、調查報告、監管報告等。若未能及時處理并化解危機,投資企業與公眾的矛盾隨時可能被激化。在墨西哥高鐵項目中,雖然根據法律規定,中資企業作為唯一投標方符合法定程序,然而當地民眾仍對程序的正當性和合法性進行質疑,最終導致該項目被取消,無疑反映了當地民眾對本國正當行政程序的疑慮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對民族利益的關注,有些國家甚至提倡“資源國家主義”(resource nationalism),傾向于全面排斥與拒絕外資企業參與本國資源的開發活動。(參見:A. F. M. Maniruzzaman. The Issue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Risk Engineering and Dispute Management in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J].Texas Journal of Oil, Gas and Energy Law,2009(5): 80-86.)。
二、中資企業海外投資非政府性障礙的成因
近期中資企業所遭遇的投資困境主要表現為超越法律的非政府性障礙,雖然中資企業的投資事項符合東道國政府的實體性和程序性法律規定,然而,我國海外投資企業時常忽略與東道國當地民眾的交流和溝通,忽視當地民族文化以及民意訴求。毋庸置疑,非政府性障礙的成因是多層面的,包括外部政治勢力的介入和國內政治集團的對抗。然而,在錯綜復雜的政治沖突外,東道國的投資環境、投資母國的監管模式以及投資者的自利驅動也是非政府性障礙存在的原因,并成了東道國國內外政治勢力阻礙中資企業投資的“正當”借口。
(一)東道國政府寬松的投資環境
我國對外投資主要流向地為拉丁美洲、非洲和東南亞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甚至為最不發達國家,其經濟水平相對落后,且面臨著維護民族獨立、發展經濟的艱巨任務[9]。由于面臨多重壓力,環境保護往往不是當地政府的首要任務,即使存在環境保護相關立法,也在執行和監管力度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顯著差距[10]。因此,東道國投資環境趨于寬松,具體體現為環境標準較低、薪資水平不高、政府疏于監管等方面。在特定情況下,東道國政府還傾向于降低本國環境、勞工等標準以吸引外商投資[11]。另一方面,東道國政府的行政權力卻往往較大,政府能夠對國內經濟、行政事項進行直接干預,外商投資審批很少有公開聽證、公眾參與等正當行政程序要求。
為吸引外資,東道國規定的環境保護、勞工標準相對寬松,甚至還向外國投資者提供“超國民待遇”,如企業稅收減免等。然而,在國內民眾抗議事件發生后,東道國政府卻不能有效履約,甚至不能承擔保護外國投資者和投資財產安全的國家責任。東道國政府的投資優惠與事后違約相輔相成,是非政府性障礙產生的直接動因。
(二)投資母國管制責任的缺位
投資母國對海外投資企業享有一定的管轄權
從國際實踐來看,普遍接受的國家管轄權原則有地域原則、國籍原則、保護原則。即使確定了管轄權,針對法人國籍的認識,不同國家或組織也采取不同的認定標準,有設立地規則、住所地規則、準據法規則、資本控制規則和復合標準規則等。總體而言,投資母國對海外投資企業具有合法的管轄權。。與管轄權相對應,投資母國對本國企業的域外行為負有國際法層面的母國管制責任。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曾專門建議在雙邊投資條約中增加投資母國義務的規定。
作為對外投資的新興大國,在現有法律體系下,我國尚未承擔起應有的母國監管責任。例如,雖然我國將企業社會責任寫入新修訂的《公司法》,然而其無法規制對外投資的企業
我國《公司法》第5條明確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修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公司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規制的對象僅為“依照本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同時,我國《公司法》主要規制企業的域內行為。。截至目前,我國并沒有一部系統的對外投資法,也沒有完整的對外投資法律制度,監管海外投資企業的規定散見于零星的規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文件中。以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的指導意見為例,2008年1月,國資委發布了《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該意見指出我國中央企業負有如下責任:堅持守法經營誠實守信;不斷提高持續盈利能力;切實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加強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推進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保障生產安全;維持職工合法權益;參與社會公益事業[12]
。國資委意見對中央企業對外投資也有指導意義[13]
,然而,該指導意見并沒有法律效力,性質為倡導式的企業自愿宣言。
顯然,我國并未承擔起對投資企業域外行為的監管責任,在東道國政府投資環境寬松的前提下,若投資母國不能對企業實施嚴格的要求,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往往為降低運營成本,損害當地勞工關系、破壞生態環境,進而引發當地民眾與中資企業的沖突。
(三)海外投資企業社會責任的缺失
晚近以來,隨著跨國公司數量的增加,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愈發受到關注。通過將企業視為“公民”,作為“擬制人”的企業應承擔服務社會的功能
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意涵在于企業追求利潤之外,對與其經營相關或受其經營影響的個人和集體所承擔的超越法律的、道義的和社會公益的責任。(參見:Krista Bondy, Dirk Matten & Jeremy Mo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Codes of Conduct: Governance Tools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Corporate Governance,2008(16): 295;Jennifer Oetzel, Kathleen A. Getz & Stephen Ladek.The Rol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Responding to Violent Conflict: A Conceptual Model and Framework for Research[J].American Business Law Journal, 2007,44:335;盧代富.國外企業社會責任界說述評[J].現代法學,2001(3):143; 蔣建湘.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化[J].中國法學,2010(5):124.)。然而在實踐中,企業經營者對經濟責任、法律責任的認同仍高于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8]。
我國海外投資企業也未能全面參與到當地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大體而言,中資企業能夠自覺以東道國的法制水平規范投資行為,但是,與當地企業相比,外商投資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偏低,更何況中資企業習慣于“單打獨斗”,甚至不了解東道國的風俗與習慣。由于文化差異、語言障礙和行業的特殊性,中資企業及其中國籍員工與東道國當地民眾接觸較少[15]。例如,在非洲國家,當地居民指出,相比于西方國家企業的行為,企業社會責任并不是中國投資企業商業計劃的內容之一;同時,中資企業鮮少參與社區事務或者當地社會活動,更沒有公開或討論環境保護和人權措施[16]。
廣義的企業社會責任包含企業透明度的要求[17]。 透明度原則的內涵要求利益攸關方能夠獲得與其利益相關的重要程序、計劃和行為的信息,而不僅限于程序或計劃的制定者和執行者。目前,國際人權保護組織積極推動跨國企業透明度建設[18]。在我國對外投資中,企業的透明度問題比較突出[19]
。由于信息不對稱,當地民眾可能產生對中資企業環保標準、勞工標準的疑慮,進而迫使投資項目下馬
如2011年在肯尼亞,當地民眾由于不能與中資企業順暢溝通,最終只能采取抗議的方式。(參見:Kirk Herbertson. Leading While Catching Up: Emerging Standards for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s[J].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 & Policy, 2011(11): 22.)。當然,透明度要求不僅體現在企業運營過程中,在企業先期籌備階段,對環境影響的分析、預測、評估和結果公布過程也均應體現透明度。
近期中資企業海外投資屢遭當地民眾和非政府組織的抗議,歸根結底,成因主要體現在企業與當地民眾的關系上。具而言之,由于中資企業的行為違背了當地民眾的預期,企業與非政府組織、當地民眾本為“榮辱與共”的關系才逐步惡化。
三、投資母國消除海外企業非政府性障礙風險的國際經驗
中資企業面臨的非政府性障礙或可直接歸因于東道國政府的違約行為,然而,單獨依靠東道國行政和司法救濟無法消除中資企業面臨的非政府性障礙的風險,更無法確保未來的中資企業不再面臨相似的尷尬處境。從本質而言,處理中資企業海外投資的非政府性障礙不能僅依靠東道國政府,也應該從投資母國的角度考察防范和化解中資企業非政府性障礙風險的方式。
(一)投資協定約束東道國管制責任
作為調整跨國投資行為的專門協議,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以下簡稱BIT)或國際投資協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以下簡稱IIA)的關注點已從外商投資保護轉向消除政府性投資障礙,發展至今,第三代投資協定則更強調國家管理社會或環境為目的約束企業行為的權利
參見:Federico Ortino.The Social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Draft a New BIT/MIT Model?[J].International Law FORUM du droit international,2005(7):243; Mary E. Footer.BITs and Piece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J].Michigan Sta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9(18):38-43.。申言之,第三代IIAs或BITs旨在實現投資者和當地民眾的利益平衡,明確東道國政府的保護和管制責任,在投資決策中將當地民眾的利益訴求納入考量范圍。具體有兩種方式督促東道國政府履行對本國國民的責任:一是在不構成投資障礙的情形下,明文規定東道國政府對環境措施的規制權,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第1106條允許政府采取保護環境所必需的行為
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第1106條第6款之規定,在遵守關于此類措施的實施不以恣意的、不公正的和不構成對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變相限制的情形下,第1(b)、(c)款和第3(a)、(b)款不應理解為阻止成員方采用或維持以下措施,包括環境措施:(a)為保證與本協定不相抵觸的法律或法規得到遵守所必需的;(b)為保護人類、動植物生命或健康必需的;(c)為保護生命的或非生命的可耗竭自然資源所必需的。; 其二為規定 “標準不得降低”條款(“nonlowering of standards” clause),以避免東道國肆意降低環境措施或勞工標準以吸引外資
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第1114條第2款規定:“成員方認為通過降低國內健康、安全或環境措施而鼓勵投資的行為是不恰當的。因此,成員方不應免除或毀損上述措施,或提議免除或毀損,以鼓勵投資者在其領域內設立、收購、擴張或保留投資。”。
在雙邊投資協定中,2012年《美國雙邊投資范本》第8.3(c)條和第12條分別規定了政府對環境的管制權和“標準不得降低”條款,第13條規定了勞工標準問題[20]
。將東道國政府的管制責任納入IIAs或BITs,平衡了投資者權利、國家管制權和當地民眾的利益訴求,有利于形成三方互利共贏的局面。更為重要的是,將東道國管制責任納入雙邊或多邊協定能夠產生管理和執行的法定依據,并督促締約方善意履行承諾,能夠有效實現投資者和當地民眾間的和諧關系[21]。
(二)投資母國對海外投資企業的管理機制
1.時興的“共同管制”模式
投資母國對海外企業的管制主要存在三種模式:“國家管理”模式、“自愿規則”模式和“共同管制”(coregulation)模式
“國家管理”模式盛行于20世紀70年代,投資母國采用本國規定管理跨國公司的行為。在這個時期,全球范圍內出現了制定國際法和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來管制跨國公司行為的呼吁。其后,對跨國企業的管制從以政府主導轉為“自愿規則”模式。在聯合國放棄《跨國企業行為準則》的磋商和談判之后,1999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提議制定并在全球范圍內實施具有自愿色彩的《全球契約》,通過企業自律與自愿的行動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全球契約》即是“自愿規則”模式的典范。當前,西方國家對海外投資社會責任的規制多為“共同管制”模式。。投資母國管理海外企業極易損及東道國政府的主權,而放任自由的“自愿規則”模式則容易
導致海外企業的社會責任危機。在全球治理的語境下,“共同管制”模式開始時興,其含義是通過兩個以上的利益相關者參與企業制定和執行社會責任標準的過程。通過利益攸關者與企業簽訂協定確保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與此同時,利益攸關者對海外企業進行監督。海外企業的利益攸關者包括投資母國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多邊國際組織[22]。
“共同管制”模式的創新之處在:其一,引入利益相關者參與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其二,通過簽訂協議等形式保證企業履行職責,從而將企業的自愿行動轉化為受監督的有拘束力的合同事項
對“共同管制”的模式并沒有統一見解,勞拉將企業社會責任機制分為自我管制、行業合作和共同管制,其中共同管制是指企業除外的相關人參與到制定和執行企業社會責任標準中,而不問標準的拘束力,在此廣義的定義下,企業參與全球契約也構成“共同管制”的模式。(參見:Laura Albareda.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From Self-Regulation to Co-Regulation[J].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8(8): 435.)。在實踐中,通過國內政府部門或非政府組織與海外投資企業簽署協議,超越法律的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將轉化為合同義務,進而形成多方治理的“共同管制”局面。
2.拓張的管轄權
傳統上,東道國政府單方排他地監督和管理外商投資企業在該國的活動,但晚近以來,由于經濟活動趨于交織化,基于“效果原則”(effects doctrine)的管轄權理論得到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承認和重視。其主要觀點在于賦予投資母國對投資特定事項的管轄權,進而克服地域管轄權的局限。
美國《對外援助法》、《海外反腐敗法》等立法專門對投資企業域外行為的監管和懲罰進行了規定。以《海外反腐敗法》為例,美國多次對海外企業的腐敗行為開展調查,并認定海外企業的域外活動違反本國域內法,進而給予懲罰,其中,絕大多數案件都涉及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加拿大等發達國家也都出臺了相似的法律規定,通過對特定事項的域外管轄,投資母國能夠有效消除嚴重違反國際道義的投資行為。
3.廣泛的國際知情權
增加海外投資企業透明度建設是幫助企業獲得當地民眾信任的有效方式。國際知情權(the international right to know)制度在推進美國跨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方面具有顯著功效。根據國際知情權制度的要求,總部位于美國的公司或在美國金融市場籌集資本的公司及子公司、主要的承銷商應披露在國外運營的信息,包括環境信息、人權和勞工權益相關的信息[23]。與美國《緊急事故應急計劃和社區知情權法案》中有害物質排放清單的信息披露相似,美國中心數據庫存儲跨國企業的數據,并要求企業提交電子數據,以降低透明度的公開成本。在美國,企業數據發布在國務院支持并維護的網站中。
誠然,國際知情權制度的成功或失敗并不依靠訴訟行為,而憑借公眾對網站上公布的信息的反應。除美國國務院支持的網站公布企業海外投資信息外,美國存在眾多非政府組織對企業施壓,從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進程[24]。因此,愈來愈多的美國企業通過廣告、年度報告和新聞發布會,發布域外經營活動的相關信息。除美國外,在法國、英國和挪威等其他發達國家,企業均有向股東和社會公眾披露企業社會和環境表現的義務[25]。
(三)海外投資企業的“公民”身份認知及行為規范
投資母國應該激勵具有“公民”身份的企業主動承擔起道義責任和公益責任。歐盟委員會認為:當前,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通過實施市場導向的負責任的“公民”行為,而不是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才能實現企業的持續發展和股價持續攀升的目標[26]
。
為協同投資利潤和社會責任,部分跨國企業建立起自愿性行為準則來確定勞工、人權和環境標準。第一個全球性的企業行為準則為“蘇利文原則”,其要求簽約的公司遵守非歧視性的工作條件并增加“受壓制的種族群體”的機會原則[27]
。如今,“蘇利文原則”關注的重點轉移至員工自由結社權、適當的健康和環境標準、可持續發展等領域[28]。投資母國的主要作用在于建立起良善的外部條件以激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例如,《挪威雙邊投資范本(草案)》曾規定:締約方同意鼓勵投資者的投資行為符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跨國企業指南》,并積極參與聯合國《全球契約》[29]
。
國外的企業間組織和跨行業的合作組織也是推動企業提高責任標準的外部力量。例如,在商業協會的協調下,特定行業能夠產生統一的專有規則、標準和管理方式。行業間或跨行業統一的標準抑制了企業間的無序競爭,國內團體的管制也能協助企業建立最佳商業模式[30]。除外,商業協會也時常充當企業集體行動的代表,在與政府或國際組織的溝通和協商中捍衛企業方權益。對那些可能遭受社會和環境問題抗議的企業而言,搭建與當地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合作的平臺能構建起與當地企業和民眾間的利益攸關體形象,切實有效化解企業的生存危機。
四、防范中資企業海外投資非政府性障礙風險的法律策略
2013年7月至8月,云南大學緬甸研究中心組織開展了針對中國赴緬投資與援助的調查問卷,其中,76.7%的受訪者仍認為密松水電站不能重啟[30]。由此可見,非政府性障礙對中資企業海外投資的影響非常深遠,若單純依靠企業的自律,顯然無法及時有效地破解和避免中資企業在發展中國家遭遇的困境。在“一帶一路”政策推動下,在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未來的開發項目中,我國政府應有效防范和化解中資企業海外投資的非政府性障礙風險,實現我國海外投資又好又快發展的目標。
“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類規則”是我國政府幫助中資企業克服東道國非政府性障礙的因循路徑。在國際規則層面,我國應充分運用投資協定督促政府承擔保護和管制責任,實現協定促進和保護投資的功能與效用;在國內規則層面,我國應制定投資母國對海外企業的監管責任規定,實現“國內法治”和“國際法治”的良性互動,進而提升中資企業的國際形象。
(一)投資協定中添加“政府管理標準”條款
截至目前,我國已與100多個國家簽訂雙邊投資協定。以近期與尼日利亞、古巴等國簽訂或修訂的IIAs和BITs為例,并未涉及投資東道國環境保護的專門條款;在我國與東盟各國簽訂的《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投資協議》中,也并無相關規定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尼日利亞聯邦共和國政府相互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古巴共和國政府關于促進和相互保護投資協定的修訂》。筆者也發現我國與日本、韓國于2012年簽署的多邊投資協定已有環境標準不得降低的規定,但是,在與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簽署的投資協定中并無此規定。(參見:Japan’s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Signing of the Japan-China-Korea Tr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EB/OL].[2014-11-25]. http://www.meti.go.jp/english/press/2012/0513_01.html.)。
由于未將環境、勞工標準納入協定中,投資東道國政府可能迫于經濟壓力,選擇降低勞工標準和犧牲國內環境,并放棄正當行政程序的理念,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一味降低投資標準,可能在短時間內吸引外資,卻容易引發并加深投資企業與當地民眾的矛盾,最終使民眾對投資企業的合規運營活動產生反感,不利于企業在當地的長期投資,甚至還會影響投資國在東道國公眾中的形象。
由此,在近期簽訂或修訂的BITs或IIAs中,宜適時添加“政府管理標準不降低”條款,并在承諾不降低環境標準、勞工標準之外,加入管理外資的正當行政程序的規定,以保障東道國以公平合理的投資條件和程序吸引外資,避免“社會傾銷”,通過執行合理的標準和程序,減少當地民眾對中資企業違規的疑慮,從而有效維護和諧的投資關系。
(二)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資法律體系
我國對海外投資社會責任承擔的規定散見在《境外投資管理辦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對外承包工程管理條例》中。然而,現有對外投資管理框架的缺陷在于:第一,規范級別較低,如國資委和證監會的文件只是規范性文件;第二,可操作性不強,如《對外承包工程管理條例》僅僅規定對外承包工程應“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注重生態環境保護,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第三,適用范圍有限,上述規定僅對上市公司、中央企業和對外承包工程具有指導意義;第四,自愿性的標準居多,國資委規定本質上為指導意見。
我國對外投資社會責任監管采取以“自愿規則”為主的模式,但在海外投資中,作為負責任的國家,我國應承擔起對海外投資企業的母國監管責任。具體而言,在立法中,我國應明文規定所有海外投資企業應遵守當地的風俗習慣,并強制性地要求企業遵守國際上最低限度的勞工和環境標準,激勵中資企業使用“蘇利文原則”、“全球商業標準范本”等自治性國際性文件,避免當地民眾對中資企業勞工標準和環境標準的質疑,在國際市場上樹立起負責任的中資企業形象。同時,我國涉外立法可以參考基于效果原則的行政和司法管轄權,對企業域外腐敗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管理,從而樹立起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三)強化企業海外信息披露機制
透明度是消除中資企業非政府性障礙的關鍵環節。美國學者韋伯斯特研究發現,中資企業在非洲等地的投資對當地基礎設施、醫療、教育和食物供給等領域做出了極大的貢獻[30]
。然而,我國僅對上市公司披露企業社會責任或環境責任作出具體的要求
參見:2006年施行的《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和2008年施行的《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引》。,同時,透明度建設進程也較為緩慢。這也導致了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對中資企業評價不高。
提高中資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主要力量應是由政府保障利益攸關者和公眾的國際知情權,其核心在于建設和運營公眾參與性的透明度工程。良善的市場機制應建立在信息對稱的基礎之上,我國商務部可參照美國政府的做法,以政府投資的方式建設并運營中資企業透明度網站,鼓勵企業在該透明度網站上及時發布履行社會責任的報告,相關的行業組織或商務部門可以定期發布行業透明度報告或中資企業透明度報告。我國政府部門應對企業信息披露的完整性、真實性、準確性和及時性進行監督。除此之外,中資企業還應加強在東道國國內的透明度建設,特別是用東道國官方語言宣傳企業對當地經濟的貢獻和對公益事業的參與程度,在本地營造公開透明、正直友善的企業“公民”形象。
(四)提高企業本土合作的溢出效應
實現企業合作的溢出效應包括兩種路徑:其一是提升行業協會的自治功能;其二是與東道國企業和民眾建立起 “利益共同體”的關系。國外存在眾多的非政府組織監督企業的行為,基于我國的國情,短期內培育非政府組織對中資企業提供服務并進行監督的想法不切實際。我國應著眼于發揮行業協會的功能,行業協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制定行業的社會責任標準,通過“共同管制”模式參與并監督中資企業的社會責任建設,進而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
針對企業面臨的文化沖突和當地“經濟貢獻”不足的難題,除向當地民眾公開信息外,我國政府應該激勵中資企業構建與當地企業、民眾、非政府組織間“休戚與共”的利益共同體。針對潛在的非政府性障礙風險,中資企業可以展開與當地企業進行合資、合營等合作方式。在技術密集型行業中,中資企業宜積極融入本地產業鏈,構建完整的上下游關聯企業鏈條。與當地企業的合作不僅能夠發揮本地優勢和智力資源,也提供了與東道國公眾直接交流和溝通的平臺,能夠有效化解信息不暢而導致的誤解,也履行了企業在東道國的“經濟貢獻”等社會責任,進而將企業風險降至最低,產生企業合作的正外部性。
(五)發揮司法機制的事后救濟功能
在消除非政府性障礙方面,根據稅收對價的理論,東道國政府應承擔第一性的責任。非政府性障礙在本質上是超越法律的投資障礙。出于道義責任,企業應自覺維護良好和諧的投資關系,然而,中資企業面臨的非政府性障礙還可能包括國際政治勢力的介入和東道國國內反動派的利益主張,該障礙實難通過投資母國監管有效根除。此類型的非政府性障礙本質上為不合法的投資障礙,擾亂了公平正義的投資環境。面對不公正的政治訴求,中資企業應積極利用事后救濟的有效途徑,統籌運用東道國國內救濟措施和國際規則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針對東道國國內救濟措施,中資企業應堅定立場,以東道國投資者的身份要求東道國政府機構承擔保護責任,并履行約定。在未能按約履行并承擔保護責任的情況下,中資企業應主動要求東道國政府承擔違約責任。在國際規則層面,在本地救濟途徑未能解決爭議時,我國可通過BITs或IIAs提請ICSID投資仲裁,也可根據合同主張臨時仲裁或者第三方仲裁等。去政治化的國際司法機制是消除非政府性障礙的強有力后盾。
參考文獻:
[1]商務部. 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情況[EB/OL].[2015-01-24].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501/20150100877244.shtml
[2] 張曉君.貿易自由化與環境政策協調發展論——兼評WTO 貿易導向的協調模式[J].現代法學,2010 (6):141.
[3] Ibironke T. Odumosu-Ayanu.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atalysts in West Africa: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Content Laws and Industry-Community Agreements[J].North Carolina Central Law Review,2012(35): 80.
[4]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China Overtakes the United States to Become World’s Largest Energy Consumer[EB/OL].[2014-11-25].http://www.iea.org/index_info.asp?id=1479.
[5] 梁詠.中國投資者海外投資法律保障與風險防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9-62.
[6] Zuo Tao.The Inadequacies of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Regul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Myitsone Dam, Burma[EB/OL].[2014-11-25].http://www.earthright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land-water-rights.pdf#page=29.
[7]張晗.中企在緬電站陷政治漩渦 30多億投資可能打水漂[EB/OL].[2014-11-25].http://news.sina.com.cn/c/2013-02-06/085426219368.shtml.
[8]周佑勇.行政法的正當程序原則[J].中國社會科學,2004(4): 121-124.
[9] 張清敏.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政策的布局[J].外交評論,2007(2):22.
[10] Ruth Gordon.The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gagement with Sub-Saharan Africa[J].Environmental Law Reporter News & Analysis,2012,42:11-114.
[11] Mary E. Footer.BITs and Piece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J].Michigan Sta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9(18):38-43.
[12] 國資委.關于印發《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的通知[EB/OL].[2014-11-25].http://www.sasac.gov.cn/n1180/n1566/n259760/n264851/3621925.html.
[13]國資委研究室.國資委負責人就《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答記者問[EB/OL].[2014-11-25].http://www.sasac.gov.cn/n1180/n1566/n259760/n264866/3621552.html.
[14] 田虹.企業社會責任效應[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1.
[15] Kirk Herbertson.Leading While Catching Up: Emerging Standards for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s[J].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 & Policy,2011(11):23.
[16] Louise Redvers.Angola: Questions about China’s “Win-Win” Relationship with Nation[EB/OL].[2014-11-25].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102030058.html.
[17] 李雪平.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法律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28-29.
[18] William B. T. Mock.Corporate Transparency and Human Rights[J].Tuls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2001(8) :17.
[19]佚名.全球跨國企業透明度:中國公司排名墊底[EB/OL].[2014-11-25].http://data.163.com/12/0713/06/8698FPBA00014MTN.html.
[20] Alex Wawryk.Regulating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hrough 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M].Oxford:Palgrave MacMillan,2003:56.
[21]2012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EB/OL].[2014-11-25].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2/04/188199.htm.
[22] Edwin C. Mujih.“Co-deregulation”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Operat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tnering agains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2008(16): 249.
[23] Abdallah Simaika.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Alternatives to Liability in Influencing Corporate Behavior Overseas[J].Columbia Journal of Law and Social Problems,2005,38:348.
[24]薩繆爾·O·艾杜烏.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實踐[M].楊世偉,譯.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1:193.
[25] Lin Li-W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Window Dressing or Structural Change[J].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0(28):74.
[26]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Concern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business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5 (COM(2002) 347 final, Brussels, 2 July 2002 (2006) [EB/OL].[2014-11-25].http:// 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february/tradoc_127374.pdf.
[27]The Sullivan Foundation.The Global Sullivan Principles[EB/OL].[2014-11-25]. http://www.thesullivanfoundation.org/gsp/principles/gsp/default.asp.
[28] Barbara A. Frey. Legal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Protec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J].Minnesota Journal of Global Trade,1997(6):174.
[29]Mary E. Footer. BITs and Piece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J].Michigan Sta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9,18:61.
[30]Timothy Webster.China’s Human Rights Footprint in Africa[J].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2013,51: 649-660.
[31] Kevin T. Jackson. Global Corporate Governance: Soft Law and Reputational Accountability[J].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0,35:80.
[32] 盧光盛,李晨陽,金珍.中國對緬甸的投資與援助:基于調查問卷結果的分析[J].南亞研究,2014(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