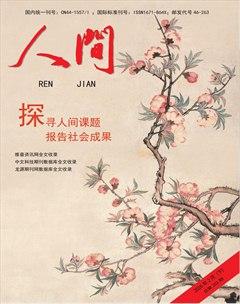中國民族問題治理的歷史經驗與啟示
趙旭東
摘要:民族國家的構建在于塑造一個具有共同政治認同、基本政治制度一體化的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族治理制度與觀念是歷史的產物,是歷史經驗與革命實踐結合的產物。
關鍵詞:中國;民族治理;歷史經驗;啟示
中圖分類號:D6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2-0112-03
一、中國古代的民族治理制度與思想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歷史的流變中展現出了一部民族交融與發展的史詩,中華民族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包容并蓄的精神便蘊含其中。在關于中華民族組成的問題上,費孝通認為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格局。“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單位, 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 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 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 “中華民族這個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還有它的特色在相當早的時期, 距今三千年前, 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若干民族集團匯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 被稱為華夏, 它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 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了這個核心。它在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后, 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份日益壯大, 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 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系作用的網絡, 奠定了以這疆域內部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 形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 經過民族自覺而稱為中華民族。”①中原的華夏民族與周邊的少數民族的關系在相互的交往中的不斷密切,因此對于民族問題的認識也不斷深入,開始形成一系列處理民族關系的思想,實施了處理民族問題的相關制度。先秦的《禮制正義》中就有“修其教不易其訴,齊齊政而不易其宜”的記載。這種處理民族關系的思想被后世各王朝所沿襲。
秦漢時期民族治理的思想為因俗而治,即根據民族地區的不同形勢設立管理機構進行統一管理。秦漢的統治者一般通過設立郡縣、屬國來管理內徙的邊疆民族,不具備設置郡縣管理的邊疆地區則設立諸如西域都護府等機構進行管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主題是國家統一與民族融合。北方內遷的少數民族在與中原地區的交流中逐漸漢化,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少數民族政權。至南北朝時期,已經產生了北方少數民族王朝與南方漢族王朝對峙的情形。各政權的統治者在處理民族問題上除了采用羈縻的政策外,多采用征戰的方式來解決爭端。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北朝的南征還是南朝的北伐,雙方的統治者都堅持自己是華夏的正統,可見他們都有渴望民族統一的愿望。北朝的少數民族政權認為華夏正統是以德相承,并不是依據民族來相承。而南朝則認為“內諸夏外夷狄”,自己以華夏正統而自居,但是南朝又不得不面對北朝對峙的事實。南北朝時期的兼并戰爭和經濟文化交流,促使民族隔閡逐漸淡薄,民族融合不斷加深,到隋唐時期已經形成天下一家的局面。隋唐時期受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大融合的影響,皆采取了較為開明的民族政策。唐代統治者倡導夷夏一家親,采取懷柔、招撫為主的民族政策,通過和親、冊封、盟誓和通使等多種方式來調整民族關系。其中設置羈縻府州管理邊疆是唐王朝的創舉。此外唐王朝實行屯田互市, 密切少數民族地區與內地經濟往來。宋代,中央繼續推行羈縻制度管理少數民族地區。蒙元時期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在西藏通過宗教領袖對藏區進行統治,元世祖時期封宗教領袖八思巴為國師。元代中央通過設立宣政院來管理西藏事務。在西北對畏兀爾采取封賞、聯姻等方式與畏兀兒建立緊密的聯系,以此來穩固對于西北的統治。元代時期,中央對西南地區實行土官制度,這一制度是以羈縻制度為核心建立的。明代依然沿襲因俗而治的思想,對于西北、東北少數民族進行招撫,設立一系列羈縻衛所。在西南則沿襲土司制度。對于西藏地區通過政治上的分封形式來確立明朝與西藏各教派和地方勢力之間的政治隸屬關系。明代與蒙古的關系除了軍事對峙之外,實行了封貢與互市的政策。清朝政府在民族事務管理方面的制度化和法制化進行了系統地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堪稱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翹楚。早在后金政權時期,后金政權的統治者就非常重視民族事務管理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天聰七年(公元1633年)皇太極曾經遣官前往內蒙古科爾沁部和外藩蒙古宣布《飲定法律》(又稱《盛京定例》)。后來,清朝政府陸續制定和增修《理藩院(部)則例》、《回疆則例》、《蒙古律例》、《西藏通制》等,確認了有關少數民族地區的行政區劃、職官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司法制度、宗教制度、經濟貿易制度等。這些制度或法律對少數民族地區事務管理規范化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使清朝官員在管理民族事務方面有章可循,在處理民族問題方面有法可依。②具體而言,清王朝在蒙古地區推行了盟旗制度,在西藏地區則設立了“金瓶掣簽”制度。新疆地區則采用伯克制與軍府制,后期在新疆設省加強對于新疆的管理。西南地區清王朝推行“改土歸流”的政策,這加強了中央對于西南的管理。縱觀古代的民族政策,歷代都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其中因俗而治是歷朝統治者所遵循的觀念,這種治理觀念的推行密切了各族人民間的聯系,推動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這一思想對于當代的民族治理仍然具有啟示意義。
二、近代以來民族觀念的變遷與民族國家的建構
晚清以來,中國置身于千年未有之變局,為了挽救危機,晚清政府在民族問題方面采取了平滿漢畛域、邊疆地區新政等政策,但是這些政策在內憂外患之下并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民族問題依然深重。近代中國被帝國主義列強強行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之中,被迫加入到世界民族國家的競爭行列,在這種世界潮流之下,晚清政府的這些措施遠不能解決近代以來的民族問題。雖然自古以來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是在這樣一個大的封建帝國里,先民們只有諸夏與夷狄的觀念,但并沒有近代意義上的民族的觀念。有以漢族文明為中心的“ 天下” 觀念, 但卻沒有在民族之林中自立的“國家”觀念。華夏與夷狄的區分, 不是基于人種、種族血統, 而是基于是否接受禮治與教化。③古代的民族觀念與近代的民族國家觀念有著天壤之別。近代的民族國家要對外確定邊界,對內締造大眾的平等性關系,強調公民權,以此維系社會的有機關系。中國近代意義的民族國家不是中央王朝集權和強烈控制的結果, 而是民族自覺的產物。這種民族自覺的動因, 一方面來自西方列強侵略給中華民族所帶來的整體性的壓力和危機,另一方面則來自帝國體系逐漸的瓦解, 各民族對建立新的政治共同體新的、內在的需求。④
在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民族的概念扮演了重述歷史與規劃未來的重要角色,而民族主義則扮演了把“民族”作為概念轉化為民族國家的政治魔術師。民族主義是現代性的政治共同體意識與行動,民族主義構建了民族,以民族為根基,推動了民族國家的創建。⑤中國最早提出民族主義的是梁啟超,他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說:“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 其在于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于世界也,國之獨立。”他所指民族主義,具有嶄新的內容, 是指整個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是為了“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而非狹隘的排滿主義或種族主義,因而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和進步作用。維新派與革命派關于民族主義的爭論在于是否排滿。辛亥革命后,建立獨立、民主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成為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基本共識并得到確立, 則標志著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最終形成。具體體現為中華民國成立初期五族共和的理念。孫中山在其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宣言書中說: 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⑥民族統一的意思, 照孫中山的說法,就是不分畛域, 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孫中山認為各民族應當平等共存,共同抵御外辱,實現民族自決、國家獨立。但是受時代的局限,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有大漢族主義的成分,他認為少數民族應該在國家的幫助下發展,逐漸同化于漢族,形成中國的“國族”—“中華民族”。五族共和的主張對于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樣的憲政安排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行民族國家建構的一種嘗試,也是對于民族問題、民族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是民國時期制定各項民族法律、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
1912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了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 第一次把調整民族關系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基本內容。北洋軍閥時期制定的《中華民國約法》, 南京國民政府1931年公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和1947年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 都以國家憲法的形式來規定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把民族平等寫入了憲法。北洋政府時期,重視蒙藏事務,制定相關法律并設立蒙藏事務處,并延續清朝的羈縻政策。在發展各民族民生事業的同時也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控制,并推行民族同化。南京國民政府基本沿襲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南京國民政府在法律上承認各民族的平等地位,這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 都有法律上原則要求和具體規定。比如在政治上,制定了保障民族地區參、眾議員由當地人員選派的《選舉法》這類基本法規;規定《蒙古自治辦法原則八項》,《蒙古蒙部旗組織法》等。在文化教育方面頒布了《待遇蒙藏學生章程》、《邊疆學生待遇辦法》等法律法規。民族政策方面則頒布了《蒙藏院官制》、《蒙藏事務局職任暫行規則》、《西藏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法》、《蒙古待遇條例》等,并在中央設立蒙藏委員會管理蒙藏事務。1945 年國民黨六大宣言提出賦予外蒙、西藏以高度自治之權,體現了民國政府民族政策具有自治性的一面。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近代中國,中國一切民族與邊疆問題的根源在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因此不論北洋政府還是南京國民政府,都對內投靠帝國主義,對內為國內的大地主、買辦與大軍閥代言,民族平等與民族自治多成為了政治手段。比如說西藏、蒙古地區的民族自治,實質上仍然沿襲清代的羈縻制度。主要通過籠絡西藏、蒙古的貴族,來實現統治。在西藏體現為維持噶廈政府,噶廈政府在政治上實行政教合一的封建統治,經濟上實行野蠻、落后的農奴制;在蒙古地區則維持盟旗制度與王公制。在這種制度之下,西藏、蒙古的一些王公貴族為了自己的利益則與帝國主義勾結,實行民族分離活動。比如西藏的噶廈政府在英國的慫恿與支持下,在國際上搞“西藏獨立”活動。內蒙古的德王在日本的支持下搞內蒙古獨立,曾經一度建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在法律上承認民族平等, 但不承認中國少數民族的存在, 把少數民族視為漢族的宗支,在實際上進行民族壓迫的統治。以內蒙古為例,國民黨把內蒙古的所有問題定位為一般的地方問題, 淡化、取消其民族問題特殊性的一面。在基本政策取向和目標上, 對內蒙古實行強力控制;通過建省置縣, 將其納入國民黨中央集權體制之內。⑦1928 年9 月, 國民政府宣布熱河、察哈爾、綏遠特別區改為行省。10月, 寧夏設省, 阿拉善旗和額濟納旗由該省管轄。隨著這些行省的成立, 內蒙古的昭烏達盟、卓索圖盟劃入熱河省;錫林郭勒盟、察哈爾部劃入察哈爾省;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土默特特別旗劃入綏遠省;阿拉善旗和額濟納旗劃入寧夏省。另外, 哲里木盟和呼倫貝爾部在清末已被劃入東北三省。至20 年代末30 年代初, 清末以來歷屆中央政府準備在內蒙古地區設立行省,并將各盟旗分別劃歸各省管轄的計劃得以實現。這些行省成立以后, 加緊向各盟旗境內移民放增設縣治。自建省設縣移民以來, 盟旗權利, 蒙民生計, 均為剝削殆盡。⑧當時的建省設縣事實上剝奪了少數民族地區的自治權利,人為的制造了民族紛爭與民族隔閡,加深了對于少數民族的壓迫。但是民國時代的民族政策與封建社會的民族政策相比的仍有巨大進步的作用。首先在于對于民族問題認識上的進步,民國以來確定的民族統一、民族平等的觀念較之封建社會的“華夏”與“夷狄”觀念是質的飛躍。其次,民國時代的民族思想與民族政策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中華民族”的觀念,這一時期對民族、國民等概念的解釋、澄清和重構,為完成民族國家的構建奠定了基礎。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更是刺激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情緒,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強。各少數民族雖然承受著國民黨政府的壓迫,但是仍然表現出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覺性,與漢族群眾一同抗擊侵略,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一直不斷加強。中華民族從一個理論名詞變成了一個存在的實體。⑨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民族治理制度與觀念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早在第一次國內戰爭時期,就提出了民族綱領和民族政策。當時主要的主張是民族自決,以此實現民族獨立,采用邦聯制實現中國統一,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在中共二大中也提出了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要并入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革命的潮流之中。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在統一國家內建立“自治區域”的思想。1930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根本法(憲法)大綱草案》、1931年和1934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1931年的《關于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都對于民族問題具體的闡述。紅軍長征的成功與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對于少數民族的社會狀況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認為根據少數民族地區的狀況,不能到處采用工農蘇維埃的形式去組織少數民族政權,在有些民族中可以采用人民共和國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爭取解放。此后中國共產黨對自決權的目的進行了首次闡述,認為強調自決權不只是為了分離、聯邦,更重要的是為了團結和聯合國內少數民族。1937 年 6 月的《中共中央關于“民族統一綱領草案”問題致共產國際電》中,“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之平等權及其自決權 ,以組成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這種思想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⑩抗日戰爭時期與人民解放戰爭時期是中國民族區域自治理論初步形成的階段,1940年的《關于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關于抗戰中蒙古民族問題提綱》中提出“在共同抗日原則下,允許回族有管理自己事務之權”;“蒙古民族有管理自己事務之權”。1941年《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規定“依據民族平等原則,實行蒙、回民族語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區。”1945年10月,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內蒙工作意見的一份電報指示,對內蒙的基本方針,在目前是實行區域自治。1946年1月,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和平建國綱領草案》中提出“在少數民族區域,應承認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權。”1947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形式是一個發展提高的過程,同時也逐步明確和充實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概念與內容。1947年內蒙古自治區的建立,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重要經驗, 也形成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初型。
1949 年9 月下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 具有代行憲法的性質。它根據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 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確提出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實行區域自治, 并全面闡明了黨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綱領性原則。其中第51條規定:“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 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 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 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凡各民族雜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區域, 各民族在當地政權機關中均應有相當名額的代表。”從1950年開始全國開始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195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有力的推動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實施。1954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制定出臺,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地位。從1957年開始的“左”傾的錯誤干擾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推行,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使得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遭到破壞,理論研究陷入停滯。粉碎“四人幫”后, 我國在批判糾正“文革”帶來的歷史錯誤時, 積極大力采取施恢復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建設。在思想上糾正了“民族問題是階級問題”的“左”傾錯誤思想。在《關于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必須堅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使各民族真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1984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施行, 標志著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此后縣、鄉兩級基層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行政機關發展迅速,少數民族人口增長逐漸上升,少數民族成員對自己原有民族成份進行了恢復,民族經濟和文化也得到長足發展。1997年江澤明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中,把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論述為我國三大民主制度之一,從國家根本制度上論述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地位。胡錦濤則指出,民族區域自治,作為黨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一條基本經驗不容置疑,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動搖,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的一大政治優勢不容削弱。針對民族關系的新情況新特點,習近平提出,民族團結是發展進步的基石,要把民族團結緊緊抓在手上。2014年4月習近平在新疆考察中指出,“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促進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讓民族團結之花開遍天山南北。”
四、民族問題治理的歷史啟示
民族國家的構建在于塑造一個具有共同政治認同、基本政治制度一體化的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廣大少數民族地區的推行,確保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的全面實現。民族區域自治,就是在統一的國家內,在國家憲法的基礎上,由少數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地區的內部事務。作為當代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保障了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體現了憲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內涵。民族區域制度是解決民族問題的重要途徑與形式。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通過《民族區域自治法》以及具體的自治規章、自治條例來實現。民族區域制度對于我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都具有重要作用。各民族的繁榮與發展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實基礎,然而民族的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的具體發展都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內去實現。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作為這樣一種框架為處理民族關系、保護少數民族權益提供保障。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中央政府對地方自治機關的有效控制和協調之下,有效地解決了中央與民族地方之間的關系,使中央和地方利益得以協調發展,從而建設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歷史的產物,它根植與我國悠久的歷史傳統中,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我國的實踐和發揚,是歷史經驗與革命實踐結合的產物。堅持并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將有利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也將加速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
注釋:
①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04期。
②余梓東:《淺談清代民族政策的啟示》,《中國民族》,2004年第12期。
③蕭功秦:《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與前景》,《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2期。
④付春:《從帝國體系到民族國家-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廣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⑤王文奇:《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構建析論》,《史學集刊》,2011年5月第3期。
⑥《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二卷,第2頁。
⑦李玉偉:《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內蒙古的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1期。
⑧義都合西格:《蒙古民族通史》,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版,第五卷,第340頁。
⑨嚴昌洪等:《論民國時期的民族政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⑩青覺:《中國共產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寧夏社會科學》,2004年3月第2期。
《陜甘寧邊區參議會文獻匯編》,第105頁,科學出版社,1958年。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38,人民出版社,1991年。
金炳鎬:《民族理論通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19頁,第520頁。
金炳鎬:《新中國民族政策發展60 年》,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 年11 月,第6 期。
李保林:《試論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四個發展階段》,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0年9月第5期。
胡錦濤:《在中央民族工作回憶暨國務院第四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7頁。
新華網:《習近平新疆考察紀實:民族團結是發展進步的基石》,2014年5月3日。
常安:《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憲制建構——新中國成立初期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奠基歷程》,《現代法學》,2012年1月,第一期。
金炳鎬:《民族理論通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98頁、400頁。
張天羽嘯,鞠彬彬:《簡論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法理基礎》,新疆社會科學,2013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