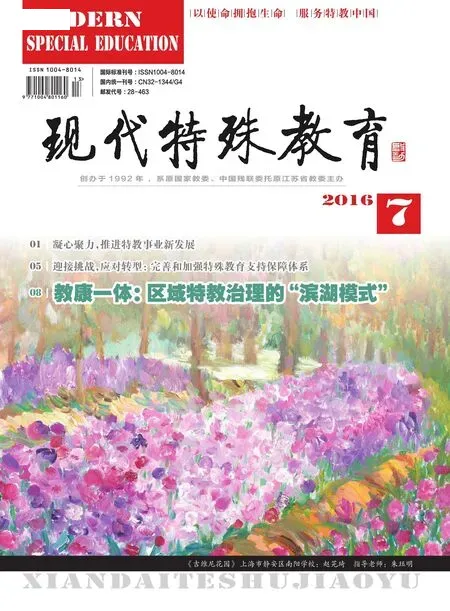著意育桃李,笑看繁花妍
——記上海市聾啞青年技術學校名譽校長戴目
·楊七平 沈幼生
著意育桃李,笑看繁花妍
——記上海市聾啞青年技術學校名譽校長戴目
·楊七平沈幼生
絳帳春風四十年,今朝鏡里驚華顛。白頭著意栽桃李,為與繁花共斗妍。已是癡聾何所求,此身合付大江流。厚顏偷得魯公句,俯首甘為孺子牛。
——戴目
人物小傳
戴目,男,漢族,1925年生,江蘇常州人。幼年因病致聾,曾入聾啞學校讀書。1945年入蘇皖解放區從事新聞工作。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在上海市教育局擔任分管特殊教育工作的視導員。1955年起先后任上海市第一聾啞學校、上海市聾啞青年技術學校副校長、校長等職。1986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為普教系統13位名譽校長之一。1991年被評為全國殘疾人自強不息模范,同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4年正式離休。曾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中國聾人協會主席等職。參與《中國手語》正、續集編纂工作,編撰出版的著作有《多國手語拾掇》《夢圓憶當年》《百年滄桑話聾人》《中國手語淺談》《現代漢語常用詞手勢圖解》(上、下冊)《漢語成語手勢圖解》。

戴目出生于1925年,年幼時被江南一戶殷實之家所收養,養父以懸壺濟世為生,是當地頗有名氣的老中醫。戴目8歲時罹患重病,經過搶救雖然起死回生,但從此留下了失聰的后遺癥。原名戴天贊的戴目感到自己從此將以目代耳,遂改名為戴目。戴目耳聾后,為人厚道的養父并沒有嫌棄他,而是送他到上海私立的福喑聾啞學校讀書。
青年時期立志從事聾人教育事業
戴目16歲從聾童學校畢業時,面臨職業的選擇。當時養父希望他能拜師學畫,學得一技之長以成名成家,可以自立于社會。但戴目經過深思熟慮后卻毅然選擇了教師這一職業,因為他認為“學畫畫固然可以有一技之長,在社會上會有個安身立命之地,不愁不能溫飽。但做一個聾啞學校教師,可以為眾多的聾啞同病免除文盲之苦。”因此戴目開始雖然遵從父命,師從著名畫家張充仁先生學了一段時間的素描,但隨后便沒再學下去,于1942年春,到中華聾啞協會附屬聾啞學校(今為上海市第四聾校)應聘為“助教”。翌年春,在蔡潤祥老師的推薦下,應聘到杭州一所私立聾啞學校教書。學期結束時,戴目因病辭去教職回到上海。同年秋,又應聘到無錫縣私立惠喑聾啞學校任教。
期間,當戴目回家看到與自己同樣失聰的孩子無處上學時,便萌生了在家鄉常州開辦一所聾校的想法。為了早日實現這一夢想,1943年秋至1944年夏期間,戴目便經常往返于無錫和常州之間。平時他在無錫教書,每逢周六下午沒課,便匆匆搭火車去常州與費耀奇、杜家瑞等同道一起商量籌劃辦學的事情。經過大半年的辛苦努力,1944年10月終于創辦了“武進縣立民眾教育館聾啞教育班”(今為常州市聾人學校),首屆招了18名聾生。
戴目主持聾啞教育班近一年,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老同學顧聯玨來訪并約他一起去蘇北抗日根據地參加新四軍。戴目經過考慮,“覺得幾年來從教困難,辦學不易,皆因社會黑暗、環境惡劣之故,況且人微力薄,難以支持(辦學)。”于是他毅然揮淚告別年邁的雙親,與顧聯玨同學一起投奔蘇北抗日根據地。在交通員的一路護送下,他們不懼千辛萬苦,終于如愿以償來到蘇皖解放區。戴目先是被安排在報社擔任校對,后來又先后在新濰坊報、解放日報和新華社等新聞單位工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戴目隨軍南下回到上海。經組織安排,先是在《解放日報》編輯部工作,《解放日報》刊登的全國解放形勢圖就是戴目繪制的。不久又調到新華通訊社上海分社資料室工作。雖然這是一份很不錯的工作,但戴目依然心系聾啞教育,希望通過教育“讓聾啞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告訴人們,聾啞人并不是社會的累贅,他們可以和健全人一樣為社會做出貢獻。”組織上了解到戴目要求繼續從事聾人教育這一想法后,根據工作需要,于1950年5月把他調到上海市教育局初等教育處任視導員,負責盲、聾啞學校的工作。
國內第一所聾人中職校的創辦者與領導者
1949年,除公立的上海特殊兒童輔導院(由著名教育家陳鶴琴先生創辦,上海解放后于1951年改名為上海市聾啞兒童學校,1952年又改名為上海市第一聾啞學校)外,上海還有5所私立聾啞學校,當時所有聾校的在校生總共有二百人左右。1952年,這幾所私立聾啞學校的畢業生寫信給上海市教育局,要求幫助解決升學和就業問題。負責分管此項工作的戴目經過反復研究,認為當時的聾啞青少年文化程度不高,又身無專長,安排他們勞動就業存在不少困難。而且當時上海剛解放不久,百廢待興,要給他們升學,條件也不具備,于是決定在上海市第一聾啞學校附設一個初中文化程度的“補習班”。翌年,將“補習班”改為“技術班”,試行對聾生進行職業技術教育。“技術班”設木工、美術兩科,有兒童玩具、家具制作、印染圖案和電影動畫等專業。戴目認為發展聾人職業教育是解決聾人出路問題的最好途徑,他和校長劉佩琪一起殫精竭慮,對“技術班”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三年的辛勤耕耘,換來了豐碩的果實:這一批由新中國培養出來的具有中級職業技術水平的聾啞學生,根據對口專業都妥善安排了工作。電影動畫專業8名學生,全部被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錄用,謝洪賓同學還擔任了木偶片《半夜雞叫》的人物造型設計工作。印染圖案專業的女學生周芹,學業成績突出,作品被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副院長龐薰琴教授所賞識,破例收為研究生,成為國內首位聾人研究生。
“技術班”的試辦成功,獲得方方面面的廣泛好評。在中央教育部盲、聾啞教育處領導的建議下,上海市教育局決定把上海市第一聾啞學校易名為上海市聾啞青年技術學校(以下簡稱上海聾青技校),并于1956年正式掛牌擴大招生。當時校長為劉佩琪,戴目為副校長。至此,國內第一所對聾人實施正規、系統的中等職業教育學校誕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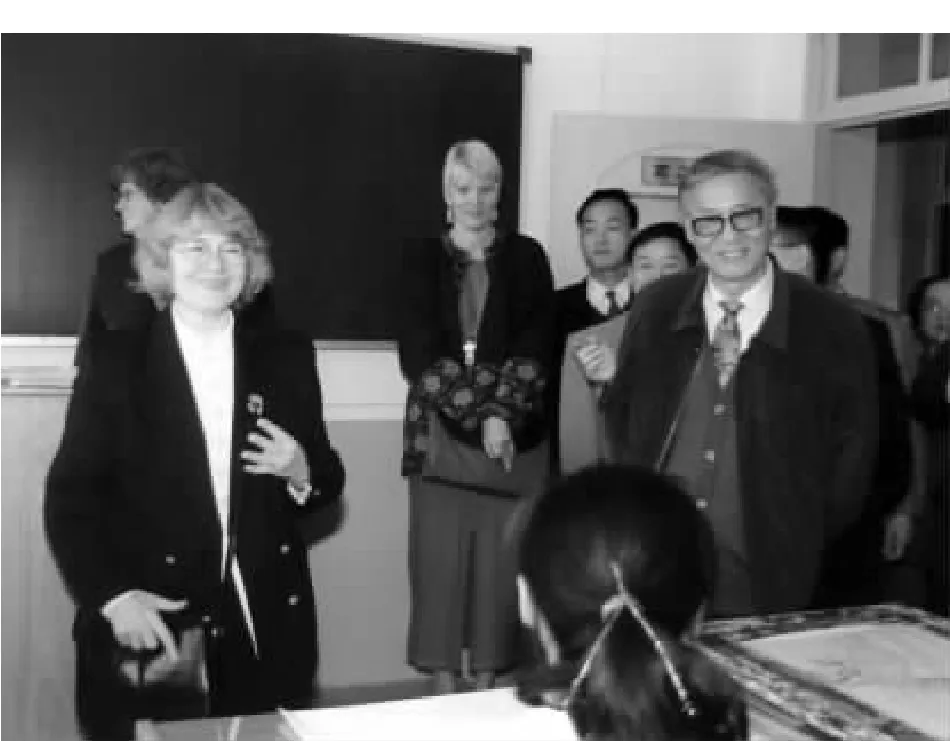
陪同世界聾人聯合會主席Kauppinen女士參觀上海聾青技校攝影滬青
屈指算來,戴目是聾青技校校長崗位上履職時間最長的一位校長。他1955年被組織任命為上海市第一聾啞學校(翌年更名為上海聾青技校)副校長;1978年,擔任校長直至1994年離休。198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段力佩、葉克平、趙憲初等13位滬上著名校長為名譽校長,戴目也是其中之一。在上海聾青技校初創時期,戴目雖然擔任副校長,但是身為聾人,他對聾人的身心特點和實際需要感同身受;多年的聾教育實踐,又為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因此在專業建設、課程設置、師資隊伍培養以及學制年限等問題上,他都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聾青技校曾停辦三年,教師隊伍被遣散殆盡。復校后,在當時特教師資數量緊缺、水平不高的情況下,戴目臨危受命,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立足自身,知人善用,堅持“實事求是、兼容并蓄、注重進修、各擅其長”的原則,使得一批新人、能人脫穎而出,挑起了教育教學的重擔。如果說,上海聾青技校現在有一支熱愛特教事業、熱愛殘疾學生、專業水平和教學能力強的師資隊伍的話,那么,這里面滲透了老校長戴目的無數心血。
戴目重視職業教育在解決聾人就業和生計問題上的作用,他認為要讓聾生畢業后勝任本職工作,專業訓練自不可少,但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培養聾生的自強意識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對聾人而言,只有自強起來,才能克服自卑,對生活、學習、事業樹立信心,才能有執著的追求,才能做到殘而有為,事業有成,平等參與社會,做到自尊、自立。正因為聾青技校重視對聾生開展自強教育,許多畢業生都能成為身殘志堅、德才兼備、為社會創造財富的佼佼者。當時有不少畢業生包括上海籍學生都能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毅然奔赴偏遠地區支援國家建設。為了用聾人自強成才的事例現身說法,激勵在校學生勤奮學習,戴目在離休后和同為聾人的聞大敏一起收集了100個自強不息、奮發成才的聾人事跡,于2003年1月編撰出版了《百年滄桑話聾人》一書,其中不少聾人英才都是上海聾青技校的畢業生。
中國早期聾教育發展史的研究者
作為一名聾教育工作者,戴目非常重視中國聾教育發展史的研究。他認為“如果從事聾教育工作,不了解不關心聾教育的歷史,就不能以史為鑒,容易誤入盲區甚至重復前人的錯誤。”因此,戴目很早就萌發了動筆撰寫中國聾教育發展史的想法。然而,要編寫中國聾教育發展史,絕非易事,首先碰到的問題就是資料不足。對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戴目利用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的機會,零零散散收集了一些資料,幾年下來積累了一大包。只可惜這包費盡他不少心血而收集起來的資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散失殆盡,戴目為此懊悔,心痛不已。
為了研究中國聾教育發展史,從20世紀80年代起,戴目又重新開始收集相關資料。他曾把希望寄予各地聾校為慶祝校慶而印刷的“紀念特刊”上。可實際情況是當時“紀念特刊”中的“校史”內容大都比較粗略簡單,寫得好且詳細的不多,利用價值不大。收集的資料尚無法編寫中國聾教育發展史,于是戴目將其撰寫成了2萬字左右的《中國早期聾人學校教育發展概況綜述》一文。在文中,戴目將中國早期聾人學校教育的產生和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1)創始階段——以1887年美國傳教士梅耐德在中國山東登州創辦啟喑學校(今煙臺聾校)為起點,至1914年前之江大學教授周耀先在杭州創辦“啞童學校”為止。(2)發展階段——以1914年前之江大學教授周耀先在杭州創辦“啞童學校”為起點,至1937年“七·七”北平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為止。此期間全國先后創辦的聾校(含盲聾合校)約23所。(3)發展緩慢的困難時期——以1937年“七·七”北平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為起點,至1949年9月底新中國建立前夜為止。此時期全國先后創辦的聾校(含盲聾合校)約32所。在該文中,戴目除了繪制有各階段創辦的聾校一覽表外,還對其中一些基礎較好、校史較長的聾校進行了簡述,對中國早期聾校的教育思想與教學模式進行了探討。
此后,戴目仍未中止對中國聾教育發展史的研究。1997年仲春,已年逾七旬的戴目到無錫走訪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上海私立聾啞學校讀書時的同學、已從聾校退休在家的宋鵬程老師。戴目從兩人敘說舊事、談寫回憶錄中突受“啟發”,當即提出廣泛邀請已退休的老教師、老校友一起寫聾校舊事,每人寫一點,編成一本書,從不同角度反映中國早期聾教育發展的大致軌跡,為后人編寫中國聾教育史留下一些有用的資料。這一提議得到宋鵬程的熱烈響應。兩人說干就干,經過多方聯系,一年多下來收到了20多篇稿件(資料),最終于1999年12月編撰出版了《夢圓憶當年》一書。該書以翔實的資料為后人展現了中國早期聾校所走過的荊棘叢生的崎嶇道路,為系統地研究中國早期聾教育作了可貴的探索,積累了彌足珍貴的資料。

戴老與學生在一起 攝影滬青
中國手語的規范者與推廣者
手語是聾人交際的工具。1985年底,戴目受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的委托,組成編纂小組,對1979年經民政部、教育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批準并正式推行的《聾啞人通用手語圖》四輯手語單詞進行增刪、修訂。經過一年多的工作,提出了初步修改意見。1987年5月,在山東泰安召開的全國第三次手語工作會議上,通過了編輯小組的工作報告,并確定將《聾啞人通用手語圖》易名為《中國手語》。1990年,以中國聾人協會的名義正式編印出版了《中國手語》(正集)。不久,戴目又受聘為《中國手語》(續集)編輯小組的顧問。前后兩次參與中國手語規范化工作以后,使得戴目對中國手語產生了研究的興趣。
1990年7月底至8月初,他代表中國聾人去美國參加第17屆國際聾人教育會議,回來后便萌生編纂一本收集有多個國家常用手語圖的書,以推進各國聾人之間的友好交往。他醞釀體例,廣覓材料,但終因當時仍在學校擔任領導工作、時間無法保證而擱置了下來。1994年5月,戴目離休。離休不離崗的戴目以“不教一日閑過”的精神,每天晨思夕讀,伏案寫作,歷經兩年多的辛勤勞作,于1996年8月終于完成并出版了《多國手語拾掇》。該書是收集了中國、美國、日本和國際通用手語500個常用詞語的手語圖集。
緊接著,針對特教界大家都很關注的手語問題,戴目在深入研究、理性思考之后,又于2002年3月推出他的新作《中國手語淺談》。該書對中國聾人手語的性質、產生及其發展、構“詞”和表述的特點、手語的規范化以及手語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都作了明確的闡述。
2007年9月,上海聾青技校為戴目從事特殊教育60周年舉辦了慶賀活動,并將其在中國手語、中國聾教育史、聾人職業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文章輯集成了《白頭著意栽桃李——戴目從事特殊教育六十周年紀念文集》一書。戴目從事特殊教育60周年,已至耄耋之年的他并沒有停下在聾教育園地里求索的腳步,即使是在得知自己身患重病時,仍然孜孜不倦。經過四年的不懈努力,2011年10月戴目主編出版了厚達900余頁、收入條目6300余個的《現代漢語常用詞手勢圖解》一書。該書對引導廣大聾教育工作者與手語愛好者正確而規范地使用手語、解決手語中的“一形多詞”(即一個手勢用來表達若干個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詞語)與“一詞多形”(即同一個詞,因其含義不同,對應的手勢也不一樣)等問題,具有很強的指導作用。
2012年4月,戴目又主編出版了《漢語成語手勢圖解》一書。該書借助《漢語成語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新世紀版)選輯的詞目及其釋義,加以手勢動作、文字說明,配制圖式而成,共輯錄了漢語成語詞目1769條。該書是一部有助于聾人學習、使用漢語成語與成語手語的工具書,開創了我國漢語成語手語研究的先河,對幫助聾人更好地理解漢語成語、更準確與規范地用手語表達漢語成語,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
戴目不僅喜歡研究中國手語,而且熱衷于中國手語的推廣。2004年,當他獲悉上海特教研究所創辦了《上海特教》專刊時,非常高興并積極支持,主動提出在刊物里設立一個“手語連載”的專欄,推廣中國手語。2004年8月,上海第一所手語學校——東方國際手語學校誕生,年近八旬的戴目把此項工作看作是他從事聾教育事業的延續,不僅出謀劃策,提出許多建設性的意見,還親自動手為手語學校編寫教材,修改教學計劃,親自上講臺為學員上課、面試,為學員開辟實習基地等。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如今,年過九旬的戴目仍在為研究上海聾教育史和醞釀編撰唐詩宋詞手勢圖解而上下求索,矢志不渝地為中國聾人教育貢獻自己的力量。
(作者單位:上海市聾啞青年技術學校,20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