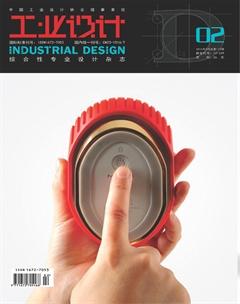“荒謬”遠比“空虛”更應讓人幸福
楊航
摘 要:《超脫》探討的是那個讓電影人們趨之若鶩的“如何生存”的議題。這里的“生存”不單單指生命在時間上的延續,而是如何活得更有價值,可能體現自對人的根源探究、面對無知過去的反思、對現實狀態的延續、對未來的選擇等等。我們從很多電影中都會捕捉到這些影子,或者有些干脆將其命為主題,為觀眾傳達一種“如何生存的哲學”。以存在主義角度進行電影批評可以找到答案。
關鍵詞:存在主義;自由選擇;西西弗斯
1 “荒謬”比“空虛”更讓人幸福——存在主義者眼中的生命意義
存在主義有一個最重要的觀點:人類是被拋露到這個世界來的,沒有上帝,沒有神的預先的決定。人來到這個世界是無數個偶然的結果。那么在這個充滿了偶然的世界當中,人應當如何確認自己的獨特性,去尋找活著的價值呢?這是在許多電影中我們經常看到的議題。
薩特對于這個問題的的答案是:選擇決定本質。人偶然來到這個世界,其本質是未被決定的,當人自己做出選擇的時候,本質才會被確定。人在不斷的選擇當中,不斷的自我定義自我。而加繆對于在荒誕世界中的生存法則,則以古希臘神話對作了最通俗的闡釋。《西西弗斯神話》中,巨人西西弗斯在地獄從山谷之底將一塊巨石推到山頂,但巨石一旦到了山頂,便會滾落下來,如此無窮的反復。“西西弗斯在下山的途中,意識到他工作的荒誕性,但他平靜而執著的個性表明了荒誕的人物的自由和明智,他從超越自然的希望中擺脫出來,同意生活在荒誕的世界中”。這個推動的過程本身是沒有意義的,當結果必然虛無的時候,推石頭這個行動的本身就是最好的反抗。加繆說:“爬向山頂的斗爭本身就是足以使一個人內心感到充實,應該認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加繆要讓我們相信的是,即使生活毫無希望,但與被空虛掠去靈魂的人相比,西西弗斯這看似荒謬的生命是有意義的。
如果說“自由選擇”是確定自己的另一種人生,那么“荒誕人”就是對現有狀態的延續。《超脫》就是一部典型的,可以用存在主義批評去分析的影片:這是一部有關人生苦痛的電影,里面的每個人物仿佛都在面臨同一種狀況:掙扎和渴望。而主人公亨利在那些想要拯救,想要尋求救贖的瞬間,感覺到無比的無力。面對現實的苦痛,那么又該如何自處。或許就像加繆所說:他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于絕對和真實的激情。面對這一切的一切,我們或許別無選擇,我們只能義無反顧地生活、盡其可能地生活。用存在主義批評來看待這部影片時,我認為可以把這部影片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可以用薩特的“自由選擇”觀點來分析,而在后半部分,我們用加繆的“荒誕人”的思想來看待。
2 “自由選擇”——自我定義生命的價值
艾德里安·布洛迪飾演的代課老師亨利,在童年時期心靈經歷過很大創傷,母親在他七歲那年服下過量的安眠藥死去,而自殺的原因是因為外祖父曾經與他的母親發生不正當的關系,外祖父或許也是自己的父親,這是他永遠無法擺脫的內心陰霾。而這所學校也沒有任何值得期盼的未來:即將關閉、學生無可救藥。亨利的真實生活和精神世界都是滿目瘡痍,面對充斥著絕望、窒息、無助的生活。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而且也不是體現你存在價值的所有證明。充滿了丑惡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謬的。在這樣一種狀況下,薩特所提供的心靈藥方:一切存在都有其本應有的價值,而一切的選擇都是自由的。就像亨利選擇承擔責任,雖然此時的他并不知道結果會是怎樣,但最起碼“去救贖”就是他所做出的選擇。
然而,“存在先于本質”中,作為“本質”的道德或靈魂,也應該都是由人在生存中創造出來的,人沒有義務遵守某個道德標準或宗教信仰,人有選擇自由的。所以在亨利的思維中常常陷入矛盾,這一點矛盾是道德與自由之間的:一方面亨利認為道德并不該被強加與他人身上;另一方面,他認為教師本身需要對孩子進行后天的引導,幫助其走上正確的人生軌道(這也是他對自己童年時孤獨無人引導的一種彌補)所以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終究無法做到真正的超然世外,做一個局外人。
3 “胖女孩梅麗迪斯”——“自由選擇”踐行失敗的悲劇人物
對于梅麗迪斯來說,她的青春期充滿孤獨和煎熬,而大部分原因都來自于疏離感和自卑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她也是年輕的存在主義者,在這個他者的地獄里苦苦掙扎。 她始終還是無法克服周圍環境對她的影響,連最親近的家人也不曾給她鼓勵,盡管她很有才華,尤其是遇到男教師之后,也試圖改變。面對同學譏諷的時候胖女孩曾經對亨利說,我希望我能和你一樣堅強。亨利告訴她,其實也不難,你要理解,很不幸大多數人的行為源于自我意識。你最好記住這一點,下次你或許還會遇到這樣的人,你時時刻刻都可能遇到這樣的人。但胖女孩最終依舊選擇了自殺,根本原因是即使她明白這樣的真諦卻無法真正擁有這樣的信念。亨利告訴她一切都會好的,梅瑞迪斯起初確實相信了,但是在亨利推開她的時候她明白了這些語言的虛無。所謂“明天會好起來的”,何時才會真的“好起來”,卻連亨利本身都無法回答。
我曾經看《死亡詩社》或者《放牛班的春天》這些影片,讓我的觀念始終停留在遇到一個伯樂后,他會相信我們并且引導我們走向自由與遠方,但我們都忽視了一個真相,生命中最難的部分并不是知道真理,而是如何真正使自己的行為走向真理。大多數情況下,很多道理我們都明白了,但是我們在行為上依舊表現得如此無知。我覺得問題出在她把對自己的認同寄托在了別人身上,“當你和我說話的時候,你讓我覺得自己是確實存在的”,這是胖女孩對男老師哭訴的一句話。遇到男老師后,她發覺生活中還是有人愿意認可她,尊重她,欣賞她的才華,并且給她鼓勵,然而她錯就錯在誤把這種認同當做自己做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人存在的本質是要靠自己去決定的,但她不是在選擇,而是一種依賴。她始終都處于一種自己渴望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卻又總是不能正面做出選擇去反抗,她從未自己認可自己,從未為自己的生命價值做出選擇。男老師拒絕她后,于她而言,最后的認同也轟然倒塌,那么她的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如果她選擇另外一種獨立的生活方式,不再去介意身邊人的嘲諷,勇敢的告訴父親自己并不想上什么斯坦福,而是渴望成為一名藝術家;不再總是把繪畫局限在一間小臥室,局限在為了發泄而去創作,那么她的生命才是真正有意義的。
正如薩特所說:要把自由選定為一種完全存在式的、本真性的價值,而不是一種虛假信念的可能性。女孩在結局自殺時,站在學校最熱鬧的地方,身后就是她的作品,這也算是她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理想中的自己展現在眾人面前。當然我們看到她的作品:中間是自己的一張照片——躺在地上,像基督在十字架受難的狀態,周圍被各種扭曲、謾罵的人臉照片包圍。她既然無法做到“用自我選擇去決定自己的本質”,那么通過自己的行動去確認自己的價值在她身上是失敗的,那么就只好承認基督教的觀點:人在生來這個世界上時,一切都已經被確定了,無法做到自主的改變自己的命運。“如果自殺,荒誕也就被否定了”。這雖然不是薩特的直接觀點,但卻代表了存在主義的基本原則:生理的自殺是一種逃避,事實上這并非一種真正的體驗荒誕之道,首先必須維系荒誕的存在,勇敢地直面它,才能談及戰勝荒誕,這也符合薩特一貫對生命的熱愛和激情。
4 “男教師”——執著推石人“西西弗斯”
影片開頭引用的加繆《局外人》中的一句話:“我的靈魂與我之間的距離如此遙遠,而我的存在卻如此真實”。影片中除了亨利以外的其他老師們,看上去都并不是很堅強:女心理咨詢老師一直用冷靜理性的態度去對待問題學生們,最終也因自己無能為力而情緒爆發;面冷心熱對教育事業充滿責任的女校長,面臨官員們的經濟利益,被逼到提早退休。我相信,他們都曾經改變過一些學生,但是太多無法改變的現實擊垮了他們,以至于他們都不知道如何做。在這樣一種狀況中,即使亨利給學生們帶來了希望,在長久的人生道路上能帶著這希望一直走下去的孩子也微乎其微。而亨利本身的內心世界也是支離破碎,這個救贖的過程本身對于他來說就是充滿痛苦的:男主角在公交車上看到雛妓賣淫的行為,下意識的聯想到母親,從而再次陷入對于自己身份的糾結和掙扎中,這件事是他內心的一個情結。在他安慰梅瑞迪斯時,被女老師撞見,看到別人眼中懷疑的目光,好像認為自己對學生的關懷交談有什么非分只想,他下意識的想起外祖父,這是他永遠不愿正視的心靈傷痛。這個過程對于身邊的人、對于他自己都是充滿痛苦的,因為注定會不斷撕裂自己的傷疤,往傷口上撒鹽。然而這個結果是未知的,他也無法判定自己的幫助是否會讓這些人的內心得到解脫。
亨利去青少年看護中心探望少女艾瑞卡,兩人在充滿希望的燦爛陽光中相擁,這個溫馨的畫面給了我們無限的希望,我們都以為影片會朝一個救贖成功的方向發展,而下一秒胖女孩梅瑞迪斯的自殺又給了我們當頭一棒:其他人的選擇或者命運并不會因自己一己之力而徹底改變。而這些問題僅僅是被呈現出來,卻并未給觀眾指明出路。影片結尾亨利獨白了愛倫·坡筆下令人窒息般的荒蕪,帶給人們的感受不是從中超脫,而是永遠地沉淪其中。這注定了亨利的“救贖”永遠不會結束,像一個永遠的使命那樣一直繼續下去。就像西西弗斯推動的那個巨石,到達山頂注定再次滾落,循環往復。這個過程本身看似是絕望的、沒有意義的,那么唯一的辦法是,把這個救贖的過程過程視為最高的意義,即使它是未知、是荒誕的。西西弗斯意識到他工作的荒誕性,但是他平靜而執著的個性表明了荒誕的人物的自由和明智,他從超越自然的希望中擺脫出來,同意生活在荒誕世界中。“對于荒誕的人而言,理想就是現在和種種現在的延續”這里的“延續”就是男教師亨利的“救贖”行為,用這種周而復始的精神作為對抗,把這個救贖他人的過程視為人生的最高意義。
除此之外,加繆認為完全有尊嚴的生活是在充分認識到荒誕之后依然肯為生活而活,因此,使自己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信服于這個荒誕的世界。在這個看似無果的“救贖”過程當中,看到生命存在的價值所在,這是亨利身上所體現的。這種信仰放在整部影片中是樂觀的,盡管結局是悲觀的。加繆在這里的觀點體現的是一種“荒誕式的英雄主義”,另一方面,“西西弗斯”——也就是男教師亨利,他失去了自己的未來,因為他自己的內心卻始終無法擺脫陰霾的束縛,無法真正做到“超脫”,那么他選擇善良選擇救贖是一種確定自己處世價值的方式,但它的存在卻是一種“現在與種種現在無休止的延續”,這絕對稱不上是一種理想狀態。男教師在這個看似永無盡頭的救贖過程中,所體會到的人情冷暖,或者是像雛妓艾瑞卡那樣帶給他心靈上的安慰,這個過程的力量是超越結果的。
參考文獻:
[1] 穆昭陽.懲罰神話中的集體意識:吳剛伐桂與西西弗斯推石[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0(10):122-124.
[2] 何向陽.“一個人的萬千身影”——尋找并成為自己的二百年[J].朔方.2009(09):3-23.
[3] 王挺.西方文學中的追求意識[J].紹興文理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02):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