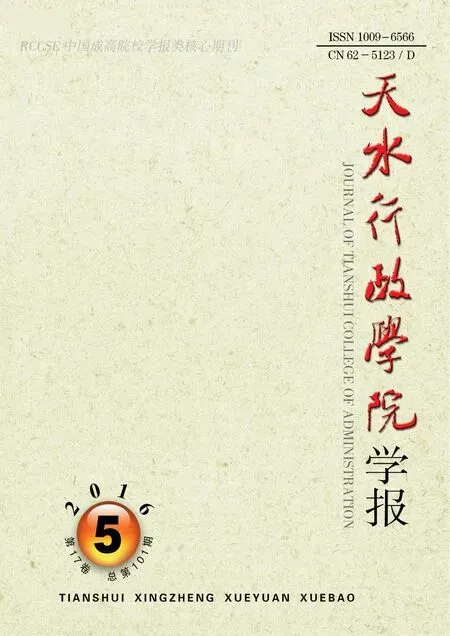村民自治的法治化路徑
杜瑞澤
(山東大學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村民自治的法治化路徑
杜瑞澤
(山東大學法學院,山東濟南250100)
我國的農村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面臨著多重困境,法治的缺失導致了農村治理秩序的混亂,亦使村民的自治難以真正實現。要讓村民自治走上法治化的道路,首先村民自治中的各方主體之間需要有明確的法律定位,并據此處理好各方關系;其次,村民自治權受到侵害時必須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濟,而現存的救濟制度無法真正發揮作用。構建以司法救濟為核心的救濟體系,通過司法途徑保障村民的自治權利,解決各方在村民自治過程中的糾紛,是實現村民自治的必要途徑。
村民自治;法治化;司法救濟
村民自治對我國的民主法治建設有著多重意義。村民自治是我國數億村民參與社會公共管理的基本途徑,是人民主權原則的重要體現。從國家層面來說,我國的民主憲政之路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而在國家的基層社會單位,即村集體中實施自治,實現村民的民主參與,可以說是我國在民主憲政方面的一種進步,也是我國民主憲政改革的基石。而且,實施村民自治也是對于村民的一種民主和法治教育,它不僅能提高村民參與社會管理的能力,還能夠讓村民在參與過程中增強民主和法治意識,使廣大村民體驗到自身所擁有的權利和自由,這將深刻地改變我國的民情。而民情,在一國的民主建設中至關重要。托克維爾甚至認為,對于民主共和制度的維系,民情的作用大于法制,是各種影響民主制度的因素中最為重要的一項[1]。而對于村集體來說,村民自治本身就是一種民主法治建設,村民集體自主處理內部事物,不受外部干涉,讓每個村民都有了參與管理家鄉的權利。而且,在民主的環境之下,村民獲得了這樣的權利并真正參與到管理活動中之后,就會對家鄉對社會產生更深的感情,這將會增強村集體的凝聚力,并促進農村社會的和諧。
然而,在現實中,我國的村民自治卻面臨著重重困境,遠未達到它應該達到的效果。在轉型中的鄉村社會中,法律和民情相交織,各方主體的職能相混雜,糾紛得不到合法解決,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村民自治離真正的法治化還有很長的距離。
一、村民自治的現實困境
(一)村民自治權難以真正實現
首先,從村集體組織和行政機關的關系來看,村委會以及村黨委會過多地受到國家行政機關尤其是鄉鎮政府的控制和干預。這種控制和干預既表現在村委會主任和黨委會書記的人選方面,也表現在村委會和黨委會的日常工作方面。雖然《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只負有“協助”鄉鎮政府展開工作的義務,但是在很多地方,村民委員會已經弱化為鄉鎮政府的手腳和工具[2]。
其次,從村民和村委會的關系來看,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普通村民行使自治權最重要的途徑是通過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雖然該法規定了村民或者村民代表達到法定人數可以提議召開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但是該法第二十一條同時規定了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由村委會召開。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村委會的制約和限制,現行法規定它們必須由村委會召開是一種制度缺陷,村委會在自身存在違法違規行為的情況下,很可能會拒絕或者阻礙村民委員會的召開,使得村民自治權的實現遇到障礙。另外,“從現階段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現狀來看,大多數農村地區的村民自治仍處于干部支配型或能人主導型的發展階段。”[3]普通村民在公共事務中的參與非常有限,有權威的村支書或者村主任往往對村集體的重要事務擁有很大的決斷權。因此,在村民自治制度的運行過程中,村民難以有效參與,村委會在一定程度上凌駕于村民之上,這部分地導致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所規定的村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出現不同程度的異化,法律規定的民主程序得不到嚴格遵守,村民自治制度在很多方面流于形式。
(二)村委會與黨支部的沖突
在村自治的實施過程中,“兩委”矛盾已經成為一個廣受關注的問題。在農村的基層組織中堅持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是村民自治制度構建伊始就確立的一項原則性規定。《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更進一步明確了村黨支部是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然而,在這樣的規定之下,在全國很多地方還存在著黨支部與作為基層自治組織的村委會的沖突。在農村地區兩委不和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常見的問題,村委會與黨支部或者相互掣肘,或者一方被另一方壓制,無論哪種情況都嚴重影響著農村正常的自治秩序。
村委會與黨支部的關系在法律層面沒有真正厘清,這在實踐中不僅造成了村委會和黨支部的矛盾,更使得村民自治制度中的各方勢力的矛盾通過村委會和黨支部的對立表現出來。首先是鄉鎮政府為了規避對村委會只能指導不能領導的規定,通過鄉鎮黨委直接對黨支部下達命令,由黨支部去實施。所以,村委會與黨支部的對立也反映出了鄉鎮機關與村集體的矛盾。其次是村委會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而村黨支部由黨員選出,兩者的民意基礎和權力來源均有所不同。本村內部的不同的派別、宗族勢力甚至是黑惡勢力滲透其中,通過支持甚或支配兩者中的一個來爭權奪利。
(三)村民自治中的腐敗現象頻發
從成立農村集體自治組織以來,農村腐敗現象就從未斷絕,甚至一度十分嚴重。由于反腐力度加大和整體法治狀況的改善,農村腐敗雖然已經得到了抑制,但是還遠未得到根治,賄選、收受賄賂、公款吃喝、侵吞集體財產等腐敗現象仍然普遍存在。
農村腐敗嚴重,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缺乏監督。雖然《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村委會的監督做出了規定,但這樣的監督在實踐中收效甚微。村民對村委會進行監督的形式主要是村務公開、建立村務監督機構和村務檔案,任期和離任的經濟責任審計。然而其中大多數措施在實踐中都沒有得到有效執行,原因有三:一是村民法治意識較低,對這些民主監督規定既不了解也不關心。二是即使村民發現村委會的操作不合乎規定,法律也沒有為其提供一個有效的解決機制。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村務公開不合法的,村民可以向鄉鎮政府或者縣政府主管部門反映,有關行政機關負責調查核實,并責令依法公布;經查證確有違法行為的,有關人員應當依法承擔責任。但是對調查的期間、調查的程序和有關人員具體應該承擔何種責任均未規定。另外,如果責令公布后村委會仍不依法公布又該如何處理?行政機關對違法的村委會成員進行的處理如何在發揮懲戒功能和不干預村民自治之間進行平衡?這些問題都有必要進行明確。三是我國的農村社會仍然是一個傳統的熟人社會,通常幾代人共同生活在一個村集體中,只要不涉及自身利益,大多數情況下村民礙于情面和風俗不會將同村村民的違法行為訴諸法律。
(四)農村地區矛盾頻發,糾紛不斷,不和諧因素增多
自從實行村民自治制度以來,農村地區的社會矛盾不斷加劇。村民與村干部之間、村民之間出現了很多糾紛,甚至演化成重大的惡性事件。很多農村矛盾得不到正常途徑的解決,致使農村上訪案件日益增多。這種現象是各種社會因素綜合的結果,但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當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在處理集體事務、化解矛盾方面的無力。
我國農村傳統上由鄉紳進行治理,鄉紳在鄉民中被公認為具有更多的知識和更高的德行,因而通常享有很高的威望。而經過建國后的人民公社運動,我國農村已經不存在鄉紳階層。廢除人民公社后,國家權力從鄉村撤離,后繼的村民自治制度卻至今沒有完全填補這一權力真空。村干部由村民選舉產生,本身就是普通村民的一員,實際上,他們在村民中的號召力和權威性完全不能與當年的鄉紳相提并論,尤其是在村民選舉中經常出現的賄選、宗族勢力或鄉鎮政府操縱、程序違法等情況下,當選的村干部更難以使村民信服。
二、村民自治的法治化
(一)實現各方主體之間的合理定位
村民自治面臨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該制度下的各方主體:村委會、黨支部、鄉鎮政府和村民之間權力(利)界限不明,定位不清,關系混亂。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確村民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以及村民自治權的主體。村民自治權的主體應該是全體村民,我國有很多學者已經對此做了詳細的論證。將“村民自治”視為“村自治”,這里的“村”的概念已經不僅僅是地理上的自然村的概念,而是以自然村為基礎集合起來的全體村民的抽象的總稱[4]。全體村民共同享有自治權是村民自治的出發點,村委會、黨支部、鄉鎮政府和村民之間的關系體系的構建也應該以此為中心。
1.村民與村委會。
我國目前的村民自治制度過多地關注村民委員會的建設,而相對忽視了村民自治權這一中心問題。從立法層面來看,我國村民自治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據是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的規定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城市和農村按居民居住地區設立的居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居民、村民選舉。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同基層政權的相互關系由法律規定。由此可見,憲法只是對村民委員會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并沒有明確確立村民自治權。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基本上也是以對村民委員會的規定為主,至于村民自治權的行使及其保障則著墨不多。從實踐層面來說,正如上文所述,村民對村集體事務的參與非常之有限,村委會對集體內部的大小事務的包辦影響了村民自治這一直接民主的實現。
全體村民是村民自治權的主體,村委會只是村民自治集體的“執行機關”,構建村民自治制度首先要明確這一認識,并將它付諸實踐。真正實現全體村民在村民自治中的主體地位,就要擴大村民在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決策中的參與,細化相關的法規制度。
要擴大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的職權,對其職權范圍,召開、表決的程序進行進一步的規定,在增強其規范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時,提高其履行職權的能力。
2.村委會與黨支部。
根據《村委會組織法》的規定,黨支部與村委會屬于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同時,黨章也規定了黨必須在村民自治中處于領導地位。在理論上,在兩者的關系中黨支部處于領導地位。而在實踐中,黨支部與村委會這兩套班子經常發生矛盾甚至處于對立局面,這一矛盾已經稱為我國村民自治制度中普遍出現而又難以解決的難題。
根據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并向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負責并報告工作。而對于黨支部的規定則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要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這種領導核心作用主要分為兩方面:(1)領導和支持村民委員會行使職權。(2)支持和保障村民開展自治活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黨支部對村民委員會的職權的行使是“領導和支持”,對村民的自治權利和自治活動則是“支持和保障”。黨支部確實對村委會具有領導職能,然而這種領導絕不是干涉甚至是取代村委會的正常工作。村委會是直接由村民選舉產生負責村集體事務的機構,在管理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方面享有獨立和完全的權限。應該對黨支部的領導作用進行進一步限定和明確,防止黨支部與村委會的職權混同以及爭權現象的出現。黨支部職權應該限定在四個方面:(1)對村委會進行監督。(2)密切聯系群眾,幫助和支持群眾自治。(3)調節村民和村委會的關系。(4)黨的政策的宣傳工作。
3.村委會與鄉鎮政府。
村委會與鄉鎮政府的關系問題無疑是村委會自治制度中的又一個長期存在而又難以解決的問題。從法理上來說,村集體是一個社會團體法人,而村委會作為社會團體法人的執行機關,只對全體村民負責,只有在違法情況才受到國家機關的直接干預。但是,村集體絕非一般的社會團體,村委會與國家機關也有著更為復雜的關系。從《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來看,鄉鎮政府對村民委員會進行“指導、支持和幫助”,但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事項。而村民委員會有義務“協助”鄉鎮政府開展工作。但在實際中,村委會與鄉鎮政府的關系早已發生了變異。“指導”變成了“領導”,“協助”變成村委會對鄉鎮政府命令的執行。村民委員會并非獨立于國家機關的民間組織,反而成為鄉鎮政府的“手腳”。這種情況在全國大部分農村地區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村委會與鄉鎮政府“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有其深層次的原因。首先是體制上的原因。改革后的鄉鎮、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基本上由人民公社的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的建制延續而來,除了正式的政權組織以外,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擔負著一定的行政功能,具有準行政和類行政組織的特性。政權組織的體制性權利雖然上收至鄉鎮,但功能性權力仍然延伸到農戶[5]。其次是思想認識上的原因。我國農村具有濃厚的“官本位”的傳統思想,對官方傾向于依賴和盲從。同時,農村地區還普遍存在著這樣的錯誤意識,認為村干部是“官”而不是民間組織的負責人,而“官”就要聽從上級也就是鄉鎮領導的安排。另外,鄉村社會中復雜的社會關系、利益機制也是村委會與鄉鎮政府關系變異的原因之一。
對于村委會往往受制于鄉鎮政府的問題,應該確立村委會相對于鄉鎮政府的平等地位。
村委會是村民自治體的執行機構,而村民自治體是獨立于國家機關之外的社會團體。村委會代表村民自治體的利益和意志,因而村委會與鄉鎮政府應該是平等的“官與民”的關系,而不是上下級的關系。村委會有義務協助鄉鎮政府在農村的工作的展開,然而這種協助應該是一種合作關系,而不是指導命令關系,對于鄉鎮政府逾越職權的干涉村委會有權拒絕,如果鄉鎮政府的干涉已經對村民自治造成了侵害,村民自治體有權進行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二)建立有效的權利救濟機制
1.現有救濟制度的缺陷。
無救濟即無權利,村民自治權作為一項民主權利,必須有一套有效的機制為其提供保障和救濟。從我國現今立法來看,關于村民自治制度之下的權利救濟的規定是十分薄弱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主要有四個條文對村民的權利救濟進行了規定,涉及到村委會選舉、村規民約的制定、村務公開、村委會損害村民合法權益的決定、村委會不履行法定義務和鄉鎮人民政府對村民自治的干預。而在以上幾個方面進行救濟的主體主要有三個:一是鄉鎮人大和縣人大常委會;二是行政機關,主要指縣鄉政府及有關主管部門;三是人民法院。然而,從目前的村民自治的實施狀況來看,無論哪種上述的救濟途徑均未能有效發揮作用:第一,根據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村民自治權的內容包括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而對村民自治權的救濟的規定卻僅限于以上幾個特殊事項,零碎片面,遠不能涵蓋村民自治權的全部內容。第二,僅僅是原則性概括性方向性的規定,沒有對救濟的程序進行細化,造成了救濟機制缺乏操作性而難以實施。第三,法院的司法救濟僅限于“村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成員做出的決定侵害村民合法權益”的情況,因而適用范圍非常狹窄。村民自治的權利救濟主要由地方人大和行政機關進行。然而無論是地方人大還是行政機關都難以對村民自治權進行充分有效的救濟。根據我國的憲政設計,人大的監督對象是國家機關,村委會作為一種民間機構也置于人大的監督之下,似乎有違法理。而且人大是代議機關,其行使職權的方式也決定了其無法對村民自治的權利進行直接有力的保障。行政機關對行政自治權的救濟同樣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鄉鎮政府本就存在干預村民自治的傾向,現行法律又賦予了鄉鎮政府對村民自治中的違法行為進行調查和處理的職權,這無異于強化鄉鎮政府和村委會的關系中存在著的上下級的錯誤傾向。而且相比于司法救濟,行政救濟政策性強而法律性弱,在程序性和穩定性方面均存在欠缺。第四,從以上的規定也可以看出,我國村民自治立法中關于村民自治糾紛處理主體的規定非常混亂,除了負責對村民自治工作進行日常指導的民政部門外,還規定了鄉鎮和縣級人大與政府,主體的不明確導致事實上的多部門看似都有權處理而實際上最后誰都不處理的后果[6]。第五,缺少法律歸責機制。在村民自治權利的實現過程中,對權利的救濟和對侵權人的法律責任機制是一體兩面的。對于權利受到違法行為侵害的村民的權利救濟,在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對違法行為的行為人課以一定的法律責任。但是,如果說現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權利救濟的規定非常薄弱的話,那么對法律責任的規定則更為欠缺。正是法律制裁嚴重缺位,才導致村民自治中違法行為的責任人漠視法律規定,并使得村民自治中的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成為常態,賄選、腐敗等嚴重違法行為亦屬常見。
2.完善司法救濟。
無論是人大救濟還是行政救濟均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對村民自治中的權利的救濟必須以司法救濟為核心。以司法救濟作為解決權利糾紛的手段是現代法治的重要特征,“司法最終”是一項重要的現代法治原則,一切法律糾紛至少在原則上應通過司法程序及訴訟程序解決,法院對于糾紛及相關的法律問題有最終的裁決權。在法治社會,當權利受到侵犯時,通過司法途徑獲得救濟既是一條必然途徑,也是一條最終途徑[7]。在村民自治出現的矛盾和糾紛中,完善司法救濟更有其必要性。相比于地方人大,司法機關具有更強的強制力和執行力。相比于縣鄉政府,司法機關更具超脫性,不存在復雜的利益關系和體制障礙,因此公正的救濟更易于實現。
村民自治中對權利的侵犯主要分為兩種:一是因為行政機關對村民自治的干預,二是村民自治體內部的糾紛。對于第一種糾紛,雖然學界進行了長期的呼吁,但我國法律至今并未明確將其納入到行政訴訟的范圍之中。2014年修訂的《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關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概括性規定是:“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的”。村民自治權作為一種社會權利并未被涵蓋其中。行政受案范圍的局限性使得鄉鎮政府插手村民自治事務、干涉村民自治權的行使的情況下,受到侵犯的主體沒有得到司法救濟的機會。這既不利于村民自治本身的發展,也不利于鄉鎮政府權利行使的監督,與法治精神極不相符。因此,在未來的立法中有必要將行政機關對村民自治的侵犯納入到行政訴訟范圍之中。
對于第二種糾紛,我們可以根據糾紛性質的不同分別將其納入到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范圍之內。(1)將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納入刑事訴訟。在我國農村地區的選舉過程中,破壞選舉現象極為普遍,其中尤以賄選現象最為嚴重且呈現出多樣化的形式。在我國,破壞人大選舉的行為可以構成破壞選舉罪,但對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僅僅規定“由鄉級或縣級人民政府負責調查并依法處理”。實踐已經證明,這樣模糊而缺乏明確的法律制裁的規定是難以發揮作用的。村委會選舉是村民自治中的關鍵環節,關系著村民自治的成敗,破壞村委會選舉也是對農村的社會治理和社會秩序的破壞。在刑法中應該對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作出規定,這也是現實的要求。(2)將村委會履行管理財產的職能時造成的權利侵害納入到民事訴訟體系中。村委會主要具有三個方面的職能:第一,作為集體財產的管理人,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于村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第二,作為農村社區的管理者,維護社會秩序,提供公共產品。第三,作為基層政府行政的委托人,實施一些行政行為,因而屬于委托行政。將第一類行為納入到民事訴訟的范圍中,這在我國已有相應的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農業承包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和《關于村民因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問題與村委會發生糾紛人民法院應否受理問題的答復》均已明確村委會的訴訟當事人的地位。然而這兩件司法解釋并不能涵蓋所有的問題,接下來需要在立法中對村委會和村民的民事糾紛的受案范圍、審理規則等進行進一步規定。(3)將村委會進行農村社區管理活動時造成的權利侵害納入到行政訴訟范圍中。這應當是村民自治權的司法救濟的重要內容。村委會對農村的管理承擔著重要的職能和義務,比如依照法定程序召開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進行村務公開接受監督,建立村務檔案等。村委會是否履行義務或者按照程序履行職能都關系著村民自治權的實現。比如,如果村委會不按照規定進行村務公開,那么就影響到村民的民主監督權的實現。在這種情況下,村民應該有權對村委會提起行政訴訟。但是,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體中的執行機構,從我國目前的行政法學理論上看并不能成為行政訴訟的主體。對于這個問題,學界有兩種解決辦法:一是通過將村民委員會視為行政主體賦予其行政訴訟被告資格[8]。二是從根本上扭轉只有行政主體才能作為行政訴訟被告的觀念,以是否具有公共權力,是否執行公務為主要標準來判斷某個主體能否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以這樣的標準來看,村委會在村集體的管理過程中確實享有公共權力并承擔相應的職能,因而村委會可以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這兩種理論路徑雖然依據不同,但殊途同歸,均為村委會的行政訴訟主體資格進行了論證。在當前的現實情況下,運用行政訴訟的途徑救濟村民的集體自治權實屬必要,同時這樣的立法也并不會帶來行政法理論上的混亂。
村民自治必須通過法治化路徑才能走出困境:通過對各方主體進行更加合理明確的法律定位,凸顯村集體作為村民自治權主體的地位;擴大村民參與并加強村民對村委會的監督,這是促進村民自治權實現、減少和杜絕程序違法以及腐敗現象的重要方式;限定黨支部的領導權限,使村委會能夠更好地行使職權;確立村委會對于鄉鎮政府的相對平等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夠更好地抗衡鄉鎮政府的過度干預;通過建立完善的司法救濟體制,使違法行為受到司法的裁決,使村民自治下的合法權益得到司法的保障,同時也會為當前頻發的矛盾糾紛提供穩定、合法、有效的解決機制。
[1](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216—218.
[2]房正宏.村民自治的困境與現實路徑[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9):25.
[3]盧福營.論村民自治運作中的公共參與[J].政治學研究,2004,(1):20.
[4]崔智友.中國村民自治的法學思考[J].中國社會科學,2001,(3):131.
[5]徐勇.政權下鄉:現代國家對鄉土社會的整合[J].貴州社會科學,2007,(11):9.
[6]劉志鵬.我國村民自治立法問題研究[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154.
[7]周佑勇.村民自治權利司法救濟的突破口[N].學習時報,2007-9-20(5).
[8]黃榮英.村民自治權利救濟的法律缺失與完善[J].行政與法,2010,(5):85.
On the Rule of Law in the Villages’Autonom y
DU Rui-ze
(Law School,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In our country,the system of the villages’autonomy is in trouble,The lack of the rule of law results in disorder in the village governance,and it alsomakes difficulties for the villages’autonomy to come true.Villages’autonomy must obey the rule of law,firstly the different subjects need clear legal status,and they should dealtwith each other according to their legal status;Secondly,the right of villages’autonomy need effective reliefwhen itwas violated,but now the system of relief can’twork well.The necessary way to achieve the rule of law is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reliefwith judicial relief at the core,safeguarding the right of villages’autonomy and solving the disputes in the process of villages’autonomy by judicial approaches.
villages’autonomy;the rule of law;judicial relief

D638
A
1009-6566(2016)05-0052-06
2016-06-29
杜瑞澤(1992—),男,河北衡水人,山東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憲法與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