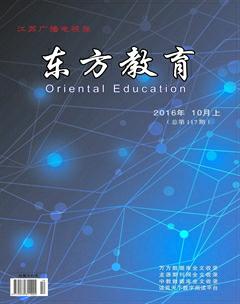同伴關系作為留守兒童心理發展的保護性因素
鄭璐璐+李紅
摘要:以往發現留守兒童在孤獨感、狀態焦慮、不良人格特質等心理健康狀況得分均顯著高于非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心理發展的生態模型描述了個體特征、留守環境與兒童發展結果之間的動態作用過程。留守兒童的心理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一些保護性因素,以促進個體良好的社會適應,其中同伴關系是留守兒童心理發展的重要保護性因素。文章繼而探討了同伴關系在擁有一般負性經歷、家庭功能缺失等特點兒童的心理發展過程中的保護性作用,從而論證了同伴關系在留守兒童成長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同伴關系;留守兒童;保護性因素
一、留守兒童現狀
農村留守兒童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特殊的龐大社會群體,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從農村流動到其他地區,孩子留在戶籍所在地農村,并因此不能和父母雙方共同生活的18周歲及以下的未成年人[1]。對留守兒童的研究發現留守與非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狀況存在著差異,表現為前者在孤獨感、狀態焦慮、不良人格特質等方面得分均顯著高于后者童[2-4]。
二、農村留守兒童發展的生態模型
那么,為什么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狀態普遍低于非留守群體呢?Bronfenbrenner的生態系統模型認為,兒童青少年的心理發展受到相互嵌套的環境影響。每個個體都處于多種復雜的生態系統環境的中心,其中家庭和同伴等近環境直接影響個體發展,留守狀態等遠環境屬于個體發展的背景,通過近環境間接作用于發展結果。宏系統本身缺乏解釋力,往往通過近端環境來影響個體的發展。
農村留守兒童心理發展的生態模型大致描述了個體特征、留守狀態與兒童發展結果之間的動態作用過程[5]。在這一系統中,遠、近環境因素以及個體特征會通過各種方式作用于兒童的發展。近環境因素和個體特征會直接作用于兒童的發展結果,同時通過作用于個體特征間接影響兒童的發展。同時,個體特征還會調節近環境因素與兒童發展結果之間的關系。
留守遠環境(如留守狀況)既直接作用于留守兒童的發展,同時也借助于近環境因素和個體特征間接影響兒童的發展。對于間接作用,一方面留守遠環境通過近環境因素和個體特征等中介作用影響兒童發展結果;另一方面,留守遠環境與兒童發展結果之間還受到近環境因素和個體特征的調節作用。反過來,留守兒童的發展結果也會作用于遠環境、近環境和個體特征,形成一種動態作用過程[5]。
三、留守兒童的保護性因素
(一)保護性因素的概念
青少年社會適應影響因素有較多分類,其中研究者根據影響因素對個體的影響是消極還是積極的,分為危險性因素和保護性因素兩類。以往研究已經發現了青少年兒童成長環境中的危險因素并不一定導致消極結果。研究者由此推測,社會適應因素中可能還存在某些緩沖或抵消不利影響的積極條件。于是研究者又提出了保護性因素的概念。保護性因素指可以調節、阻隔或抵消危險性因素帶來的不良后果,或即使在危險環境下也可以緩解不良結果的發生,促進良好社會適應的各種因素。這樣的分類對于有助于理解各層生態環境與個體發展的關系,幫助研究者們找到預防和干預個體社會適應不良的途徑和方法,從而促進個體的積極發展。
保護性因素通常有3種作用模型,分別是補償模型、保護模型和挑戰模型[6]。補償模型認為保護性因素和危險性因素共同預測青少年的社會適應,兩者的作用相互獨立。危險性因素和保護性因素分別增加了消極結果和積極結果的可能性,后者緩解、抵消和補償了前者所帶來的消極后果。保護模型認為,保護性因素和危險性因素對心理發展的影響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即當某種保護性因素出現時,危險性因素的效應將被削弱。挑戰模型澤提出,在一定條件下危險性因素也可能發揮保護性因素的作用,促進青少年的良好適應。例如,在適度的家庭沖突中,青少年反而有機會理解沖突的發展變化,并且從眾學習沖突的解決辦法。
(二)社會支持系統下的保護性因素
基于以上理論支持,研究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各種環境和個體因素對留守兒童的保護性作用和機制。例如,郝振從積極心理學視角出發,對留守兒童的自尊、心理控制源等積極品質與人際關系、行為表現、情緒控制、心理支援、生活信心、社會適應等社會適應性進行回歸分析,以期找到農村留守兒童社會化的保護性因素[7]。結果發現高自尊和內控歸因對農村留守兒童的社會適應發揮了保護作用。宋淑娟采用自尊量表和班級人際環境問卷對留守兒童進行策略,發現班級生生關系和師生關系會通過不同的方式影響留守兒童的自尊[8]。
對留守兒童的保護性因素研究的分析發現,社會支持系統的研究較多。社會支持是指個體從外界得到的物質或精神幫助,或是個體對外界支持的感知等。一項對于留守初中生的研究法發現,那些善于采取主動講述煩惱、主動求助等積極主動的應付方式的個體,能更好地獲得社會支持,從而對其心理健康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9]。具體而言,當他們遇到問題和麻煩時,往往會依次選擇朋友、母親、父親、教師、(外)祖父母和親戚以獲得幫助和關心。在他們首選的朋友選項上,擁有 6個及以上朋友的留守兒童在社交焦慮、孤獨傾向等方面的心理健康水平顯著高于朋友較少(1-2個)的個體 [9]。
當然,只有切實感受到的支持才能為個體運用,作為一種韌性資源(應對壓力時表現為一種韌性人格),對心理健康起調節作用,因而領悟社會支持的研究得到了重視。李海華以負啟動范式研究,考察了不同領悟社會支持水平留守兒童對情緒刺激的注意偏向和再認偏向,結果發現在啟動任務中,領悟社會支持水平高的留守兒童對情緒刺激判斷的正確率高,對積極情緒刺激的反應時更短;領悟社會支持水平低的留守兒童澤對消極情緒刺激的分心抑制能力更強[10]。
四、同伴關系作為留守兒童心理發展的保護性因素
由以上研究中也可以看出,在社會支持系統中,同伴關系作為留守兒童心理社會適應的保護性因素,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
(一)留守兒童與同伴關系
國內對同伴關系對留守兒童的保護性作用多從社會支持的角度有所涉及,但關于同伴關系保護性作用的單獨的、較為詳細的探討則只是集中在某幾個心理變量上的探討(如孤獨感)。例如,國內對留守兒童同伴關系的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社會接納性、友誼質量均與孤獨感呈顯著負相關。留守兒童的社會喜好和友誼質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負向預測其孤獨感[4]。因此我們有必要先來了解一下國內外對于同伴關系的探討,看看對一般或其他特殊群體而言,同伴關系究竟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及影響。
總的來說,國內對同伴關系對留守兒童的保護性作用多從社會支持的角度有所涉及,但關于同伴關系保護性作用的單獨、詳細的探討則集中在某幾個心理變量上的探討(如孤獨感)。因此我們有必要先來了解一下國內外對于同伴關系的探討,看看對一般或其他特殊群體而言,同伴關系究竟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及影響。
(二)同伴關系對兒童的影響
國內外研究者對心理健康的各種影響因素進行考察的過程中,同伴交往由于對個體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受到研究者的極大關注。例如,Schwartz等人發現擁有較多的朋友能夠緩解學業成績不良可能帶來的抑郁癥狀[11];友誼質量能夠有效地負向預測青少年的社交焦慮癥狀[12];班級生生關系與兒童的自尊之間存在顯著相關[8];Adams等人發現兒童的負性經歷所帶來的皮質醇變化和自我價值感的降低會因為擁有一個好朋友而得以減輕[13]。
以往的研究發現,留守兒童往往體驗著一般負性經歷,具有家庭功能缺失等特點。因而本研究根據留守狀況的這些特點及表現對國內外相關研究進行了梳理。
1.同伴關系與一般負性經歷
Adam等人考察了小學5年級和6年級學生在經歷負性事件時,好朋友在場是否能夠作為保護因素,削弱負性經歷對個體總體自我價值感和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軸的作用[13]。結果發現,有至少一個好朋友在場時,緩解了皮質醇的升高與事件消極性之間的正向關系,同時也緩解了自尊與事件消極性之間的負向關系。也就是說,當一件消極事件發生時,至少一個好朋友在場能夠減弱事件消極性對皮質醇和自尊的影響。
Powers等人在非營利的初級護理和婦產科診所(服務于低收入人群和無家可歸者)的等候區招募378名被試,通過研究者給被試讀出每一道題并記錄被試的作答,完成了貝克抑郁問卷(BDI-II)、童年創傷問卷(包括性虐待、身體虐待、情感虐待、身體忽視、情感忽視5個領域)、社會支持行為量表。結果發現,①個體在童年期遭受的情感虐待和各種忽視,對成年期的抑郁有較強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大于性虐待和身體虐待所帶來的影響。②感知到的家庭支持與童年期受到不良對待的經歷相關,感知到的家庭支持并不能預測成年期的抑郁程度。③對女性而言,感知到的朋友支持與成年期抑郁、情感虐待和忽視顯著相關。考慮到各種不良對待方式的作用,感知到的朋友支持能夠保護個體,減少抑郁的危險[14]。
Schmidt 和Bagwell測量了3~5年級的670名男女生,以自我報告的方式獲得了友誼質量、關系/身體欺負、焦慮和抑郁得分。結果顯示積極友誼的兩個方面(幫助和安全)起到了緩沖作用,但只在女生身上有體現,且對焦慮和抑郁都有作用,證明了積極友誼在受欺負和內部焦慮中的保護作用[15]。女性可能更擅于發現并重視他人的幫助,引申開來,親子依戀關系可能可以提供一些解釋。
2.同伴關系與家庭功能缺失
Chester等人研究了家長養育和同伴關系對單親家庭(只有母親)中非裔美國青少年(7~15歲)社會心理適應的影響。結果發現,母親養育和同伴關系對青少年抑郁癥狀都有主效應,交互效應不顯著;同伴關系對青少年外化癥狀有主效應,并存在同伴關系與積極教養方式的交互效應。當母親的積極養育行為水平較高時,同伴關系沒有顯著影響;母親積極養育行為水平較低時時,同伴關系有顯著影響[16]。
Kerns等以參加某次為期6天5晚夏令營的97名8~12歲女生為被試,考察了親子關系、入營前的社交自我概念和入營后的同伴關系對女生想家的情感預測力。結果發現,社交自我概念、同伴社會支持和友誼質量能夠預測思家的情感;反過來,入營前思家的情感并不能預測營中的同伴關系。社交自我概念和同伴關系可能是夏令營中思家情感的保護性因素[17]。國內研究者通過結構方程模型探討了城市中學生的疏離感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功能和同伴接納的關系,結果發現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受到家庭功能的完全中介作用間接影響青少年疏離感,而同伴接納對這一中介作用起調節作用[18]。
五、未來研究展望
(一)發現留守兒童的特異性保護因素
雖然間接說明了同伴關系的保護作用,但近期有研究者開始質疑保護性因素的普遍性[19]。也就是說與其他個體相比,某種類型的個體在特定的發展結果上是否更受益于某種保護因素?
農村留守兒童中的保護性因素的效應可能具有群體特異性,這也使得對農村留守兒童群體的保護性因素或保護機制的研究更優意義。那么,同伴關系對留守兒童的保護性作用,與其他負性經歷兒童發展中同伴關系的保護性作用一致嗎?有待從留守兒童的特點(如家庭功能缺失,社會境地地位較低)出發,進一步研究。
(二)重視對保護性作用機制的探討
以往研究總結了3種保護性因素模型,即補償模型、保護模型和挑戰模型。現有研究多從某一種單一模型(尤其是補償模型和保護模型)入手進行研究,鮮有研究論及模型間的相互作用。現實中可能存在各種模型的有意義組合,因此今后相關研究可考慮根據留守兒童心理發展的實際情況來探討各種保護性因素之間的累積性作用。
(三)考慮到即時性和延續性的問題
已有的大量橫斷研究探討了同伴關系作為保護性因素對處于危險性因素中的兒童(如留守兒童),研究者更希望通過追蹤設計對同伴關系持續作用后的發展結果進入深入探討,以此繼續探討保護性因素作用的即時性與延續性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郝振,崔麗娟.留守兒童界定標準探討[J].中國青年研究,2007(10):40-43.
[2] 范方,桑標.親子教育缺失與“留守兒童”人格、學績及行為問題[J].心理科學,2005,28(4):855-858.
[3] 劉正奎,高文斌,王婷,等.農村留守兒童焦慮的特點及影響因素[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07,15(2):177-179.
[4] 孫曉軍,周宗奎,汪穎,等.農村留守兒童的同伴關系和孤獨感研究[J].心理科學,2010(2):337-340.
[5] 趙景欣,申繼亮.農村留守兒童發展的生態模型與教育啟示[J].中國特殊教育,2010(7):65-70.
[6] 金燦燦,鄒泓,李曉巍.青少年的社會適應:保護性和危險性因素及其累積效應[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12-20.
[7] 郝振.農村留守兒童的社會化狀況及其保護性因素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08.
[8] 宋淑娟.班級人際環境對留守兒童自尊的影響[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9(2):75-77.
[9] 雷芳.不同地區留守兒童心理健康狀況和人格特征比較[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0,18(1):74-76.
[10] 李海華.不同領悟社會支持水平留守兒童對情緒刺激的認知偏向[D].西南大學,2009.
[11] Schwartz,D.,Gorman,A.H.,Duong,M.T.,& Nakamoto,J.Peer relationship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s interacting predictor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middle childhood[J].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2008,117(2):289-299.
[12] Festa,C.C.,& Ginsburg,G.S.Parental and peer predictors of social anxiety in youth[J].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2011,42(3):291-306.
[13] Adams,R.E.,Santo,J.B.,& Bukowski,W.M.The presence of a best friend buffers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experiences[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1,47(6):1786-1791.
[14] Powers,Abigail,Ressler,Kerry J.,& Bradley,Rebekah G.The protective role of friendship on the effects of childhood abuse and depression[J].Depression and Anxiety,2009,26(1):46-53.
[15] Schmidt,Michelle E.,& Bagwell,Catherine L.The protective role of friendships in overtly and relationally victimized boys and girls[J].Merrill-Palmer Quarterly: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7,53(3):439-460.
[16] Chester,Charlene,Jones,Deborah J.,Zalot,Alecia,& Sterrett,Emma.The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of African American youth from single mother homes: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parents and peers.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2007,36(3):356-366.
[17] Kerns,Kathryn A.,Brumariu,Laura E.,& Abraham,Michelle M.Homesickness at summer camp:Associations with th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ocial self-concept,and peer relationships in middle childhood[J].Merrill-Palmer Quarterly: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8,54(4):473-498.
[18] 徐夫真,張文新,張玲玲.家庭功能對青少年疏離感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效應[J].心理學報,2009,41(12):1165-1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