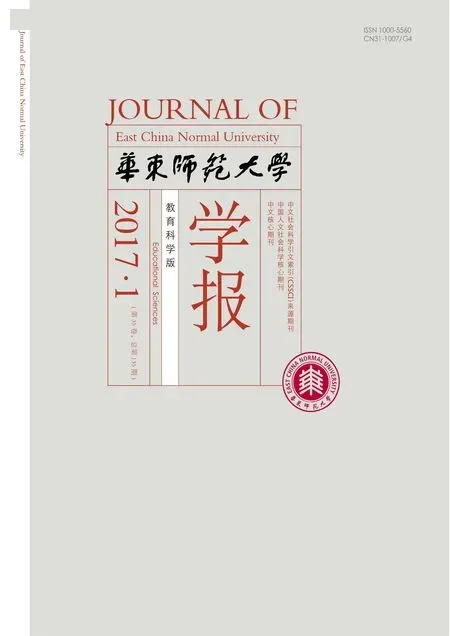課程,悠游于科技的邊緣
——威廉·派納與楊澄宇關于課程和科技關系的對話
威廉·派納 楊澄宇
(1.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溫哥華; 2. 華東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上海 200062)
?
課程,悠游于科技的邊緣
——威廉·派納與楊澄宇關于課程和科技關系的對話
威廉·派納1楊澄宇2
(1.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溫哥華; 2. 華東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上海 200062)
楊澄宇(以下簡稱“楊”):寬泛而言,您是否認為科技的進步會促進教育的發展?
威廉·派納(以下簡稱“派納”):是的,我認可這樣的說法。如果沒有技術的幫助,諸如網絡資源在內的許多教育經驗無法獲取。但更重要的是,處于支配地位的科技會對教育產生負面影響,因為它會重建學生與教師的關系,使他們之間不再需要互相適應并以此來決定學習的方式與內容。這是一種控制學習的“方便法門”。這樣看來,原本應是“復雜對話”的課程變成了項目間的對話,而不是真正的對話。當本該是交互式形態的課程僅僅提供文本或產品之時,教學也就淪為了其所采用工具。所以說對于這樣的論斷,我基本贊同。
楊:好的。那么從更寬泛一點的意義上來說,您認為高科技改進了我們的生活嗎?
派納:我基本贊同。譬如醫療的發展,可以救治人類疾病;但有些藥品也會危害到人的生命。
楊:今天我們的世界或許可以被看成是一個“后人類”(Post-humanity)的社會,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正在大行其道,您認為我們的教育或課程需要對此做出改變以適應它嗎?
派納:當然必須去適應。我認為我們需要去研究這樣的境況:為何會有這么一個新概念出現?它為何重要?如果我們把世界作為文本來分析,這樣的情況會對國際文本、歷史文本產生怎樣的影響?這個對于人類的新概念意味著什么?——我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人類。所以我認為,課程理論與課程專家們更應該對此進行研究,并對這個話題做出回應。
楊:是的,讓我們考慮國際的、具體的“文本”。中國在教育政策制定方面,越來越關注高科技在教育中所占的比重,特別是信息技術對教育的影響。政府大力提倡信息技術教育與信息意識的培養,這也是國際的趨勢,譬如21世紀新技能的提出等等。
派納:對于這樣政策的制定,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這是一種對于課程的控制方法,并且限定了討論的邊界。它暗示我們,教育天然地要為經濟服務。但是我認為教育是獨立的。人生的一個重要目的甚至就是學習和理解自我,而非為新經濟和新技術作準備。教育并非僅僅是讓我們變得更有競爭力,或者使得我們成為雇主希望變成的樣子。這個話題在美國也有很大的爭議。在政府層面,他們知道雇主的要求,為之所做的準備都可以看成是一種對大學的控制方法。當然,在這方面,公立和私立大學在課程管理和商業參與方面不盡相同。另外,在大學層面,讓每個學生變得更加專業,讓開設的課程更加專業化,這確實是非常“經濟”的做法。
楊:您對美國大學教育提倡的STEA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rt,Mathematics)理念有何見解?
派納:我對此非常熟悉。但我覺得目前他們提倡的只是STEM,沒有A,沒有藝術教育。在他們看來藝術并不重要,這是件可怕的事情。我們并不在乎藝術、美術、音樂、詩歌,我們唯一在乎的就是賺取金錢。
楊:如此說來,您似乎對自由市場經濟并沒有好感?
派納:是的,這里沒有自由市場,只有非自由市場。少部分人掌握了絕大多數的財富,這是一個壟斷的資本市場。
楊:您知道,我本科所學的專業是經濟學,所以我還是相信自由市場,相信“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的。經濟學家哈耶克對政府的行為有不信任感,他認為市場經濟可以讓我們擺脫政府的控制。
派納:我并不相信這點。就西方而言,政府和商業機構緊密合作,整個國家本身可以說就是一個大的“生意”。有一點我非常欣賞中國。就我在中國的課程研究經驗來說,盡管我從未和他們分享過我對意識形態的觀點,但我確實欣賞政府將國家和經濟分開看待的態度。在美國已經無法這樣了,在加拿大也只能是勉力為之。另外,就算市場是自由的,有“看不見的手”讓我們擺脫政府的控制,但它在政治和文化領域,依舊具有相當大的破壞性。因為“看不見的手”總是將大多數人的東西交到少數人手上。
楊:是的,對于這種不平等,我們深有感觸。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美國一些地方的學生放學后會在校車上完成作業,因為那里有家里提供不了的網絡。
派納:對。而且我還說過,要讓孩子們遠離網絡。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網絡會放大孩子的焦慮和緊張感,會起到示范效應,最極端的例子就是自殺率的上升。
楊:您認為這是網絡的責任嗎,還是說這是學習和生活壓力增大所導致的?
派納:網絡讓事情更加糟糕,比如它鼓勵人們上傳暴力等充滿負面情緒的圖片。
楊:但是,您知道嗎,上海家庭的網絡覆蓋率達到了95%,這超過了美國的平均水平。江蘇省早就實現了的一個項目,就是讓每一所學校都有網絡教室。
派納:哦,太糟糕了。我的意思是這可能會比較糟糕。
楊:當然,有這個可能。我們這么做是想讓學生獲得優質的教育資源,特別是一些農村地區。
派納:是的,這就是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在農村地區通過廣播接受遠程教育的原因。當時紐約的教師通過廣播向農村的孩子講授數學、化學等課程。所以,希望你們能取得好的效果。
楊:讓我們從宏觀轉向微觀領域。您知道,在如今的課堂上,學生的學習充滿了許多新科技的元素,譬如翻轉課堂和慕課的流行。許多學者認為這將使得學習更有效率。
派納:他們是怎么測定的?你相信嗎?
楊:他們相信新技術的運用可以使老師更有效率地匹配學生的需求。
派納:他們或許只是在做一項“生意”,以此獲利。或許,這也是一種所謂的“宿命”:技術成為了他們新的信仰,就像成為了他們原先所信仰的上帝一樣。
楊:所以說您不相信科技可以促進學習?
派納:不,我相信科技。對于特定課程而言,一些網站確實可以提供有用的、有趣的學習資源。但是就每一個微觀事件而言,情況可能大不相同。
楊:我們是否可以認為,由政府來力推這些可能是有危險的?
派納:是的,我贊同這點。經費可以用在其他更有價值的地方,比如提高教師的薪水、縮小班級的規模、提升教師的經驗等;另外,也可以利用這些經費為教師創造更好的條件,譬如更舒適的休息室等等,讓教師們的生活不要那么緊繃,而成為一個正常的人。我和張華教授曾共同編著過一本書,其中有一個章節是關于中國教師教育發展狀況的,對于其中教師是怎樣失去自我、怎樣耗盡自我精力的部分,我感到震驚。
楊:讓我們回到具體的課程。您覺得不同學科在面對科技進步時遭遇的問題一樣嗎?譬如數學、物理、化學與藝術等課程是否面臨同樣的境遇?
派納: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不同學科是否都需要運用更先進的科技來進行教學?在北美和歐洲學界,有一種稱為“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新興學科,用信息技術的手法來處理人文問題。我曾聽過我一位同事的演講,他統計莎翁《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愛”這個詞出現的頻率,他發現羅密歐使用這個詞多過朱麗葉。這說明什么?我不太確定。我認為藝術、人文學科乃至人類的交流無法用數字來測算,對人類的某些行為與情感做統計也是沒有必要的。總之,將新技術運用于所有學科,這是個很危險的趨勢。
楊:這確實值得我們深思。在中國,一些地方教育部門對教師教學的評價也加入了新技術運用這個元素,鼓勵乃至要求教師采用信息技術。
派納:人類正處于日益科技化的世界中,技術占據統治地位。我認為我們很難跳出這樣的境遇來感知和行動,這也是我覺得歷史學科應當成為一門主要課程的原因。歷史上至少有過不同于今天的境況,對于教學而言,過去的經驗如影隨形,想要擺脫非常困難。我因此提出了“再激活”(Reactivation)這一概念,引導學生“瞥見”其他時刻或可能的道路。
楊:是的,如您所說,“在別處”非常重要。我常常疑惑的一點在于,現在的西方教育界有一種聲音,呼吁要學習中國的基礎教育以及學生學習的方法。但是目前中國的許多課堂甚至還處于“前現代化”的程度,遑論“后現代化”的課堂了。許多學者認為,我們需要先達到教育的“現代化”階段,譬如對數據的重視,高科技的采用,乃至民主精神,然后再走向后現代。但是有人則認為我們可以直接從“后現代”啟程。
派納:我并不認為歷史是分階段演進的,也不認為所有地區都要遵循同樣的歷史進程。就我所理解的中國而言,它是復雜和多樣的,一些農村還處于前現代,但大城市已經擁有非常高的科技水平了。就民主來說,有一種非官方、非政府的存在形態,它發生在大街上,形成于人群中。另外,我們正面臨后現代境遇,對所有事情都爭論不休,外來者和本地人一樣聰明和復雜。所以我覺得中國已經準備好了。
楊:但是還有一種危險,我們可能會拒絕接受別人的經驗。比如,我們會說,別光盯著西方的課堂,他們也正遭受一堆問題的困擾。
派納:確實,只用中國方式同樣也會有問題。當然,不僅僅只有一種“中國式教育”,而是有許多種。不同地區的環境不同,課堂也不同。在我的研究領域中,我非常欣賞中國同行的一點就是,他們想了解西方,但會做出判斷,辨別哪些是自己需要合作的對象,并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
楊:我同意您的觀點。我們或許可以更本源地看待課程與科技的關系。現代課程誕生于管理時代,恰如加拿大籍日裔學者Ted Aoki所言,這是基于規劃的課程。如果我們同意課程理論源于此,那么,我們的道路在何方?回到生活世界,還是走向美學和藝術?于我而言,這是一個兩難問題。
派納:確實是兩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理解這種兩難。通過理解它,知道它產生的原因,知曉它如何成為歷史的,了解隱藏于其后的原因,我們就能找到超越它的經驗,并對下一步行為做出建議。我理解你們可能處于的境地。我們的政府曾經對我們說:“走開,你們是麻煩制造者。”他們現在希望通過商業操作來解決問題,雖然也會失敗,但人們沉迷于其中。我想,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充分理解這種兩難。我并不認為我們的工作會被這種兩難所捆綁,當然,我們的力量也很微小。
楊:是的,在時代面前我們微乎其微。我想起了海德格爾曾經探討過工具“在手”的狀態,我的疑惑是: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和現代社會都有工具和技術,那么它們之間有什么實質的區別?錘子在手的狀態和現在拇指黨的狀態有什么不同?我看不出太大的區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派納:我認為“在手”客體的改變會帶來主體關系的改變,以及“在手”的變化。你可以成為一個樂觀主義者,沒必要成為悲觀主義者,因為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事態會往哪個方向發展。在短期內,可能只有一點曙光,這就是我們成為現實主義者的原因。但你可以有所作為,可以繼續教學。我在高校剛入職的時候,有一次校長來聽新教師的課并給出評價。但我沒有因為校長來聽課而做出任何改變,我依舊讓學生以非常放松的姿態進行交流。我想,他能看出我在做什么:我正在用自己的聲音、方法,讓學生互相交流并沉浸在課堂中。
將教育和就業、經濟狀況聯系起來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在我年輕的那個年代,教育更多地關乎自我發展。當然,我覺得政府會很高興看到今天的這種改變。按照我的理解,課程的領域非常廣泛,而不僅僅包括諸如語言、數學、藝術等在內的學校科目。當然,也要有一些正式的課程,來滿足人們的具體需求。討論課程其實就是討論不停累加的教育經驗,而不是限于特定的學科領域中,因為這些經驗是互相交叉的。
楊:是的,我非常贊同您的觀點。就像Ted Aoki曾經說過的,課程就像一座橋梁,我們更需要的不是快速通過,而是在橋梁上凝視(Contemplation)、徘徊(Lingering)。我更愿意將之理解為一種游戲與悠游的狀態。我們常說要打開課程的“黑箱”,但是我現在愈發覺得打開的方式很重要。采用像醫生那樣打開病人腹腔的方式恐怕是不妥的,老實說,我倒是覺得“黑箱”是一種保護。
派納:這個關于“黑箱”的說法,我很欣賞。
楊:說到“上手”,我最近正在思考身體和課程的關系,回到身體或許是件有趣的事情。中國傳統觀念中的身體可能和西方觀念不太一樣,這或許是個理論的突破口。在中國傳統觀念中,身體不僅包括自然的身體,也包括社會的身體和某種意義上超越的身體。它們之間的關系非常微妙,有時候甚至是以通過對一種身體的壓制或削弱的方式來獲得另一種身體的解放。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中國戲劇《牡丹亭》,在其中主人公因為生病而得以在夢中再續前緣。通過對自然身體的削弱,她暫時擺脫了社會身體的壓制并使得超越的身體成為可能。因為,在湯顯祖的觀念中,至情即道。
派納:在西方也有類似的經驗。我記得曾有一位美國作家在旅行至摩洛哥時患病高燒,他認為通過這段病痛的經歷,我們得以理解自我,理解自我和身體的關系。對我來說,年輕時病患是我的朋友,而現在它卻試圖殺了我。
楊:最后向您請教一個我個人非常感興趣的問題:作為課程理論界的大家,您覺得課程理論的發展趨勢是什么?您曾經領導了課程理論的概念重建主義運動,您覺得下一個10年或20年,在課程理論界可能會發生什么?
派納:我覺得這取決于不同國家,取決于在哪里提出問題。在美國,我看不出有什么能超越個人中心,這是一種身份政治。幾乎所有人都堅持認為,自己受到的傷害多過他人。他們呼吁保護個人權益,譬如黑人和白人的種族問題,這表明社會生活會受到極端政治的威脅。課程理論應當對此做出回應。我呼吁課程研究從個人政治轉向倫理領域,希望人們可以超越對于“革命”的渴求。就我現在所在的加拿大而言,我還看不到具體的前景。如果我接下來幾年沒有退休,我將從事加拿大的課程理論研究,了解它的過去并描繪它的未來。我曾經編撰過一本關于國際課程研究的手冊,張華教授在其中一個章節中曾描述并展望過中國課程研究的現狀與未來。
對話手記(楊澄宇):我震驚于派納教授廣博的知識、深刻的見解。這樣的體驗不僅來自于和他的對話,也來自于對他著作的閱讀和諦聽他的授課。他不僅坦誠率真并善解人意,而且對同行的工作充滿尊重。在課堂上,當他介紹Ted Aoki的思想時,我似乎感受到歷史正拂過我的肌膚。對于我所請教的問題,他總是會在第一時間列出詳盡的書單。溫哥華是座美麗的城市,有著眾多的華人和日益高企的房價;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在城市的一角,面朝大海和雪山。在對話結束的時候,在回去的路上,我問派納教授怎么看待去年其所在的教育學院排名上升到了世界前十的問題。他笑道:“因為我在這里啊,噢,不,我不知道原因,我是在開玩笑。”最后,我們談論了生活。(2016年7月12日,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溫哥華)
(責任編輯 童想文)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1.011
威廉·派納(William Pinar),著名課程理論家,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研究首席教授,概念重建主義運動的代表性人物,曾任國際課程研究促進協會主席,亦是其美國分會的創始人。2000年,派納獲得美國教育研究協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2004年其著作WhatisCurriculumTheory獲得美國教育研究協會頒發的杰出著作獎。楊澄宇,本文通訊作者,華東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講師,博士,研究領域為語文課程與教學論、教育現象學等;2016年出版著作《語文生活論》(教育科學出版社),此前亦出版過詩集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