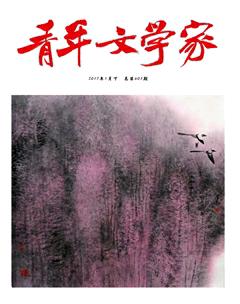《帶燈》方言詞淺析
何楠楠
[中圖分類號]:H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3--01
語言與文學,二者的聯系是非常緊密的。語言是文學的載體,同時語言也是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則是語言的升華。不同地域的作家由于受自己所在地區的方言土語的影響在寫作中便會不自覺地運用這種方言,形成自己獨有的語言習慣。語言的恰當使用,不僅能表達出作者思想感情,更是能體現出作品的特色與其地域文化。讀過賈平凹的文學作品的讀者都會有一種明顯的感觸——他對方言詞運用得爐火純青。下里巴人說的圖畫在賈平凹這里卻登上了文學這座大雅之堂。細細品味,這種文學語言也是別有一番滋味的。文章主要從賈平凹最新的文學作品《帶燈》方言詞入手,探討其方言文化和文本價值。
一、作品中的方言詞
根據統計,《帶燈》中共出現方言詞106個。筆者按照詞的性質將這些方言詞分為六大類,分別為名詞31個、動詞45個、形容詞23個、副詞3個、量詞2個、感嘆詞及擬聲詞2個。在同一性質的詞下,按首字母排列順序列出作品中的方言詞,位于方言詞右上標的數字為詞頻,其次為釋義,隨后舉出作品中的例子,在此僅列出部分例詞例句。
(一)名詞
額顱11:顙,額頭(眉上發下部分)。
(1)他頭撞在墻上,額顱往下流血。關中人習慣將額頭叫“額顱”。
(二)動詞
瓷2:本意是用高嶺土燒成的一種質料,所作器物比陶瓷細致而堅硬。在關中方言中多用來形容人不動、呆頭呆腦的。
(2)馬連翹瓷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面對自己老伙計的慘狀,帶燈內心是十分感慨的。“瓷”的使用,表現出帶燈對往事的回憶及對自己老伙計的同情與悲痛。“瓷”在關中方言中有動詞和形容詞兩種詞性。動詞為發呆、呆立不動之意,形容詞即形容人呆頭呆腦、笨拙的樣子。在《帶燈》中,為動詞“瓷”的運用。
(三)形容詞
稀3:形容人長的漂亮。
(3)那些人也就不敢硬塞,說:櫻鎮上還有這么稀的女子!原字為皙,皮膚白皙之意。賈平凹用“稀”來代替“皙”,屬于別字。但“稀”一方面為“皙”的另一種寫法,另一方面也包含了“稀”本字的另一含義,即帶燈的美在櫻鎮是很少的,十分稀罕。
(四)副詞
恁19:那么、那樣、如此。
(4)馬副鎮長就說:人就恁容易死!?
(五)量詞
頁1:指數量的量詞,不僅指書頁,而且指磚、瓦等。
(5)樹就被鋸斷了,枝干倒下來靠在房間后檐上,砸壞了四頁瓦。在關中農村多用來指瓦的數量。
(六)擬聲詞及感嘆詞
失1:擬聲詞,通常是趕牲畜時的發音。
(6)毛林哭著哭著,一扭頭,看見雞上了柜蓋,在篩子里吃麥,說:失!把雞攆走了。(P104)此處為趕雞時的擬聲詞。
二、方言詞對帶燈人物形象的刻畫作用
(一)現實化的農村女干部形象
在小說《帶燈》中,賈平凹對不同的人物語言有不同的著筆。作為小說的主人公帶燈,她是櫻鎮綜合治理辦公室的年輕女主任。賈平凹在塑造帶燈這一角色時,對處于不同位置的帶燈所賦予的語言是不同的。當帶燈面臨形形色色的上訪者,面對綜治辦的各種任務,當她騎著小摩托到各村調查時……這些時候,帶燈的語言都是比較方言化的。如:(7)帶燈說:我有宿舍,我笨狗扎的什么狼狗勢力?
在關中有“笨狗扎的狼狗勢”這樣一句方言,意思是沒有什么真本事還喜歡擺譜。身為櫻鎮綜治辦主人的帶燈,她的語言可說是十分接地氣的,賈平凹讓帶燈“說”出的方言十分的恰當。
(二)理想化的柔情與細膩的女性形象
雖然帶燈是一名農村基層女干部,可是她一出場就與眾不同,帶有超凡脫俗的氣質。當她對現實中的一些事情無可奈何的時候,她把理想放在想象的情感之中,遠方的親人元天亮便成了她的情感寄托,是她在濁世中的依靠,已為人妻的帶燈不斷地向元天亮寫信訴說,因為和丈夫沒有共同語言且對元天亮的崇拜使得元天亮成了她的傾訴對象。據統計,小說中共有24封“給元天亮的信”。
(8)我趴在窗戶上還是仰望著夜,天是模糊的,但仿佛有光,我的身子在黑暗里發白,星星出來了,星空浩淼如海。
這24封“給元天亮的信”充分展示了帶燈的文采,其語言之優美、情感之細膩、神思之癡狂使人根本看不出這是一名基層農村女干部寫出來的信。在這些信中帶燈很少使用方言詞,即使有個別語句中應用了方言詞那也是帶有一絲文氣的詞。
元天亮是櫻鎮的能人,是一名文化人。帶燈在寫給元天亮的信中語言可說是十分細膩的,絲毫不見農村人語言的粗獷與隨意。在寫給元天亮的信中,帶燈大膽表露著自己的感情,她善良聰穎,純粹而又不做作。信中的語言充滿了山間田野的氣息,展現了一名女性特有的柔情與細膩。
說帶燈的理想化還有一方面是她對改造農村的理想化。帶燈的形象與櫻鎮格格不入,她的美在櫻鎮是很“稀罕”的,同樣,進入櫻鎮的帶燈,她的心也是孤高的。她所處的櫻鎮像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哪落灰。她沒有想著在櫻鎮當官,而是在干著一系列的實事,可在一系列的行動之后,帶燈突然意識到,面對自己改變不了的東西,最好的方式就是改變自己。帶燈想要憑借自己的力量改變櫻鎮的想法一次次被打擊,或許,那真的是她的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