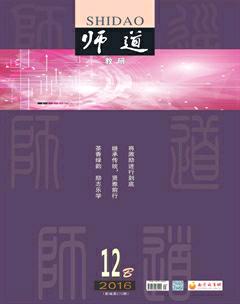語文課可以這樣上
黃錦文
近日,偶然的機(jī)遇,拜讀了吳忠豪教授的文章《關(guān)于小學(xué)語文課程改革的幾點(diǎn)思考》,又回想起一年前在南京參加的國(guó)培計(jì)劃(2013)一線優(yōu)秀教師培訓(xùn)技能提升研修項(xiàng)目時(shí),聆聽吳教授的講座《課改路在何方》。吳教授對(duì)語文課程的獨(dú)特理解,對(duì)語文教學(xué)的深刻思考,對(duì)當(dāng)下語文課堂教學(xué)的精僻分析,讓當(dāng)時(shí)聽講座的我們這些一線語文老師熱血沸騰,難抑心中的激動(dòng)。尤其吳教授講到語文課堂中“以講讀為主”的語文課程形態(tài),原本“聽說讀寫”并重的語文課,變成了“以講讀為主,聽說寫為輔”的“主從關(guān)系”,更是引發(fā)了我們這些飽受語文教學(xué)之苦的一線教師的共鳴,臺(tái)下不時(shí)響起因共鳴而激發(fā)的掌聲。確實(shí),當(dāng)下的語文教學(xué)存在“教”得過度的問題,語文課成了老師主宰講解分析,學(xué)生自主學(xué)習(xí)實(shí)踐嚴(yán)重不足,以致出現(xiàn)了大多數(shù)語文示范課上,學(xué)生竟然可以只聽不寫的咄咄怪事。語文教育專家周一貫老師把這種現(xiàn)象稱之為“高耗低效”現(xiàn)象。試看現(xiàn)在的語文課堂,整堂課都是以教師講解課文為主,老師根據(jù)自己對(duì)文本的理解,對(duì)文本的解讀,或根據(jù)教參的要求,單純講故事情節(jié)或抽象地講述思想內(nèi)容,語文課成了基于教師感情的文本分析,閱讀與表達(dá)嚴(yán)重失衡。一堂課下來,老師都是課堂的主角,學(xué)習(xí)課文的主角,學(xué)生乃是配合老師完成教學(xué)內(nèi)容的配角。老師需要讀的時(shí)候,學(xué)生“一二讀”,老師的教學(xué)設(shè)計(jì)里需要“感情讀”的時(shí)候,學(xué)生很配合地,似乎真的就能按老師的要求,帶著“xx”的感情讀。說句實(shí)話,學(xué)生真的讀到那份上嗎?即使真的讀到那份上了,就真有這樣的體驗(yàn)了嗎?即使真有那體驗(yàn),這節(jié)語文課又達(dá)到了哪種目的和教學(xué)效果呢?學(xué)生的語文水平又有了哪些長(zhǎng)進(jìn)呢?
《語文課程標(biāo)準(zhǔn)》指出:語文課是一門實(shí)踐性很強(qiáng)的課程。我認(rèn)為,工具性與實(shí)踐性是語文課的本質(zhì)屬性。語文作為一種社會(huì)交際工具,最核心功能在于能夠熟練“運(yùn)用”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參與社會(huì)交際。英國(guó)的哈羅德·帕爾默博士也指出:“衡量學(xué)生是否學(xué)會(huì)語文,不是看‘理解了多少語言知識(shí)和規(guī)則,也不能僅僅看‘積累了多少詞語句子,而是應(yīng)該看他是否能夠熟練地‘運(yùn)用這種語言為評(píng)價(jià)的主要標(biāo)志。”
基于此,筆者認(rèn)為語文課是可以從聽、說、讀、寫四大基本功入手,設(shè)計(jì)教學(xué)流程,抓好每個(gè)環(huán)節(jié)的教學(xué)與訓(xùn)練,從而切實(shí)提高學(xué)生的語文素養(yǎng)與語文能力。筆者提出,語文課可以這樣上:
聽:聽,分兩大方面的內(nèi)容:一,聽寫。課上先進(jìn)行聽寫檢查,聽寫的內(nèi)容是本課需重點(diǎn)掌握的生詞、關(guān)鍵句(這是檢查預(yù)習(xí)的階段),教師批改、生生互改。二,聽讀。出示與課文內(nèi)容相關(guān)的問題,學(xué)生不打開書本,聽讀課文(錄音范讀、學(xué)生讀),訓(xùn)練學(xué)生專心聽的能力。用耳朵聽,是最容易走神,所以訓(xùn)練學(xué)生帶著問題專心聽的能力,是關(guān)鍵。聽完之后,回答與課文內(nèi)容相關(guān)的問題。這個(gè)環(huán)節(jié)主要是加強(qiáng)學(xué)生對(duì)課文內(nèi)容的理解。
說:說的訓(xùn)練,主要是進(jìn)行概括課文內(nèi)容的口頭表達(dá)能力訓(xùn)練。
讀:讀是理解的基礎(chǔ)與根本,讀也是語文課上必不可少的。然而,不是為了讀而讀,讀必須是有目的,有指向性的。所以,讀這個(gè)環(huán)節(jié),筆者認(rèn)為,應(yīng)是讀文本中難理解的內(nèi)容,需要反復(fù)斟酌、細(xì)味的部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重點(diǎn)、難點(diǎn)。同時(shí),這一環(huán)節(jié)不純粹是反復(fù)地讀,更是通過細(xì)讀文章重點(diǎn)部分,從而滲透學(xué)法的指導(dǎo),讓學(xué)生掌握學(xué)習(xí)語文的方法,提升語文能力。這是語文教學(xué)責(zé)無旁貸的責(zé)任,正所謂得法于課內(nèi),得益于課外。語文學(xué)習(xí)方法的滲透,要根據(jù)文本內(nèi)容與實(shí)際選擇訓(xùn)練重點(diǎn),讓學(xué)生逐漸掌握各類語文學(xué)習(xí)的方法,熟練運(yùn)用各種語文學(xué)習(xí)方法解決問題。如:聯(lián)系上下文理解詞語,抓關(guān)鍵詞、關(guān)鍵句理解,體會(huì)作者的情感等等,這些都是語文學(xué)習(xí)的有效方法。
寫:語文學(xué)習(xí)的最終目標(biāo)是表達(dá),檢驗(yàn)語文學(xué)習(xí)的成效,最實(shí)際有效的方法就是看學(xué)生寫作與表達(dá)的水平。每節(jié)語文課都應(yīng)該有寫的訓(xùn)練。這里的寫,指的是語言文字的實(shí)踐練習(xí),也就是輸出的環(huán)節(jié)。這個(gè)環(huán)節(jié)甚至可獨(dú)立成一節(jié)課進(jìn)行專項(xiàng)訓(xùn)練,當(dāng)堂訓(xùn)練,當(dāng)堂評(píng)講,當(dāng)堂訂正修改。訓(xùn)練的內(nèi)容包括語言的運(yùn)用,語言的實(shí)踐、語言表達(dá)等。
筆者構(gòu)思的語文課,聽、說、讀、寫,環(huán)環(huán)緊扣,目的明確,訓(xùn)練到位,改變了“以講讀課文”為主的教學(xué)形態(tài),教師的教學(xué)相對(duì)過去纖夫拉船式的教學(xué)要輕松自如,學(xué)生從被動(dòng)接受、被動(dòng)聽課轉(zhuǎn)為課堂的主人。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語文課指向?qū)W生語文能力的訓(xùn)練,相信對(duì)學(xué)生語文能力的提升與語文水平的提高大有裨益。
責(zé)任編輯 黃日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