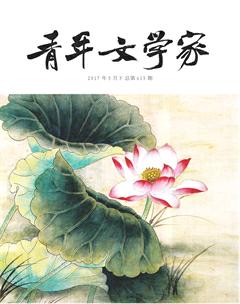淺論詩歌創作實踐
摘 要:詩歌歷史源遠流長,詩歌創作歷久彌新。本文從詩詞照亮現實著墨,結合自身的創作實踐,去鉤沉和梳理一段詩詞的記憶,講一段關于詩詞的當代故事。
關鍵詞:詩歌;創作;實踐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5-0-02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詩歌在浩瀚的文學大觀園里可謂一枝獨秀,千古品評,耐人尋味。在當今“文化自信”思想的感召下,詩歌這一深厚的文化土壤如何勃發生機,生長出具有時代烙印的文字,對于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浸潤人民心田,提振民族精氣神,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本文從詩詞照亮現實著墨,結合自身的創作實踐,去鉤沉和梳理一段詩詞的記憶,講一段關于詩詞的當代故事。
一、“詩言志”,“詩緣情”——詩抒情言志
關于詩歌創作的目的,提出了“詩言志”和“詩緣情”。“詩言志”萌芽于《詩經》。作為一個理論術語提出在《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有趙文子對叔向所說的“詩以言志”。后來《尚書·堯典》中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莊子·天下篇》有“詩以道志”,《荀子·儒效》有“《詩》言是其志也”。
隨著對詩歌本質特征認識的深入,中唐時期韓愈等古文運動家提出了"文以貫道"的理論,宋代理學家周敦頤在《通書·文辭》中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提出了“文以載道”, 說"文"像車,"道"像車上所載之物,通過“文車”的運載,“道物”可以達到指向的目的地。曾經風靡熒屏的電視劇《亮劍》,確為當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為澆胸中塊壘,筆者反復觀看之后寫下了《觀<亮劍>有感》:
之一
進退留轉太平常,組織意圖最難忘。趙剛走馬任政委,云龍復出訓野狼。
之二
政委團長好搭檔,知識工農結合棒。政委原是神槍手,笑談闊飲服野狼。
之三
觀摩戰法到戰場,摞倒云龍喝肉湯。云飛黃埔論劍法,蔣閻戰區夸野狼。
之四
云龍云飛征戰忙,不論我弱與敵強。狹路相逢敢亮劍,嘯傲長空看野狼。
這胸中的塊壘,就是如何理性對待“進退留轉”,如何正確理解“組織意圖”,如何團結協作,如何務實擔當。這是筆者的“志”之所在。
針對“詩言志”,后代詩論提出“詩緣情”。“詩緣情”出自陸機的《文賦》“詩緣情而綺靡”。“緣情”即因情而動,因情而作;“綺靡”即華艷美好,言之有文。由于對“志”的內容的不斷豐富,對“志”的側重點也各有不同,有人甚至把“言志”和“緣情”對立起來,以致衍生出重理和重情兩派。客觀而論,中國一部詩歌史,是情理并重的歷史。
從《毛詩序》到劉勰,從孔穎達到白居易,從葉燮到王夫之,莫不如此。他們強調詩歌既應觀照現實,又應感物吟志;既為教化服務,又突出其抒情性。情物交融,情志并重,實現了功利性與藝術性兩不偏廢,完美統一。《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發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既反映了“詩言志”的文學思想,又突出了文學創作的蓬勃感情,是作者情懷和思想的有機統一,是詩歌抒情言志的美麗注腳。
筆者在創作了《觀<亮劍>有感》后,“情動于中”而不能自靜,于是創作了《沁園春·劍》:
晉中大地,千里戰壕,萬里沙飄。望營房內外,刀劍霍霍,肉鍋上下,沸沸滔滔。糧食敵借,槍炮敵造,重創日頑功勛高。解放迫,看淮海云飛,血染戰袍。
野狼遠勝神雕,引蔣閻云飛競折腰。昔坂田聯隊,悉數干掉,山崎大隊,全軍報銷。一代英豪,堅苦卓絕,亮劍云天豈大雕?俱往矣,聽胸中回響,野狼嗷嗷。
通過《沁園春·劍》,更深層次地把“狹路相逢敢亮劍”的亮劍精神鋪于紙上,躍然心間,展于眉梢,溢于言表,做到了“情”與“志”的有機結合,主動呈現,動己動人。
二、“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詩為時為事
關于詩歌創作的對象,新樂府運動倡導者白居易曾在《與元九書》中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反映時事,即“多詢時務”,即詩人《秦中吟序》所謂“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二是反映現實,即詩人《與元九書》所謂“裨補時闕”。白居易為時為事而著而作的主張,是對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的繼承,是對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重要貢獻。
《詩經·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誓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中“樂土”的渴望,正是對春秋戰國時代魏國的農奴不堪沉重的剝削和壓迫的現實再現。對他們心中的樂土,懷有極其強烈的向往之情。
面對當今以德治國、依法治國的治國理政大勢,面對舉國上下“打虎”“獵狐”“拍蠅”的高壓反腐,筆者在教學《竇娥冤》一文時,感時感事,寫下了《沁園春·冤》:“楚州大地,三樁誓愿,千古奇冤。望旗槍之上,血濺白練,六月飛雪,怨氣沖天。東海孝婦,亢旱三年,竇娥銜冤赴黃泉。官吏每,都無心正法,百姓淚漣。 地也不分好歹,斥錯勘賢愚枉做天。昔梁祝化蝶,當壚舉案,萇弘化碧,望帝啼鵑。一代烈女,感天動地,平反昭雪見青天。俱往矣,建法治中國,譜寫新篇。”希望“建法治中國,譜寫新篇”迫切,溢于言表。
面對特教學校殘疾孩童,回顧那些身殘志堅的勵志故事,頓時產生了“感時花濺淚”的心靈共鳴。這就是《假如——獻給特教孩子的歌》:“假如給我三天光明/假如給我三天鳥鳴/假如給我三天獨行/假如給我三天淺唱低吟/不/沒有假如/行動才能照亮心靈”。既白描了盲、聾、跛、啞等殘疾孩童的渴望,也希望用勵志故事讓他們揚起風帆,用行動照亮心靈,做出正常人羨慕的業績,成就屬于自己的價值人生。
三、“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功夫在詩外
清朝孫洙在《唐詩三百首序》中寫到:”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即“熟能生巧”“厚積薄發“。詩讀多了,讀熟了,就能從”模仿“到”轉化“,從”借用“到”引申“,達到張口就能背,提筆就能寫的境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專門指出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的三重境界:一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二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熟讀”是第一重境界,“會吟”是第二重境界,“作詩”是第三重境界。可見,不經一番寒徹骨,難得梅花撲鼻香。“熟讀”是經歷徹骨之寒,“作詩”是收獲撲鼻之香。
宋朝大詩人陸游在《示子遹》(《劍南詩稿》卷七十八)中說:“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宏大。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瀨。數仞李杜墻,常恨欠領會。元白才倚門,溫李真自鄶。正令筆扛鼎,亦未造三昧。詩為六藝一,豈用資狡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這種詩外功夫,正是“學詩”之至理,“作詩”的題中之義。對作詩,不僅應知押韻、知句式、知修辭,還應知內容、知意境、知中外、知古今。這種“知”的功夫,不僅在知識的淵博,更在實踐的廣闊。正如陸游所言:“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廣泛的生活實踐正是“詩外功夫”。為了寫好古典詩詞,特別是“沁園春”這一詞牌,筆者在廣泛記背唐詩宋詞的基礎上,對毛澤東詩詞幾乎達到熟讀成誦的地步。因而為時為事,抒情言志,撰寫了二十余篇以“沁園春”為詞牌的詞作。
以上是筆者在撰寫詩詞上的點滴體會,也是對古今詩詞大家踐行創作實踐的有益嘗試,特就教于方家與同行。
參考文獻:
[1]高永貴.試析唐詩中的“雨中情”[J].短篇小說,2013(6).
[2]高永貴.觀《亮劍》有感[J].金田,2016(4).
[3]高永貴.寫作的原因淺析[J].金田,2016(5).
[4]高永貴.寫作動力與寫作者主體探討[J].青年文學家,2016(4).
[5]田耕宇.杜甫詩歌創作主觀動機研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1(8).
[6]言嵐.詩歌創作情感與文學修辭藝術[J].河北學刊,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