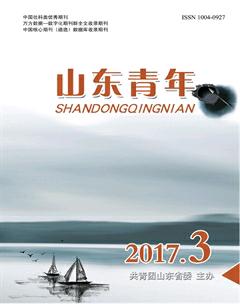從佛教的中國化看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性
蒲怡囡
摘 要:佛教從西漢末、東漢初年傳入中國,經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和改造,形成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教。而且其中某些思想觀點、思維方法,又被儒道學派所吸收,并逐漸融合成為中國特有的哲學思想體系。這些現象的產生與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的包容性有著極大的關系。
關鍵詞:傳統文化;佛教中國化;和合;包容性
在世界四大文化體系中,中國傳統文化被認為是惟一沒有中斷的文化體系。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沒有中斷,原因當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強的包容性。正是這種包容性,維系了中國傳統文化脈絡綿延不絕,它所哺育出來的民族精神維系了我們民族生生不息。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為主體的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性首先體現在厚德載物思想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自然的理解是,天地最大,它能包容萬物,天地合而萬物生、四時行。從這種對自然的理解中引申出做人的道理:人生要像天那樣剛毅而自強,像地那樣厚重而包容萬物。維系中華民族精神的主體文化是儒學。儒學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里對中華民族在思想方式、行為規范、道德禮儀等各個方面,長期起著支配作用。儒學主張泰山不辭細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這種精神使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對外來文化向來不排斥。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川流不息,正是由于其吸納百川的結果。
中華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在于“和合”二字,“和同之辨” 肇始于西周末年的史伯, 他說,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所謂“和”就是不同事物均統一、和諧或摻和, 是以諸因素的差異性為前提的動態聯系。所謂“同” 指相同東西的簡單相加或同一。“和”對于我們民族心理的形成具不很大的影響。“和” 的心理傳統能休現出民族的特色。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傳》的“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都是主張思想文化的多元開放。這種多元開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使儒學不斷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為一種綿延不絕的思想體系。另一方面,這種多元開放的文化理念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傳統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并蓄的傳統。錢穆先生說:“中國人常抱著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外面一切異樣的新鮮的所見所聞都可融匯協調、和凝為一。這是中華文化最主要的一個特性:文化發生沖突只是一時之變,要求調和乃是萬世之長。中華文化的偉大之處乃在最能調和。”
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強大的同化力為前提的。它用這種強大的同化力去影響和改造外來文化,使之具有中國的特色。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性是吸收外來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基礎,沒有這樣一個基礎,不僅不能消化、吸收外來文化,還有可能被外來文化所同化,從而喪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由于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包容精神,其結果是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不斷同化外來文化。外來文化的進入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卻并沒有使中國傳統文化喪失其特有的本色。一切外來文化一旦進入中國,便開始了中國化的進程。中國社會強烈的寬容氣氛,甚至使得一些獨立性很強的外來文化,也在不知不覺中融合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之中。
佛教從西漢末、東漢初年傳入中國,經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不但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而且其中某些思想觀點、思維方法,又被儒道學派所吸收,并逐漸融合成為北宋時期的哲學思想體系。
佛教在傳入中國之初為了自身的生存,就已經采取了中國化、通俗化的手段,主要是以黃老釋佛。如安世高譯《安般守意經》,釋“安為清,般為靜,守為無,意為明,是清凈無為也。”東晉道安則以《老子》解《般若經》。安史之亂后,儒釋道三教在思想觀念上互相融匯。儒家在堅守孔孟倫理和社會政治思想的同時,廣泛吸收道家和佛教的心性之學,充實自己的理論體系,這一時期的士大夫往往在思想上具有二重性,即在政治上推崇儒學,在生活則出入佛老。正是這種對佛性的吸取,使儒學開始向新的理學方向轉化。儒學接納佛教義理,佛學也不斷吸收儒學和老學的成分,使得佛教在唐代形成了具有濃厚中國本土特色的宗派,如天臺宗、禪宗。它們一采納道家的自然主義為開端,又淡化出世色彩向世俗靠攏,盡量減少同儒家倫理的沖突。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僧徒以“人皆可以為舜堯”解釋佛性,并出現了專講孝道的佛經。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崇尚倫理道德的, 而人的主體性是一切道德活動的原動力。道德規范歸根到底是人的經驗,人的社會需要的產物,而非外在于人的異已力量。因此尚德的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即可以說是尚人的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崇高人倫道德的特點在對“孝”這一道德規范的倡導中得到了體現。原始佛教的內容和中國傳統“孝”道有著天壤之別。中國自古就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的說法,而佛教正是主張無君無父、絕嗣為木;中國的傳統是視家庭為享受天倫之樂的基本單元,而原始佛教則主張辭親出家,視家庭為牢籠。于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文化與外來佛教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其結果是,佛教逐漸附會儒家對孝道認可,直至對原始佛教背悖,與世俗凡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地張揚孝道。在老學和儒學的影響下,佛教的外來色彩逐漸淡化。
儒釋道三教的合流,對于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儒學吸取了佛教宗教哲學的某些論證方法,使自身的哲學思辨,尤其是在本體論上有所建樹;佛教的中國化,使其多數宗派具有了世俗色彩,吸收儒學中的倫理因素;道教則把倫理上的探討與外在修煉方法相分離,從佛教和儒學中吸取營養,開始創立新的道教理論。這些都為五代宋元思想文化發展提供了前提。
對于宗教來說,人的生存只不過是為了永生的準備而已,而目的只在于虛無縹渺的彼岸世界的到達,目的只在于“出世”,現實人生是微不足道的。而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則是以肯定現實人生為前提的。一般來說,佛教宗教精神都重視人的主體意識,即“心”的作用,而且關于主體意識的分析比較細致,把“心”看做是脫離物質存在的絕對。這種思想對于中國思想文化有較大的影響,宋明時期形成的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其思維方式直接受到禪宗的影響。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除所謂的“主體意識”論之外,還有“本體”觀念。佛教從西漢末東漢初年傳入中國,與中國傳統文化逐漸融合,經歷了很長的時間,佛教不但中國化了,而且也成為形成中國文化中新的思想體系的一種有影響的思想資料。
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國社會思想文化在內部形成豐富多彩、生動活潑的局面,在外部則向世界開放,不斷接受異質文化的激發和營養,從而使自身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充分發掘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包容精神要求我們要自覺地、不斷吸納外來文化,借鑒其他文化的優秀文明成果。佛教在中國傳入、發展的過程, 就是由神道到人道,對儒家文化認同、并為儒家文化吸收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的鮮明的現世的人格主題非但沒有被浸沒而且通過宋明時期心性問題的闡發,變得更加豐富了。所以,這種吸收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積極態度。中國傳統文化是以“人”的內容與“和”的形式相統一為特征的,兩者之間,既有適應的一面,又有不適應的一面。適應的方面主要體現在中國文化通過“和”的機制,吸收了外來文化的精華,從而豐富了儒家文化為主干的“人”的文化。正因為有以“人”為主題的豐富文化,才使得中國屢經劫亂而文化不絕。
[參考文獻]
[1]張曉華.佛教文化傳播論.[M].人民出版社出版.
[2]張豈之.中國思想文化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3]張豈之.中華人文精神.[M].陜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單位:陜西學前師范學院,陜西 西安 71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