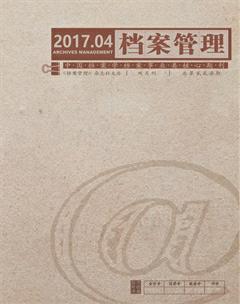檔案正義論質(zhì)疑
王笛
摘 要:文章首先提出社會(huì)正義的取向問(wèn)題是檔案正義必須解決的問(wèn)題。其次從檔案留存的初衷不是維護(hù)正義、檔案工作者的職責(zé)不是維護(hù)正義兩方面論述了檔案正義不能成為檔案管理的工作準(zhǔn)則;從檔案正義理論依據(jù)不可靠、檔案正義驅(qū)動(dòng)力不足兩方面論證了檔案正義無(wú)法成為檔案事業(yè)的發(fā)展方向。文章認(rèn)為,有關(guān)“檔案與社會(huì)正義”還存在許多有待解決的問(wèn)題,正義無(wú)法作為檔案工作的法則和檔案事業(yè)的方向標(biāo)被提倡。
關(guān)鍵詞:檔案;社會(huì)正義;檔案正義
Abstract:The article first puts forward that the orientation of social justice is a problem that the “archives for justice” must be solved. Secondly, social justice cannot be a working guidelines a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preserving the records is not to maintain justice and the duty of the archivist is not to safeguard the justice.“Archives for justice” can not become the standard of the archive management. Social justice can also not becom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rchives since the theory of “archives for justice” is unreliable and the driving force is not enough.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about “archives for justice”,that justice can not be promoted as a rule of archives and archivists.
Keywords: Archives;Social justice;Archives for justice
“檔案與社會(huì)正義”是近年來(lái)檔案?jìng)惱硌芯康臒衢T話題之一,檔案在社會(huì)正義的維護(hù)中能夠發(fā)揮怎樣的作用、檔案工作者在社會(huì)正義的維護(hù)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等問(wèn)題引發(fā)了許多檔案學(xué)者的思考與討論。維恩·哈里斯(Verne Harris)作為“檔案與社會(huì)正義”研究領(lǐng)域的重要代表,認(rèn)為無(wú)論是否處于面臨壓迫和轉(zhuǎn)型時(shí)期的社會(huì),檔案工作者都應(yīng)該積極參與反抗壓迫、追求民主的政治活動(dòng),以正義為檔案事業(yè)的發(fā)展方向[1]。蘭達(dá)爾·吉莫森(Randall C Jimerson)也認(rèn)為檔案的保存服務(wù)于維護(hù)社會(huì)正義、保障公民權(quán)利的需要,并提出檔案工作者應(yīng)該承諾自己以及所從事的職業(yè)符合社會(huì)正義的需求[2]。一些檔案學(xué)者支持他們的觀點(diǎn),并開始從檔案應(yīng)從哪些層面追求社會(huì)正義、檔案工作者如何參與到社會(huì)正義維護(hù)中去等角度進(jìn)行研究和探索。我國(guó)檔案學(xué)者付苑[3]、羅亞利[4]對(duì)“檔案與社會(huì)正義”的代表人物和觀點(diǎn)進(jìn)行了梳理和總結(jié),丁先存對(duì)我國(guó)檔案正義的缺失和實(shí)現(xiàn)路徑進(jìn)行了論述[5]。
同時(shí),也有一些質(zhì)疑的聲音出現(xiàn)。國(guó)外學(xué)者馬克·格林(Mark A. Greene)對(duì)“符合倫理道德要求的檔案工作者就是在檔案工作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追求正義”這種觀點(diǎn)表示不認(rèn)同,他認(rèn)為無(wú)論檔案工作是否以正義為目標(biāo),都可以為自己保存了社會(huì)真實(shí)面貌而驕傲[6]。理查德·馬修(Richard J. Matthews)則從解構(gòu)主義出發(fā),認(rèn)為“檔案正義”和“檔案行動(dòng)主義”的觀點(diǎn)是對(duì)德里達(dá)思想的誤讀[7]。
筆者認(rèn)為,“檔案與社會(huì)正義”的研究還存在許多問(wèn)題。對(duì)于受到不公正對(duì)待的群體和個(gè)人來(lái)說(shuō),檔案的確可以成為他們爭(zhēng)取自身權(quán)利、追求社會(huì)公正的重要工具,但檔案正義是否應(yīng)當(dāng)成為整個(gè)檔案事業(yè)的方向標(biāo),檔案正義是否能夠作為檔案工作的最根本法則被提倡,是值得思考和探討的。
1 社會(huì)正義的取向難以界定
“檔案正義”(archives for justice)來(lái)自“檔案”與“社會(huì)正義”的結(jié)合,這就使得“社會(huì)正義”成為一個(gè)不可回避的概念。正如溫迪· 達(dá)夫(Wendy Duff)等人在文章中所承認(rèn)的那樣,社會(huì)正義的概念是復(fù)雜、多樣且難以定義的,而在檔案與社會(huì)正義的研究中,對(duì)“社會(huì)正義”進(jìn)行界定又是十分必要的[8]。那么,如何界定“社會(huì)正義”就成為檔案正義的一大難題。
首先,正義本身是一個(gè)很難定義的詞匯。古希臘哲學(xué)家柏拉圖認(rèn)為正義是一種內(nèi)在的和諧,在于人的各種品質(zhì)在自身內(nèi)各起各的作用,做自己本分的事就是正義[9];同為古希臘偉大哲學(xué)家的亞里士多德將正義與法律相連,認(rèn)為法律的運(yùn)作是以對(duì)公正與不公正的區(qū)分為基礎(chǔ)的,法律是判斷正義的標(biāo)準(zhǔn)[10]。近代則有羅爾斯和哈貝馬斯關(guān)于正義的爭(zhēng)論。羅爾斯的正義是一種“程序正義”,他提出兩個(gè)正義原則,一是每個(gè)人都有平等的權(quán)利去擁有可以與別人的類似自由權(quán)并存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權(quán),二是對(duì)社會(huì)和經(jīng)濟(jì)的不平等安排應(yīng)能使這種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地符合每個(gè)人的利益,而且與向所有人開放的責(zé)任和義務(wù)聯(lián)系在一起[11],第一個(gè)原則體現(xiàn)了“自由”,第二個(gè)原則體現(xiàn)了“平等”。哈貝馬斯對(duì)羅爾斯的“程序正義”進(jìn)行了批判,他主張正義是通過(guò)公民之間的對(duì)話、協(xié)商、交流、談判之后達(dá)成的公式所決定的,公平的對(duì)話程序是達(dá)成正義原則的基礎(chǔ)[12]。從古至今,無(wú)數(shù)思想家、哲學(xué)家對(duì)“何為正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duì)于正義很難給出一個(gè)確切的定義。那么,檔案所維護(hù)的應(yīng)該是柏拉圖的內(nèi)在和諧還是亞里士多德的法律,是羅爾斯的自由與平等還是哈貝馬斯的公平對(duì)話呢?
其次,社會(huì)正義沒(méi)有固定的取向。如果說(shuō),公平是目前大多數(shù)人所認(rèn)可的一種正義取向,但對(duì)公平本身又有不同理解。一方面,許多事物的價(jià)值很難被衡量。例如一份檔案的價(jià)值就很難界定,它不僅僅是一份紙質(zhì)記錄,還可能是個(gè)人資產(chǎn)的憑證、家族記憶的載體。《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檔案法實(shí)施辦法》第28條規(guī)定,“損毀、 丟失或者擅自銷毀檔案館保存的國(guó)家所有的檔案和單位保管的國(guó)家所有的檔案以及集體或者個(gè)人所有的對(duì)國(guó)家和社會(huì)具有保存價(jià)值的或者應(yīng)當(dāng)保密的檔案的……造成損失的,可以根據(jù)檔案價(jià)值和數(shù)量,責(zé)令賠償損失”,那么一份關(guān)乎個(gè)人利益的歷史檔案應(yīng)該責(zé)令損害人賠償多少才算是對(duì)雙方公平公正,這是值得討論的;另一方面,每個(gè)人的價(jià)值取向不同,甲之砒霜,乙之蜜糖,一群人認(rèn)可的公平正義對(duì)于另一群人來(lái)說(shuō)可能是剝削壓迫。如果將時(shí)代因素也考慮進(jìn)去的話,不同歷史時(shí)期社會(huì)對(duì)正義的判斷也是不同的,例如報(bào)仇雪恨這種在古代被視為正義之事的行為在當(dāng)今社會(huì)顯然是不可取的,作為要流傳于后世的檔案,如何保證今日所維護(hù)的社會(huì)正義能夠迎合后代的正義取向呢?
既然正義本身概念難定,社會(huì)正義又沒(méi)有固定取向,那么檔案對(duì)社會(huì)正義的維護(hù)又從何入手呢?
2 檔案正義難以成為檔案工作準(zhǔn)則
2.1 維護(hù)正義不是多數(shù)檔案被留存的初衷。無(wú)論是結(jié)繩、刻契,還是文書、信件,都是形成者為記錄事物、表達(dá)思想而作,為留存信物憑證、備以日后查閱而把這些記錄保存下來(lái)就形成了檔案[13],所謂伸張正義、申訴社會(huì)不公并不是大多數(shù)形成者進(jìn)行記錄的初衷。即使是如司法檔案這類記載著訴求自身權(quán)利、維護(hù)公平正義內(nèi)容的檔案,其形成的出發(fā)點(diǎn)也是作為案件的記錄、審判的憑證以及對(duì)司法的監(jiān)督。檔案的原始記錄性意味著無(wú)論檔案與弱勢(shì)群體有沒(méi)有關(guān)聯(lián)、其內(nèi)容是否有關(guān)社會(huì)的不公正待遇,它都會(huì)作為社會(huì)記憶的載體、國(guó)家寶貴的資源被留存,這也是檔案資源豐富多樣、檔案價(jià)值無(wú)可比擬的原因。
檔案不是為正義而生,這就意味著并不是所有的檔案都能夠?yàn)樯鐣?huì)正義出力。在一些檔案應(yīng)用于社會(huì)正義申訴的實(shí)際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對(duì)社會(huì)正義起到實(shí)質(zhì)性貢獻(xiàn)的是一些特定的檔案資料。例如《記憶、正義與公共記錄》(Memory,justice and the public record)一文講述了挪威“戰(zhàn)爭(zhēng)兒童”為自己因特殊身份而受到的不公正對(duì)待做抗?fàn)帲螳@得身份認(rèn)同和經(jīng)濟(jì)賠償?shù)倪^(guò)程,在這一過(guò)程中,起到關(guān)鍵作用的有證明“戰(zhàn)爭(zhēng)兒童”真實(shí)身份的個(gè)人檔案、“生命之源”計(jì)劃挪威指揮部的文件記錄[14];《打破規(guī)則,拯救記錄:東帝汶人權(quán)檔案和正義研究》(Break the rules, save the records: human rights archives and the search for justice in East Timor)一文以東帝汶獨(dú)立斗爭(zhēng)為例從歷史和政治層面探討了檔案在東帝汶人民追求自決權(quán)利中的角色和作用,其中被運(yùn)用到的是記錄違反人權(quán)情況的檔案文件[15]。但我們不能忘記,在一個(gè)穩(wěn)定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中,更多的是記錄常規(guī)性業(yè)務(wù)活動(dòng)、有關(guān)普通公眾的生平經(jīng)歷的檔案資料,類似“戰(zhàn)爭(zhēng)兒童”檔案、人權(quán)檔案等關(guān)乎受害群體、不公正待遇的檔案只是眾多檔案文件中的一小部分。不可否認(rèn),這類檔案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jià)值,但如果過(guò)分追求檔案正義,以正義作為檔案工作各環(huán)節(jié)的判斷準(zhǔn)則,是否意味著只有對(duì)維護(hù)社會(huì)正義、支持公平公正有用的檔案才會(huì)被保管,而與正義無(wú)關(guān)的一些日常性信息資料就不再受到重視了呢?
在正義準(zhǔn)則下的檔案工作是有目的性的,其目的就是維護(hù)社會(huì)正義,這樣的目的性會(huì)帶來(lái)選擇,有選擇就會(huì)有舍棄,有舍棄就不可能全面完整。而對(duì)于一些學(xué)者將檔案正義與檔案資源的完整保存相關(guān)聯(lián),認(rèn)為豐富館藏、保障公民平等利用檔案就是實(shí)現(xiàn)檔案正義的觀點(diǎn),筆者并不認(rèn)同。對(duì)社會(huì)正義的維護(hù)應(yīng)該是對(duì)反抗不公、追求公平等活動(dòng)的主動(dòng)參與,而豐富館藏、提供利用是檔案工作的本職,只能算作對(duì)社會(huì)正義行為的被動(dòng)支持,沒(méi)有弱勢(shì)群體、受迫害群體對(duì)檔案的利用,檔案所謂的正義價(jià)值就沒(méi)有體現(xiàn),因此被動(dòng)的期待并不能作為檔案事業(yè)對(duì)社會(huì)正義的主動(dòng)追求。
2.2 維護(hù)正義不是檔案工作者的主要職能。從社會(huì)層面看,檔案職業(yè)的首要責(zé)任不是維護(hù)社會(huì)正義。
職能的專業(yè)化趨勢(shì)來(lái)自分工的影響,社會(huì)分工不僅是一種行為規(guī)范,同時(shí)也會(huì)被當(dāng)作一種責(zé)任[16]。每個(gè)人在自身的分工內(nèi)各司其職、各行其是,構(gòu)成了社會(huì)機(jī)器的有序運(yùn)轉(zhuǎn)。現(xiàn)代社會(huì)中法律與正義的關(guān)聯(lián)最為緊密,英文中“justice”一詞既表示“正義”“公正”,也有“法律制裁”“法官”之意。西方法學(xué)認(rèn)為法就是正義的代表,正義是衡量是否符合法的目的的準(zhǔn)則[17],從這一角度看,法律的制定工作是與社會(huì)正義有最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工作。在我國(guó),人大代表作為國(guó)家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的組成人員,體察民情、反映民意,討論和決定國(guó)家重大事項(xiàng),監(jiān)督并推動(dòng)法律法規(guī)、決定決議的有效實(shí)施,他們的工作是對(duì)社會(huì)公平公正的切實(shí)推動(dòng),反映不公、呼吁平等是他們的責(zé)任。而檔案工作的核心職責(zé)是管理檔案,如歷史記錄的保管者、社會(huì)記憶的建構(gòu)者等角色和責(zé)任都是圍繞“檔案”這個(gè)工作對(duì)象產(chǎn)生的。從檔案的收集、整理到檔案的保管、鑒定再到檔案的編研、利用,檔案管理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都有既定的工作規(guī)范,做好這些工作是對(duì)檔案工作者的最基礎(chǔ)要求,也是檔案工作者最基本的責(zé)任。
誠(chéng)然,如馬克思所說(shuō),人應(yīng)該追求全面發(fā)展,但這種全面發(fā)展不應(yīng)該影響到其本職工作的開展。也就是說(shuō),正義可以作為檔案職業(yè)倫理道德的一項(xiàng)要求,但不應(yīng)該以檔案工作者本職的弱化為代價(jià)。檔案職業(yè)所做的更多的是一種幕后工作,而對(duì)社會(huì)正義的維護(hù)常要求走到臺(tái)前,正面沖突與爭(zhēng)端,這需要參與者投入大量的時(shí)間和精力,承擔(dān)管理國(guó)家檔案資源工作的檔案工作者既沒(méi)有維護(hù)正義的職責(zé)也沒(méi)有足夠的時(shí)間和精力去擔(dān)當(dāng)這項(xiàng)工作。
從個(gè)人層面看,普通檔案工作者缺乏維護(hù)社會(huì)正義的能力。
回顧上文所舉的挪威“戰(zhàn)爭(zhēng)兒童”、東帝汶人權(quán)斗爭(zhēng)的案例,再加上美國(guó)黑人民權(quán)運(yùn)動(dòng)、婦女解放運(yùn)動(dòng)等著名運(yùn)動(dòng),不難發(fā)現(xiàn)反抗不公正對(duì)待、追求公平正義通常是受迫害群體中的組織或個(gè)人、歷史學(xué)家、社會(huì)學(xué)家或?qū)@一群體有特別關(guān)注的人。二戰(zhàn)時(shí)期華沙猶太人居住區(qū)發(fā)起了一個(gè)秘密文檔項(xiàng)目,其領(lǐng)導(dǎo)人是一位歷史學(xué)家,他帶領(lǐng)收集并歸檔了包括科研人員、作家、教師、公共部門工作者以及無(wú)數(shù)普通猶太人在內(nèi)的眾多猶太居民記錄,為后世了解當(dāng)時(shí)猶太居民的艱辛生活提供了資料[18]。南亞裔美國(guó)人數(shù)字檔案館(South Asian American Digital Archive,SAADA)的兩位創(chuàng)始人中,Michelle Caswell是一名優(yōu)秀的檔案學(xué)者,她是美國(guó)加利福尼亞大學(xué)洛杉磯分校信息學(xué)院檔案學(xué)專業(yè)的助理教授,擁有威斯康辛大學(xué)麥迪遜分校的圖書與情報(bào)科學(xué)博士學(xué)位,在多本檔案學(xué)核心期刊上發(fā)表過(guò)文章[19],另一位創(chuàng)始人Samip Mallick擁有美國(guó)密歇根大學(xué)工程學(xué)院計(jì)算機(jī)科學(xué)學(xué)士學(xué)位、美國(guó)伊利諾斯大學(xué)圖書與情報(bào)科學(xué)碩士學(xué)位,曾是芝加哥大學(xué)圖書館南亞收藏的助理書目員,也曾為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委員會(huì)(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南亞和國(guó)際移民項(xiàng)目(South Asia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rograms)工作[20]。
我們能否期待或要求所有的檔案工作者都具備與這些人相當(dāng)?shù)膶W(xué)識(shí)與素養(yǎng)呢?筆者認(rèn)為這是不現(xiàn)實(shí)的。哈里斯提出檔案工作者應(yīng)該成為支持或反對(duì)社會(huì)壓迫的記憶活動(dòng)家,他認(rèn)為檔案工作應(yīng)擺脫政治權(quán)力的束縛以維護(hù)正義[21]。筆者認(rèn)為,檔案的確為社會(huì)正義維護(hù)者和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來(lái)源,但這并不意味著檔案工作者一定要成為社會(huì)正義維護(hù)者或研究者中的一員,要求檔案工作者成為政治參與者或行動(dòng)主義者(activism)而不只是利用者獲取憑證資料的提供者實(shí)有難度。
3 檔案正義尚不能成為檔案事業(yè)的發(fā)展方向
3.1 檔案正義理論依據(jù)尚不可靠。以哈里斯為代表的一些學(xué)者將檔案正義與雅克·德里達(dá)的后現(xiàn)代思想結(jié)合起來(lái),試圖從德里達(dá)的解構(gòu)主義中尋找檔案正義的理論依據(jù)。但美國(guó)檔案學(xué)者理查德·馬修(Richard J. Matthews)指出,后現(xiàn)代檔案理論將德里達(dá)的“檔案熱”(archive fever)闡釋為“公權(quán)力”(archontic power)理論是對(duì)德里達(dá)“檔案熱”的誤讀,這種對(duì)解構(gòu)主義的誤解將檔案工作者錯(cuò)誤地引向了對(duì)正義的呼喚。馬修進(jìn)一步指出,應(yīng)當(dāng)認(rèn)識(shí)到正義是不可判定的,“檔案熱”與權(quán)力和非正義無(wú)關(guān),而是德里達(dá)通過(guò)對(duì)檔案本質(zhì)的研究來(lái)解釋弗洛伊德“死本能”(death drive)理論化的問(wèn)題[22]。
筆者認(rèn)為,“正義”與“非正義”相對(duì),是一個(gè)有限定范圍的詞匯。追求正義這一行為本身是一個(gè)封閉性建構(gòu)的過(guò)程,它將“正義”當(dāng)作為人行事的標(biāo)準(zhǔn),把事物圈定在“正義”的框架之內(nèi),以社會(huì)正義為指導(dǎo)原則的檔案工作是在“正義”的準(zhǔn)則下去建構(gòu)檔案體系、結(jié)構(gòu)化檔案事業(yè)。檔案正義將檔案、檔案工作和檔案事業(yè)都圈定在“正義”的柵欄內(nèi),這與解構(gòu)主義的基本思想是相悖的,從解構(gòu)主義中尋找檔案正義的理論依據(jù)只會(huì)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德里達(dá)對(duì)南非反種族隔離運(yùn)動(dòng)等政治斗爭(zhēng)的投入和支持,其出發(fā)點(diǎn)在于對(duì)“結(jié)構(gòu)”的批判,而不是出于對(duì)社會(huì)正義的維護(hù)。哈里斯等人只看到德里達(dá)對(duì)政治事件的參與,沒(méi)有深究其行動(dòng)的初衷,就將德里達(dá)的思想觀點(diǎn)套用于“檔案與社會(huì)正義”并試圖用以指導(dǎo)檔案工作實(shí)踐,這種做法是不妥當(dāng)?shù)摹?/p>
3.2 檔案正義驅(qū)動(dòng)力不足。筆者認(rèn)為,哈里斯對(duì)檔案正義的提倡是因?yàn)槠渌鶑氖碌臋n案事業(yè)處于特殊地區(qū)的特殊時(shí)期之下,而在矛盾沖突復(fù)雜多樣、正義取向并不明確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中,檔案還能否在正義的維護(hù)中發(fā)揮如此顯著的作用、取得世人矚目的功績(jī),是存疑的。哈里斯在《終結(jié)階段的檔案?jìng)惱恚貉趴恕さ吕镞_(dá)遇見納爾遜·曼德拉》一文中承認(rèn),在南非取消種族隔離制度、實(shí)現(xiàn)政治轉(zhuǎn)型的今天,檔案正義的力量正在消散,正義已經(jīng)不再是南非檔案事業(yè)的驅(qū)動(dòng)力,取而代之的是緩慢而無(wú)聊的社會(huì)“正常化”進(jìn)程,檔案部門不再是變革的工具,南非檔案工作者中也少有人成為他所說(shuō)的“支持或反對(duì)壓迫的記憶活動(dòng)家”[23]。必須看到,他所謂的“緩慢而無(wú)聊的社會(huì)‘正常化進(jìn)程”正是任何一個(gè)處于平穩(wěn)發(fā)展環(huán)境下的社會(huì)的常態(tài)。
放眼世界范圍,盡管如種族歧視這樣的不公正問(wèn)題是存在的,但一個(gè)社會(huì)的沖突與矛盾是多樣的,這種多樣同時(shí)意味著分散和弱化,因此,將檔案正義從個(gè)體實(shí)踐升華為檔案事業(yè)的整體目標(biāo)是不合適的。檔案正義只能作為檔案事業(yè)的一個(gè)宣傳方向,通過(guò)對(duì)檔案工作支持世界各地邊緣化群體或受壓迫群體反抗不公、追求平等的案例的宣傳,讓人們看到檔案的價(jià)值,使人們認(rèn)識(shí)到檔案身為真實(shí)記錄的意義:檔案是非正義事件發(fā)生過(guò)的證據(jù),是少數(shù)群體尋求身份認(rèn)同的依據(jù),并借以提高檔案事業(yè)的社會(huì)地位。但,社會(huì)正義無(wú)法成為整個(gè)檔案事業(yè)發(fā)展的驅(qū)動(dòng)力。
檔案正義似乎為檔案事業(yè)指出了一條積極向上的光明道路,但深入思考后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理論存在許多漏洞與缺陷,在這些問(wèn)題尚未探討清楚之時(shí),檔案正義不宜被過(guò)多提倡。
參考文獻(xiàn):
[1]Harris V. The archival sliver: Power, memory, and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J]. Archival Science, 2002, 2(1):63~86.
[2]Jimerson R C. Archives for All: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J]. American Archivist, 2007, 70(2):252~281.
[3]付苑. 檔案與社會(huì)正義:國(guó)外檔案?jìng)惱硌芯康男逻M(jìn)展[J]. 檔案學(xué)通訊, 2014(4):4~9.
[4]羅亞利. 社會(huì)公平視閾下國(guó)外檔案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研究概述及啟示[J]. 檔案與建設(shè), 2014(9):4~7.
[5]丁先存. 試論檔案正義[J]. 皖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 2007, 23(6):29~31.
[6]Greene M. A Critique of Social Justice as an Archival Imperative: What Is It We're Doing That's All That Important?[J]. American Archivist, 2013, 76(2):302~334.
[7][22]Matthews R J. Is the archivist a “radical atheist” now? Deconstruction, its new wave, and archival activism[J]. Archival Science, 2016(3):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