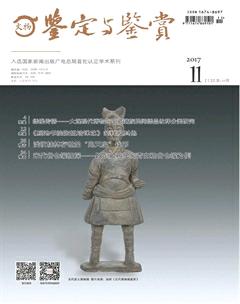淺析《后漢書》和《通典》有關羌的若干異同問題
徐晨峰
【摘 要】羌族是我國眾多民族中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自古到今,羌族人民不僅創造出自己獨特的、絢麗的文化,并且和其他民族相互融合,共同發展,為我們偉大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貢獻。《后漢書》和《通典》不僅對羌族尤其是西羌的歷史變遷、社會組織、生活習俗和漢代時漢羌關系作詳實記載,留下寶貴的資料;還以一個歷史學家獨特的眼光看漢羌關系,對后人有所啟迪。本文就兩書有關羌的若干問題進行校對分析,希望從中得到一些學術思考和研究。
【關鍵詞】羌族 歷史變遷 漢羌關系
一、兩書有關析支和賜支的用語
《后漢書》載:“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跡,穆公霸有西戎,公今欲復之。兵臨渭首,滅狄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后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牦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并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1]
《通典》載:“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跡。穆公霸有西戎,今欲復。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眾種人附落而南,出析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諸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后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牛種,越嶲羌是也;今越嶲地。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今梓橦、遂寧以西,德陽郡地。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今武都郡。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研豪健,故羌中號其后為研種。”[2]
析支是古代西戎族名之一,又稱鮮支、賜支、河曲羌,“后世便把它的所在擺在今青海積石山一帶,而《中國歷史地圖集》更把賜支河曲定在今共和縣曲溝地區”[3]。《書·禹貢》云:“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孔穎達疏引王肅曰:“析支在河關西。”[4]《史記·五帝本紀》:“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5]南朝梁王僧孺《答江琰書》有云:“豈復能使一笥可輕,八廚斯引,且登清漢,乍棄黃污,望影析支,爭涂再楫!”
據記載,析支大致在今青海東南境河曲之地,古西戎國名,亦作賜支。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于析支之一地,是為河曲羌。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余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后漢書曰,羌地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賜運載得,禹貢所謂析支者也。胡渭曰,漢人謂積石為河首,北音讀析如賜,故云,其地后為黨項所居。通典云,黨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北連吐谷渾也。
可見,析支和賜支是指代同一個事物,但是杜佑的《通典》用的是析支,范曄的《后漢書》用的是賜支。這其中的原因,筆者認為可能和時代背景有關。唐代和東漢在歷史的沿襲中,漢文書寫和語言表達也有發展變化,各有側重。所以,杜佑的《通典》用了析支,雖然不同于《后漢書》中的賜支,也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進一步看,這雖然是一個小問題,但從中可以得出杜佑在引用《后漢書》時,在很多地方會受唐代的歷史大背景的影響,小的地方如漢文書寫、山川河流等表達,深層次可能會從唐代當時的社會發展需要,對《后漢書》等引用材料進行選擇性引用和解讀。
二、兩書有關兵不西行和兵務東向的記載
《后漢書》載:“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后為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筑長城以界之,眾羌不復南度。”[6]
《通典》載:“秦始皇時,兵務東向,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筑長城以界之。”[7]
《后漢書》中的“兵不西行”和《通典》中的“兵務東向”,表面看著表達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杜佑為何要與《后漢書》用不同的表達呢?筆者通過閱讀分析,《后漢書》的側重點是秦始皇的出發點是滅六國,著眼點是關東地區。《通典》在引用時,特意用“兵務東向”,結合當時唐代的內外環境,杜佑側重的或許是為了向統治者進言,要重視內部,務外先務內。因為安史之亂后,唐王朝內部的藩鎮割據和農民起義才是政權的最大威脅者。所以,杜佑的此番心意是讓唐朝統治者重視內部問題,而不要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四處向周邊地區用兵。杜佑的階級立場應該是對他編撰《通典》的用意走向的根本所在,畢竟《通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
三、兩書有關羌亂的原因和治理措施
《后漢書》載:“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眾羌遂還據為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眾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發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舊。及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后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傳》。”[8]
《通典》載:“至王莽末,豪滇良內侵,燒當玄孫。及后漢初,遂寇金城、隴西。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郡,時涼州部,除三輔外,今安定、平涼郡之西,天水、隴西諸郡悉屬焉。皆有降羌,披發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請依舊制,益州部今漢川、巴蜀川,即當時益州是。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今范陽、上谷、安邊及漁陽、北平,即當時幽州。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部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9]endprint
無論是《通典》還是《后漢書》,都給出了羌亂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吏治腐敗,加上政策的不合理。所以,羌亂基本上在東漢一朝一直持續著。另外,治理羌亂用人不當,加上沒有完善的治理體系,所以耗費巨大,成效甚微。
筆者認為,杜佑對這個問題很是重視。《通典》中有很多關于羌亂和治理的論斷,“中心思想是要求做到‘生之者眾,食之者寡,減少冗官,定定民生”[10]。杜佑以此用來借古喻今,用東漢羌亂的治理得失告誡唐朝統治者,對待周邊民族關系和治理國內動亂隱患,要重視吏治,整頓吏治。從中不難看出,杜佑所在的唐朝時期,吏治腐敗已經到了很嚴重的程度,杜佑為了針砭時局,這也是他編撰《通典》的原因所在。
四、結語
以河湟地區為中心的諸羌,在東漢時期對漢羌關系的影響變遷,對中華民族的民族融合,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起了較大影響。兩書對此既有相同,也有不同,這和作者的出發點不同息息相關。不管怎樣,這兩部書都是研究羌的重要材料,都是優秀的文明成果。當然,由于時代和階級的不同,范曄和杜佑有他們的時代局限性。但是他們的著作仍然給后世研究羌史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在史觀上對后人也有很大啟發。
參考文獻:
[1](劉宋)范曄.后漢書·卷八七·西羌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2875-2876.
[2](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九·邊防五[M].北京:中華書局,1988:5130.
[3]李文實.《禹貢》織皮昆侖析支渠搜及三危地理考實[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1):167.
[4](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西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6](劉宋)范曄.后漢書·卷八七·西羌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2876.
[7](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九·邊防五[M].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5130.
[8](劉宋)范曄.后漢書·卷八七·西羌傳[M].北京:中華書局點較本,1965:2878-2879.
[9](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九·邊防五[M].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5131.
[10]陶(矛心)炳.杜佑和《通典》[J].史學史資料,1980(3):1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