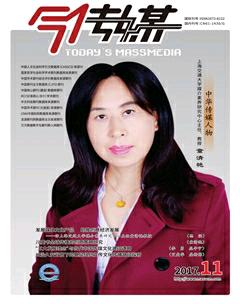新媒體視域下紀錄片的敘事策略分析
鄧高鋒
摘 要:“網紅”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央視首播,反響一般,隨后又在以青年娛樂為主的B站(bilibili,著名彈幕視頻網站)登錄,卻意外的躥紅,成為2016年現象級的文化熱點。作為現象級紀錄片在新媒體平臺意外走紅,值得每一個紀錄片學者深思,這次“意外”走紅又給紀錄片發展帶來哪些啟示呢?本文結合新媒體紀錄片的時代特征去分析紀錄片創作,并且嘗試從紀錄片敘事的角度分析其主題、結構等,從中總結紀錄片創作中的新方法論。
關鍵詞:故事化敘事;新媒體;“互聯網+”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7)11-0118-02
紀錄片在很長一段時間被看作“精英拍給精英看”的一門寫實電影藝術,這源于紀錄片創作的藝術性,而紀錄片的生產屬性決定著既要保持藝術創作特性,同時也要有足夠的商業屬性,以客觀世界為創作載體的紀錄片,天然缺乏著“俄狄浦斯情節”式的受眾吸引,因此很難大眾化,在生存發展方面略顯尷尬。與其他影視藝術門類相比,紀錄片的敘事戲劇性顯得比較羸弱,一直以來,在紀錄片創作的方法論上亟待破壁和重塑更新,為紀錄片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我在故宮修文物》意外走紅于網絡大眾,無疑具有很強的研究價值,影片是一部紀錄故宮書畫、青銅器、宮廷鐘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寶鑲嵌、宮廷織繡等領域的文物修復過程和修復者的生活的紀錄片,該片按修復門類分為3集,分別是青銅器、鐘表和陶瓷組,木器、漆器和織繡組,書畫修復、臨摹和摹印組。該片在知名彈幕視頻B站登錄播出后,在90后、00后中意外的迅速躥紅,短短幾天內播放量突破百萬次,一向評分嚴苛的豆瓣給出評分高達9.4分,超過另一現象級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有數據顯示,在微博上引起超過747萬次話題閱讀,成為年度最具影響力的紀錄片之一。
以故宮為題材的紀錄片并不少見,《故宮》《當盧浮宮遇見紫禁城》《故宮100》等,無論從制作團隊、后期特效,還是文本、構圖、解說詞都是力求精益,在制作成本上要遠遠高于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卻在話題度和影響力上都遠不及后者,那么到底是哪些特質屬性,使得《我在故宮修文物》大受B站青睞,成為現象級紀錄片作品?
最顯而易見的答案是:播放平臺不同,傳播渠道不一樣,導致了傳播力度和用戶討論度上的差異。央視是傳統電視媒體的“扛旗者”,在播出時間上有著非常嚴格的控制,《我在故宮修文物》在播出之前沒有做過多的宣傳,播出后很顯然沒有達到預期反映和關注度;bilibili是新媒體網站視頻中的代表,中國大陸一個ACGN相關的彈幕視頻分享網站,也被稱為嗶哩嗶哩、B站,網站最大的特點是懸浮于視頻上方的實時評論功能,進行雙向互動,用戶很輕松就可以完成在線討論,擁有很強的互聯網交互特性,廣受青年用戶的青睞,是當下國內最大的年輕人潮流文化娛樂社區。在B站誕生出大量網絡流行語,充分體現當今90后、00后的審美觀念和趣味。《我在故宮修文物》在B站意外走紅,雖不意味著新媒體比傳統媒體強大或者優越,卻從側面提供了一條新型的“紀錄片+新媒體”的傳播之路,為紀錄片更好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如果說《我在故宮修文物》運氣好,在傳統媒體上“有心栽花”沒能“成功”,卻“無心”試水新媒體的時候意外“柳成蔭”,那一定是某些特質符合類似于B站新媒體的傳播特性,使得其二次爆發,那影片究竟有哪些特點迎合了新媒體的特性?
紀錄片創作過程中,如何講好故事往往成為紀錄片成功與否的創作核心,紀錄片創作中最主要的創作矛盾在于敘事,主題是紀錄片創作的靈魂,敘事則是一部紀錄片成功與否的關鍵。在紀錄片題材同質化越來越嚴重的當下,深挖主題、精巧敘事顯得尤為重要,借鑒《我在故宮修文物》以大國小匠為主題的成功突圍,在新媒體語境下紀錄片創作上,有以下幾個方面可供借鑒:一是在敘事主題力求構建“我”的共性原則;其次在敘事視角上反差大,敘事結構切口小;三是紀錄片敘事大眾化,走心即受眾引力。
一、主題視角:第一人設“我”的身份重合
《我在故宮修文物》是一部關于故宮文物修復者的紀錄片,強調的主角是“我”,而“我”就是指故宮文物修復者,本來與觀眾沒有什么關系,卻因為第一人稱視角,將“我”和屏幕前面的受眾“我”聯系在一起,這種第一人稱暗示和提醒,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受眾與“國之巨匠”的距離,很多受眾在觀看時會有設定的虛擬身份,從而達到心理的某種共存。
這種零距離的第一人稱視角恰如其分的給了新媒體強烈互動的氧氣,符合新媒體互動社交的特性,受眾在達到身份認同的時候,會觸發行動和給予反饋,尋求集體的共鳴,從而獲得一種存在感和儀式感。
在B站觀看《我在故宮修文物》的時候,每當出現新人物上場的時候,彈幕出現類似“我就是男神王五勝”“我的女神紀東歌”、“我想和她在故宮騎自行車”等刷屏,當看到青銅器修復大師王有亮騎車出故宮抽煙的時候會有“前方高能預警”“我服”“碉堡了”等彈幕頻繁彈出,這幾乎成為一種用戶相互間約定俗稱的彈幕禮儀,而這大大增強了用戶的儀式感和參與感。
二、敘事視角:切口小、反差大
《我在故宮修文物》以文物修復者的日常生活作為敘事切口,擁有強大話題性的“故宮”甘當“綠葉”,成為紀錄片敘事的背景,這是一個很小的卻又很巧的切口設計,影片中有一句解說詞“這與我們想象中的氣氛肅穆、戰戰兢兢面對文物不同。修復國之瑰寶的現場,其實大多數就是這樣輕描淡寫,顯得很日常化。”這句話奠定了敘事的基調,不會采用太過莊嚴的語言和嚴謹的文本去敘事,那么如此平淡的展示日常生活的紀錄片為何能夠引起廣大網友的關注和討論呢?在敘事視角上雖然采用了大眾化敘事視角,卻在片子的整體上形成了眾多的反差,這種反差恰好迎合了樂于解構一切的青年文化口味。
1.現代解構傳統——格物與趣味共鳴
《我在故宮修文物》紀錄片中,主體是修復者,客體是故宮文物,修復者是現代人,文物是有著時間意義的歷史物品,這里面就涉及到了兩個方面的反差,一是修復者本身對傳統的認知,在影片中最為明顯的一段就是“王五勝修復唐三彩的馬尾”,由修復師的自身講述來析疑解惑。木器組屈峰作為年輕一輩的修復師,對修復工作有獨特的認知,他提出用用中國古代“格物致知”的精神來要求自己,同時用修復師的品格修養去賦予器件不一樣的解讀[1]。這本身就是現代人對傳統的一種解讀。二是發生在另外一個地方的解構如火如荼,充滿了90、00后解構一切的文化味道,比如“修復馬尾”這段,會有很多彈幕彈出如“用我的馬尾好了!”“唐三彩的馬尾是朝著地的!”“大師的想法果然不一樣”等,既是一種參與,同時也是一種趣味上的共鳴。endprint
2.年輕人的快餐文化——修復者的慢生活
影片采用了參與式拍攝手法,絕大部分采用固定鏡頭,很少使用運動鏡頭,最大程度的展示了故宮文物修復者的“慢”,但編導有意無意的在鏡頭中點綴了有趣的快節奏生活的鏡頭,比如王津師徒參加鐘表展覽,編導特意快速切換鏡頭去表現故宮之外的城市快節奏生活,諸如此類的鏡頭雖然不多,但總能看出編導的敘事意圖,極力在構建一種反差,恰如其分的表達了修復者們“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大師氣韻。
這種大師的慢生活姿態,放在以年輕人快節奏文化為主的新媒體上,又會形成另外一種奇妙的反差,很多年輕人會用很多詞匯通過彈幕去表達那種慢的向往,譬如“我要去故宮應聘”“在故宮騎自行車是怎樣的一個體驗”“我要當青銅器修復師”“我也想在故宮打杏子”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影片的話題討論度。
3.國寶級修復大師——生活上的普通人
一般以故宮為題材的紀錄片,絕大多數會被拍成文獻類紀錄片,可以試想一下:屈峰、王五勝等正襟危坐,莊嚴肅穆的鏡頭、字斟句酌加工后的文本解說詞、情景再現式的特效合成,如果是這樣,絕對不會有B站彈幕彈出的“我要嫁給王友亮”,只會形成“修復大師是敬而遠之、高高在上的國匠”身份。影片成功之處是將國寶級修復大師和生活中的普通人兩種身份巧妙的融合起來,且毫無突兀感和距離感。觀眾看到的是“隔壁鄰居、街頭菜場”的普通人的生活,“國寶級修復大師也會像普通人一樣騎自行車、抽煙”等,這種人設上的反差融合,使影片本身顯得沒有那么嚴肅呆板,從而拉近與用戶的距離,修復師們以雙重身份給觀眾帶來立體的觀賞體驗,同時豐富的記錄內容也極大滿足了觀眾的求知心理和獵奇心理。
三、“小故事”板塊化敘事:走心即受眾引力
縱觀近些年在熒屏上有影響力的紀錄片,其中影響力最大的非《舌尖上的中國》莫屬,一部美食類的紀錄片竟然被拍的如此“有滋有味”,其中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采用了故事化敘事。故事化敘事運用到紀錄片中早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BBC紀錄片將這種故事化敘事運用到了極致——8分鐘一個小故事,這在《舌尖上的中國》運用的爐火純青,《我在故宮修文物》也采用相同的敘事方法——板塊化故事敘事。
《我在故宮修文物》依托的是板塊式敘事結構,它打破了傳統敘事方式中的時間順序,輔以時間的回溯、跳躍、穿插等表現形式,“按照人物、時間、地域或主題的不同,將不同的內容分成不同的部分的一種結構形式”[2]。影片將修復者按不同工種分為不同的板塊,每個工種具體工作不同,但工種內部基本上講述的是師傅帶徒弟的中國傳統傳承關系,師傅與徒弟在每個工種上面的表現卻各有不同,這些不同都是通過小故事體現出來的,影片中出現了大量的小故事,比如王友亮喂食宮廷御貓,集體打杏子,王津參加鐘表博覽會偶遇收藏家,屈峰參加同學會,張紀歌泰合廣場騎自行車等,這些小故事的時間幾乎是新媒體平臺播出時候的彈幕最集中的時候,也是觀眾最為感興趣的地方,充分體現了小故事對受眾的吸引力,當頗有人情味的小故事一個個娓娓道來的時候,讓國寶修復大師獨特的人物形象活靈活現,也給觀眾帶來更多的人文思考。故事化敘事是現在紀錄片創作中的重要方法,結合新媒體平臺交互式特征,小故事化敘事更加走心,更加具有人文力量,能夠調動起受眾觀影和互動興趣,也更符合新媒體的大眾化傳播需求。
《我在故宮修文物》以“講好故事”代替傳統說教,“擇一事,終一生”是修復者們的國匠精神,以故事化的方式呈現給觀眾,就像一棱多棱鏡,角度不一樣,所看到的也不一樣。從紀錄片創作的角度來看,影片結合時代特征成功突圍頗具研究價值,給予紀錄片創作上新的啟發,紀錄片如何更好的結合“互聯網+”是每一個紀錄片創作者的課題。總之,本文嘗試提供一些帶有新媒體特征的紀錄片創作上的思考,供鑒之。
參考文獻:
[1] 豆露露.論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的敘事策略[J].現代視聽,2016(9).
[2] 劉璟.淺談紀錄片的結構藝術[J].青年記者,2009(23).
[3] 陳力丹.互聯網傳播中的長尾理論與小眾傳播[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3(4).
[責任編輯:東方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