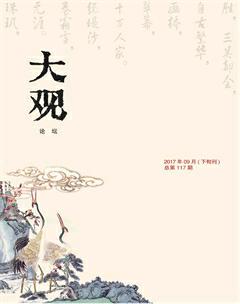淺談藝術的審美本質
摘要:審美的問題是貫通在整個藝術理論中的核心部分,藝術的認識即審美的認識,藝術的發現即審美的創造,藝術的欣賞即審美的鑒賞,可以這么說,審美是藝術鑒識于其他社會事物的根本性質。本文通過對藝術家的創作分析,來探討審美本質在藝術領域中的體現。
關鍵詞:審美;藝術家;創造;本質
我們大部分人看一幅繪畫作品更多傾向于以喜歡或不喜歡這樣的主觀判斷來定義作品好壞,在未進入大學之前的我們是一名參加高考的藝考生,主要瀏覽的繪畫作品雖然不是那么廣泛,或者是關于這方面的活動也是僅限于一些美院舉辦的高考高分卷年展和畫室的一些資深老師的作品展,但是對一些名作還是有所涉獵的。之所以用“瀏覽”這個詞,是因為我認為,只是用眼睛粗略地看一些繪畫作品,而不是在了解該作品的背景和畫家的生平的情況下,對作品的大致閱讀,而大部分情況下我們就是這樣的,在書店里沒有目的地對名畫冊作品集隨意翻看,也許撇撇嘴放下或著長時間進行愉悅視覺的簡單欣賞,這是那時候我們的狀態,那時候的我們更多是學習高考的應考作品。更有一些人會自我定義這些名作品的派別,如寫實派、野獸派等,那些名畫家對這些定義可能不會喜歡,也難以被大眾所承認。但是這些所謂的派別是無關緊要的,因為我們不是學者,不會去寫十萬字的書來闡述這些,只是在自己的生活圈里自娛自樂,影響的只是自己或身邊的一兩個人。但這些是會時常改變的,自己在某個階段也可能因為看了一些書或受身邊一些人的影響而改變。比如畢加索作于20世紀30年代的油畫作品《格爾尼卡》,記得初中時在課本里看到這幅作品,當時的感覺是迷茫的,“這是什么意思?”的疑問一直在腦中盤旋,最后也不了了之。
對其具體的了解是在大學里的藝術課程,有了在課程上的針對性才有了對事物更深的了解。針對性的審美,不只是我們對畫面效果上的欣賞,更是對作品內在的感受,是視覺與思想結合的審美。
在一幅作品被一段文字描述時,你所看到的已不只是畫的外在,不只是畫面的線條、色塊、構圖等那么簡單,而是某一個人的思想,但是我們的思想又不能被那些文字所束縛。畢加索《格爾尼卡》的解讀是來自于它的背景和歷史,即使觀看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但它的確是來自于此。而在《情迷畢加索》的電影中對作家的演繹則更有溫度了。又比如名畫家杰克遜·波洛克,他是20世紀最值得一提的畫家之一,以在帆布上很隨性地潑濺顏色、灑出流線的技能而聞名,他的作品往往具備難以忘懷的自然品質。波洛克藝術所創造的奇特成就幾乎與他所使用的筆和畫布毫無聯系。他的繪畫已經完全替代了創作的本身,是一種類似表演藝術的創作形式。“繪畫行為的極端表現,他觸及到無意義,讓我們莫名其妙,他與創造孤獨癥擦肩碰臂。沒有預約的訂單,沒有規劃的文字,也從未考慮過針對某類市場或觀眾,手欲畫,遂成畫。行險之舉,可能什么也沒說,可能無人能懂,甚至包括他自己。一個本來很可能處在邊緣的舉動,無后代,不生育。一個完全有可能被看作是頑皮兒童的涂鴉,無辨認的涂鴉。然而,像一切創新一樣,它竟然也被人承襲,抄襲,膜拜。”假如這些作品沒有了名稱,如《薰衣草之霧》《北斗星的反射》《秋韻》這些作品名,那么我們在觀看這些作品時,沒有了作者的暗示,更多的是自我的帶領,是根據個人經歷,個人情感等去理解、去尋找自己與畫家繪畫表現的共鳴點,感受理解或被理解,隨后就是喜歡或者不喜歡的定義,當然這只是少數人。有一些人因為“看不懂”而不再停留,還有一些人對畫家生平背景了然于胸時,看到的就不只是作品的表面了。
如果這些還不夠的話,那我們可以看看藝術家的平生,就會發現通常都有一個部分是青年時期與成熟時期。藝術家留意的事物,就會事無巨細地研究,把事物放在眼前,他嘔心瀝血要表現的事物,忠實的程度讓人敬畏,這是真實情感爆發的時期。米開朗基羅的教堂壁畫,他做的許多解剖,畫的無數素描底稿,時常對自己作內心剖析,對悲壯的情緒和映射在肉體上的神情的鉆研,意圖是要表現出所酷愛的那股敢于爭斗的力量。他年輕時完成西克施廷教堂的天頂和每個屋角,那些活潑生動的表現,展現的自然,熱情豪放,絕對真實。回到我們自身,如果我們這個群體也算半個藝術家的話,至少有那么一點點關于藝術的東西在我們思想的長河里,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擁有一顆年輕熱情奔放的心?還記得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有興趣在白紙上用鉛筆寫寫畫畫,但現在的自己都很難再那么畫了,因為看事物已經沒有那么純粹,那小手握著鉛筆的感覺也已不再,現在雖然有了嫻熟的手法,但彼時驚喜是現在的平靜了,如果說這是長大,那也只能欣然接受,至少還有些許回味。
讓人驚喜的作品都是產生于無意間的,哪怕是一個不知世事的孩童的隨意揮灑都有可能是驚人之作,相比那些認為對事物足夠了解,缺乏發現新事物的潛在后勁,就剝離活生生的本相,依靠從生活體驗中收集來的秘訣進行創作的藝術家好的多。
晚年的米開朗基羅在保里納教堂的壁畫作品《圣·保祿的改宗》和《圣·彼得上的十字架》按照一定的程式進行作畫,連外行的我們都能看出來,他早期的生動創造,自然的表現,激情奔放在這里已經不見了,至少喪失了一部分,另一方面是他的技巧更多了,掌握了相當數量的形式;一方面是亂用成法,雖然還是超越過別人,但和他過去的造詣比擬已經大為失神。然而米開朗基羅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他的早期和晚期的對比不過是告訴我們不管是多么細微的改變在每個人的身上都是會有的,是潛移默化,是循序漸進的,是不為人的意志所改變的。
如果一件藝術作品已經面世,并被大部分人所接受,那作為另一個觀眾的你必須要看到它的兩面性,并試著去了解它被大部分人接受的那一面,如果做不到就放下。而一味地用個人色彩去抨擊,是無力的,因為你一個人的力量是不能讓它回到倉庫去被塵封的。這里的從眾也不見得是沒有個性的,你總能在里面找到屬于你一個人的色彩。經典是永恒的,審美是要敞開心扉的。
【參考文獻】
[1]王宏建.藝術概論[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
[2]彭吉象.藝術學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作者簡介:謝盼盼(1992-),女,漢族,河南省平頂山人,華南理工大學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綜合藝術與材料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