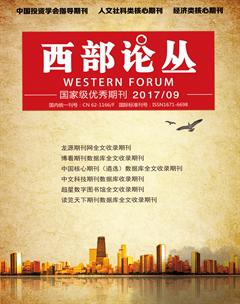繼承法上特留份制度的法律問題研究
劉夏安
摘 要:特留份制度作為繼承法上的一項制度,被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繼承法所采用,但我國繼承法上并無此項制度。我國《繼承法》第19條規定給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是必留份制度,與特留份制度存在差異,但很多時候在概念上常為人所混淆。本文從特留份的規范目的、歷史變遷等角度對特留份制度作了梳理,并認為其制度仍然具有制度意義和活力,因此我國在編纂《民法典》時應當構建特留份制度。
關鍵詞:特留份 必留份 歷史變遷 規范目的
一、特留份與必留份規范目的不同
特留份,是指遺囑人必須為特定的法定繼承人預留的,不能借用遺囑予以剝奪的份額。[1]特留份權是立法者在法定家庭繼承和遺囑自由之間作的一項妥協。被繼承人可以經死因處分剝奪法定繼承人的繼承權。但一般無法剝奪其特留份權,從而保障近親屬能在最低限度上分享遺產。關于特留份制度,僅從概念上難以看出其實質內涵,或者說,很難用一個準確的表述表達其完全周延的內涵。若僅從概念上看,似乎我國《繼承法》第19條規定的必留份制度也符合該概念的表述,必留份同樣是遺囑人必須為特定的法定繼承人預留的,不能借用遺囑予以剝奪的份額,甚至預留份制度也能統攝在這一概念下。
必留份制度在我國《繼承法》體系上雖然被安排在“遺囑繼承和遺贈”這一章,但其規范目的是為了使得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能夠獲得一定的遺產以維持生活需求,其與《繼承法》第14條酌情分得遺產權的規范目的有相似之處,都是對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人的一種照顧,只是前者適用的對象是繼承人,后者適用的對象是繼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繼承人扶養的人。舉輕以明重,連繼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繼承人扶養的人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都應當在繼承遺產時得到照顧,繼承人中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都應當在繼承遺產時更應當得到不低于前者的照顧,但考慮到第19條條文文義是針對遺囑作出的規范,在法定繼承中應當采用類推適用的方式,類推適用第19條。之所以得以類推適用的原因是因為必留份制度是對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的一種照顧,給予其必要的遺產份額不會因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的不同產生差別。而特留份制度則不然,特留份制度是建立在被繼承人有完全的自由處分自己的遺產和對遺囑的充分尊重的基礎上的,這一制度特點在各國含有特留份制度的繼承法中均有所體現,特留份制度和遺囑繼承制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如果被繼承人無法通過或沒有通過遺囑繼承的方式安排自己的遺產,則出于對被繼承人遺囑進行限制的特留份制度就失去了其制度價值和規范目的。
二、從對遺囑進行限制的角度看特留份制度的歷史變遷
(一)羅馬法上的義務份
有學者認為羅馬法中的“義務份”的起源是為了實現家庭中贍養老人和幼子的目的。從這個角度看,我國繼承法上的必留份制度更貼近于羅馬中的早期的“義務份”制度的規范目的,均有保障繼承人中缺乏勞動能力且沒有生活來源的老人和幼子的生活保障功能。羅馬法上的繼承制度以遺囑繼承為主,法定繼承為輔,到查士丁尼一世時,正式形成了“遺囑逆倫訴”,凡是不合情理的遺囑,遺囑人的近親可以向法院提起“遺囑逆倫訴”。可見隨著羅馬法中“義務份”制度的擴展,最初的有權利提起訴訟的人從被繼承人的直系卑血親或直系尊血親擴展到了兄弟姐妹等近親屬,此時“義務份”制度承擔的不僅僅是實現家庭中贍養老人和幼子的目的,它更多是因為遺囑違反了遺囑人對家庭和親屬的一種自然義務。因此應當看到,羅馬法上的“義務份”制度存在一個衍變的過程,它的規范目的也存在漂移,不是一開始就是“特留份”制度的起源,而是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有了與特留份制度相近的內涵。
(二)日耳曼法上的期待份和對羅馬法的繼受
在日耳曼法中,同樣有特留份制度的雛形。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日耳曼人沒有遺囑制度,只是在沒有親屬繼承的事后才能在生前指定他人為自己的繼承人。[2]在遺囑制度和“期待份”制度之前,日耳曼法有死者份制度,即死者生前所用的物品隨死者埋葬或焚燒。隨著天主教的影響,死者開始將其可以處分的財產捐助教會,因此死者分開始轉變為“供養分”,即有供養教會之意。但此時的供養分仍然限于教士之中,隨著這種方式的財產移轉方法為世俗法所承認,日耳曼法上的遺囑制度因而成形。[3]由此可見,日耳曼法上的遺囑制度從無到有,有其自生之土壤。在所有法律制度中,繼承法是最能體現民族特征的,因此作為繼承法中的遺囑制度,并非源自羅馬法,而與遺囑繼承制度相伴而生,作為對遺囑繼承制度進行限制的特留份制度,即便羅馬法上與日耳曼法上均有相似制度,也并非起源與更新的關系。
特留份制度在日耳曼法中最初出現,就表現出很強的對遺囑的自由處分進行限制的基因,即被繼承人只能將遺產中很小的一部分通過遺囑的方式自由處分,而大部分財產要受到特留份制度的制約,由法定繼承人繼承。與其說特留份制度是對自由處分遺產的遺囑制度的限定,不如說遺囑制度是對限定處分遺產的日耳曼法繼承制度的松綁。因為“團體主義”的日耳曼法中,一開始并沒有繼承制度,也沒有自由處分遺產的基因。爾后,隨著社會發展,遺囑制度漸起,對財產的自由處分權限增多。隨著文藝復興之后,羅馬法的興起和伴隨著日耳曼對羅馬法的繼受,意志自由的基因在法律制度中的增多,日耳曼法中合乎意思自由的遺囑制度和和對遺囑中的意思自由加以特留份制度也逐漸成型。可見相較于羅馬法,日耳曼法中的“期待份”制度最初最多只能算“特留份”制度的雛形,真正作為對遺囑自由進行限制的“特留份”制度尚未成形,直到繼受了羅馬法“私法自治”的核心后,特留份制度才逐漸發展為今天的樣子。
(三)德國和法國的特留份制度
1、德國民法中的特留份
德國法上,專以一章對特留份制度加以規范,包括特留份數額,解釋規則,特留份的補足、限制、計算等規則。其中在遺贈的給予及其與特留份之間的關系上,給予特留份權利人以充分的自由選擇請求特留份還是接受遺贈的受益。為了充分保障特留份權利人的權利,繼承人承擔有一定的法定義務,如確定義務、答復咨詢義務等,以平衡二者之間的關系。同時對特留份權利,被繼承人也可以在一定情況下對其進行限制。[4]
2、法國民法中的特留份
法國法上,對被繼承人的遺囑自由限定較嚴,不僅對遺囑自由進行限定,對被繼承人通過生前贈與方式處分其財產的自由也加以限制,且被譯成人可以自由的財產份額受到很大約束,被繼承人不可以處分的財產部分即為特留份。其特留份份額保留較德國法上為多。法國法上對繼承人的利益保護更為嚴格,可以通過生前贈與方式或遺囑贈與的方式處分財產的份額被嚴格限制,在被繼承人存有子女的情況下,可以自由處分的財產僅在一半甚至更少。
三、我國繼承法上的特留份制度建構
從前述特留份制度的規范目的和歷史變遷可以看到,我國《繼承法》上第19條確定的必留份制度并非特留份制度,其與特留份制度的規范目的有所不同,也并非源自特留份制度的歷史變遷,我國并無特留份制度,目下一些法條編纂中將該條列為特留份實為以訛傳訛。既然我國并無特留份制度,值此民法典編纂之時,是否應當在繼承編中移植特留份制度呢?就我國目前的《繼承法》而論,對遺囑自由的限制是非常少的,除了必留份制度、和預留份制度有所限制外,別無他限,且前述制度與特留份制度之規范目的有很大不同,由于遺囑自由帶來的一定倫理問題,法官審判時均只能借助于公序良俗原則裁判,使得遺囑歸于無效。但遺囑全然無效,同樣與被繼承人之意志相違背,借用公序良俗原則裁判,也有很多的不確定性,歐陸各國的特留份制度對解決上述繼承法領域的倫理問題,踐行優良的傳統道德倫理,有很大裨益。
從歐陸立法例來看,特留份制度的存在有其客觀作用,即保護家庭親屬利益。從羅馬法上的“義務份”到日耳曼法上的“期待份”直至今日德法的特留份制度,盡管制度形式、規范各有不同,但是其中內涵同一,即限制被繼承人的遺囑自由,保證被繼承人血親的繼承利益。所不同者,基于立法的出發點不同,對待遺囑自由的態度各不相同,大抵為兩種,一種是如羅馬法上那般,以遺囑繼承為主,法定繼承為輔,對遺囑自由持寬容態度,對其限制較少,對被繼承人的自由意愿尊重為先,以德國法為代表。一種是如日耳曼法上那般,遺囑繼承是對法定即成的松綁,對遺囑自由持審慎態度對其限制較多,對繼承人的利益保護為先,以法國法為代表。各國均各有民法典,特留份制度的具體規定或有不同,但其規范精神并沒有超過這兩者的藩籬。我國要繼受特留份制度,應該以哪種制度模式為范本呢?從現行繼承法的實踐來看,我國對遺囑即成自由度很高,民眾于習慣上也更愿意接受以德國法為代表的特留份制度,且我國民法學說也多以繼受德國法為主,故采德國法模式為好。
參考文獻
[1] 宋宗宇、姜紅利、王琳,《特留份制度及其在我國的法制構造》,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11期。
[2] 參見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說》,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14頁。
[3] 參見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說》,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221頁。
[4] 參見陳衛佐譯,《德國民法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年2015年版,第638-6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