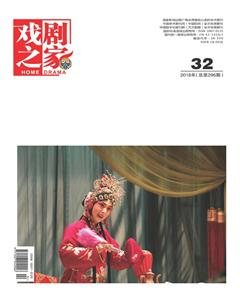千姿百態、絢麗多彩的藝術風格探微
谷一
【摘 要】藝術風格即是藝術作品所表現出來的獨特的個性、鮮明的藝術特色和較為穩定的藝術形態,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皆呈現出差異性的特點。
詩仙的豪放、易安的婉約,體現的是不同藝術家的風格;東方尚韻重神、西方注形求真,體現的是不同民族的風格;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體現不同欣賞者審美需求,并反作用于風格的形成。可見,只有在不同因素共同作用下才使得藝術形成千資百態的風格。
【關鍵詞】表現符號;藝術風格;審美意識;影視語言
中圖分類號:J60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1007-0125(2018)32-0129-02
一、“人心如面,各不相同”——藝術家的風格
藝術生產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藝術作品上必然留下藝術家個人的烙印。中國美學理念講究“文如其人”、“書如其人”和“畫如其人”。法國文藝理論家布封也曾言“風格即是人”,二者都是在闡述藝術家藝術風格的問題。
在文學領域內,我們能體會李白詩的瀟灑飄逸,杜甫詩的沉郁頓挫,也能感受到宋詞中豪放派蘇軾“大江東去浪淘盡”的恢弘氣勢,也感動于婉約派柳永的“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的哀婉凄清;在書法領域王羲之的行書平和自然、遒美健秀;張旭草書傾勢而下、流暢自如;柳公權楷書精嚴縝密、清勁峻拔。
在繪畫藝術中,同為五代時期花鳥畫的代表人物黃筌和徐熙,因風格差異而被稱為“黃徐體異”,黃畫富麗堂皇,盡顯皇家富貴;徐畫清淡雅致,描繪自然之真。北宋南北派山水畫家董源和巨然,風格也有著不同之處,董畫沉郁雄渾、氣勢宏大,盡顯北方山河的雄奇;巨然筆法細膩、形態逼真,寫盡江南風景秀美。
后印象主義的梵高和高更繪畫都喜歡用黃色,梵高用黃色為檸檬黃,顯得明朗,在其作品《向日葵》中,以青綠色為背景,與黃色向日葵相襯,用變化豐富的黃色,突出歡快的調子,寄托飽經人間苦難的畫家對生命的熱愛;高更喜歡用橙黃色,其代表作在《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中,整幅畫面色彩充滿原始的神秘情調,表現畫家本人極其苦悶的內心世界。
無論是馬遠在《踏歌圖》中所畫山之一角,還是夏圭在《溪山清遠圖》中所畫水之一涯;抑或人物畫的“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如此種種,都證明藝術家在藝術作品創作中,傾注了自己的藝術觀念、審美理想,而形成的與他人截然不同的藝術風格。
二、“因國而異,因時而變”——民族與時代的風格
在中外藝術史上,藝術受地理環境、社會狀況、文化傳統、時代背景等因素的制約,藝術風格常常呈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并且“因國而異,因時而變”。
以東方戲曲和西方戲劇為例,中國的戲曲常為大團圓式的結局,表現了樂觀積極求圓滿的民族心理,正如《牡丹亭》標目中寫道“但使相逢莫相負,牡丹亭上三生路”,主人公在三生三世,生死輪回,起起伏伏中,終究修成正果。昆曲《長生殿》中因女主人公逝去,愛情未能廝守,于是便創造“在天愿做比翼鳥,在地若為連理枝”美好幻境,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以浪漫主義色彩的手法,描寫了男女主人公因封建家庭的壓迫雙雙逝去后,卻又在墳前化成比翼雙飛的蝴蝶的唯美結局。同時中國戲曲懲惡揚善,善惡有報的價值觀十分顯著,如清傳奇劇《風箏誤》、《賽琵琶》等揭示一個“真理”,好人總會有好報,以德報怨、以德感人是中國戲曲常用的主題。
而西方戲劇則以激進式、毀滅式結局為特征,體現一種悲觀的民族心理。魯迅先生曾說“悲劇,就是將美好的東西撕毀”,西方戲劇將這一點體現得淋漓盡致。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普斯王》中俄狄普斯遭遇殘酷、悲慘的命運,一次次的想擺脫命運卻以失敗告終,讓人同情;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男女主人公難逃命運的桎梏,雙雙逝去以悲劇散場。雨果的浪漫主義戲劇《歐那尼》中,勇敢誠實的歐那尼、溫柔善良的素兒死于非命,使人噓唏不已。歐里彼得斯揭露兩性問題和家庭問題的戲劇《美狄亞》中,女主人公竟然以殺死自己親生孩子的方式,來報復另尋新歡的丈夫,如此的激進,極具毀滅性。由此可見不同的民族其藝術風格有天壤之別。
藝術風格除民族性以外,還具有時代性。隨著時代的更迭,藝術風格也因時而變。例如中國古代青銅器從總體上講都是具有造型生動、紋飾精細、裝飾華麗等特點,但如果仔細區分,就可以看出青銅器鮮明的時代特色。商周奴隸社會鼎盛時期,青銅器體積龐大,流行一種饕餮獸面紋及頭牛、虎頭等兇猛的野獸,令人恐懼,顯示出神秘的威力和猙獰的美,象征著奴隸主統治階級的秩序和威嚴。到了春秋戰國,奴隸制度的瓦解,青銅器轉為生活器具,造型從簡,并出現了采獵、種植等生活氣息濃郁的紋飾圖案。
三、“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欣賞者的審美風格
孔子曾言“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由于欣賞主體存在于不同社會層次、文化層次、年齡層次的群體中,因此其個體或群體有著多樣化的審美需求,同時多樣化的審美需求會催生更多藝術風格的誕生,二者互為聯動。
在音樂鑒賞中,有人喜歡貝多芬氣勢磅礴的《英雄交響曲》,有人喜歡勃拉姆斯安謐、恬靜的田園風格的《第二交響曲》;文人追求音樂“大音希聲”般的至高境界,“陽春白雪”的超凡脫俗,而使《漁舟唱晚》《梅花三弄》《陽關三疊》等文人歌曲歷久彌新;更多的人則偏愛直抒胸臆的山歌小曲,“下里巴人”通俗音樂的純真質樸,由此,“苗族飛歌” 、“ 信天游 ” 、“采茶歌”等民間音樂生生不息。
同時,不同人的審美偏好反作用于新藝術風格的形成。
現代流行文化綜藝、網絡劇、類型電影等等,幾乎每一種風格的都有自己固定的觀眾群體,都是在不同的藝術審美需求下形成和發展自己的風格,由此特色化、小眾化、專業化的節目得到大力提倡,促進了藝術風格的再創造。
四、結語
綜上所述,千姿百態的藝術形式,不僅包含藝術家的辛苦心血、嚴密構思,彰顯民族特色時代特征,反映大千世界的種種審美需求,更是體現出熠熠生輝的藝術風格。
參考文獻:
[1]晏俊.淺談藝術設計的風格及融合[D].鄂東職業技術學院,2010.
[2]趙煒.設計風格及融合性的藝術表現[D].美術大觀,2011.
[3]朱連生.中西繪畫藝術美學思想的幾點比較[D].鞍山師范學院學報,2004.
[4]曹成利.影視語言的詩性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11.
[5]蘇和平.色彩民族審美意識表現符號論[D].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