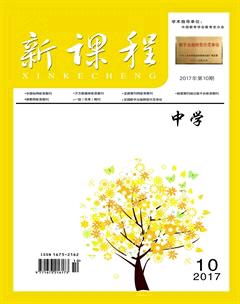又見表揚3+4=8
陳建方
“要相信學生……聰明指數絕對超過了我們小時候……給學生一個施展自己的平臺。例如:在學習《窗》這一課時,我讓學生設想一下,這個沒有看到他所希望看到的美景的病人,他會怎么樣呢?同學們紛紛去說。有的說,他懊悔至極,后來自殺了;有的說,他也舊病復發,痛苦而死;有的說,他在一次次的噩夢中死去了;還有的說他后來遇到了一個好的醫生來這個城市,于是很巧地治好了他的病,而他后來就用自己所有的錢,買下了對面的土地,把他建成了一個美麗的公園……學生的想象能力是超出老師的想象的。”
這是一位語文老師的教學隨想中的一段,乍一看,頗有道理;細一想,不禁啞然——這讓我想起了一個賞識教育的“范例”:一位小學的數學老師,因為學了賞識教育的理論,在上課時十分重視對學生的表揚,以致面對學生的作業“3+4=8”時也大加肯定:“不錯不錯,與正確答案只差1,你真聰明。”
姑且不論“聰明指數絕對超過了我們小時候”是否屬實,單是對學生答案的一味肯定,不就跟那位小學數學老師有著同樣的風范嗎?也許有人會說學生的答案不都有道理嗎?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分析。
第一種答案:他……自殺了。
如果稍微注意一點原文的第一自然段,我們就會發現問題之所在:
“兩人的病情不允許他們做任何事情借以消遣,既不能讀書閱報,也不能聽收音機、看電視……只有靜靜地躺著。”第一段中的這一句告訴我們,這兩位病人病情已極為嚴重的,甚至可以說,隨時可能死亡,所以才會有這一幕:“第二天早晨,醫護人員送來了漱洗水,發現那個病人早已咽氣了,他們靜悄悄地將尸體抬了出去,絲毫沒有大驚小怪。”如果病情不是這么嚴重,那靠窗病人的死亡將會讓他們感到震驚,而不會如此平靜地處理。這就告訴我們,這兩位病人中的任何一位都沒有可能自殺,因為此時此刻,他連自殺的能力都沒有,又何來自殺的一幕出現?縱然出現也只能是出現在毫無生活閱歷、閱讀又不夠仔細的初中生腦海里。
第二種:“他也舊病復發,痛苦而死。”
這一種結局不錯,但是“舊病復發”這個詞明顯有誤,因為他本來的病就嚴重得沒法治愈,隨時可能死亡,又何來“復發”一說?
第三種:“他在一次次的噩夢中死去了。”
這種說法,仍是表述存在誤區,因為人可以在一次次噩夢中醒來,卻無法在噩夢中死了一次又一次吧?或許可以改為:一次次的噩夢折磨著他,他終于在痛苦中一命嗚呼了。
第四種:“他后來……公園……”
這一條看似最容易駁倒,其實光從合理性而言是最難駁倒的。因為古代的名醫孫思邈可以把已經抬往墓地的棺材中的“死人”救活,如今醫學這么發達,醫生中的圣手也偶爾會出現,無法醫治的疑難雜癥,一個好的醫生確實也能迎刃而解,藥到病除。問題是,這個答案,可能在課堂上就會遭到同學的駁斥。為什么呢?
這就類似于有同學續寫《孔乙己》,說孔乙己最后一次到咸亨酒店喝完酒爬回去的途中遇到了一位富有的好心人,給他治好了斷腿,并資助他參加科舉考試,于是,孔乙己便像范進一樣在考場上春風得意,并當了高官。
這樣的想像是合理的,但只是一種用偶爾代替必然的合理。文學作品來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展示的應該是一種相對必然的、普遍的現象。所以,這位同學對《孔乙己》的續寫,是不成功的,他也違背了續寫(或想象)的原則——忠于原作的內容和主旨。原作的結局是:“我到現在終于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原作是以孔乙己這一人物形象控訴封建科舉制度的毒害,而這種續寫對科舉明顯是一種頌揚。
同樣《窗》一文中采取歐亨利式的結尾,甚至可以說比《孔乙己》的結尾留給了讀者更廣闊的補白空間。
作者的意圖是用一扇窗戶照出了兩個靈魂,表現出兩種截然相反的處世態度,揭示了人性的美與丑。
不靠窗的那位病人,雖然每天下午津津有味地聽病友們的故事,享受著美好時光,但他并不滿足,他還強烈地渴望占有那扇
窗戶。
這雖然也是熱愛生活的愿望使然,但其核心卻是自私的。
私心極度膨脹,最終導致采取見死不救的手段堂而皇之地取得靠窗的床位。
然而,生活偏偏不肯饒恕他,他費盡心機得到的只是光禿禿的一堵墻。
而此情此景恰恰發生在這樣一個情節之后:“他白晝無時不為這一想法所困擾,晚上,又徹夜難眠。結果,病情一天天加重了,醫生們對其病因不得而知。”
按作者的意圖,會讓這位不靠窗的病人逃脫死亡的劫難嗎?當然不會,因為文中的他是惡的化身,是撒旦!這第四種答案的錯誤此時此刻肯定是顯而易見的,這與《孔乙己》的那段續寫犯了同樣的錯誤。
對這四種答案的肯定,都不如那位小學數學老師對3+4=8的肯定,因為他的點評,至少讓學生明白自己的答案與正確答案相差了1。
所以,對學生答案的點評一定要恰如其分,而不能形而上學地解讀賞識教育,對學生一味地表揚,那樣就與教育教學的目的背道而馳了。
參考文獻:
[1]姚煒.《窗》的教學設計和教學感言[J].語文教學通訊,2006.
[2]牛海兵.賞識教育研究[D].魯東大學,2014.
編輯 李琴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