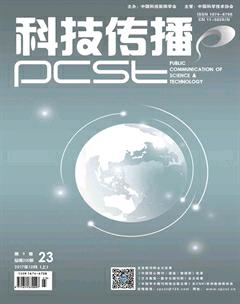“限娛令”的冷思考
史璐
摘 要 2012年廣電總局頒布“限娛令”,對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的娛樂節目進行規范和管理,以期改變電視節目過度娛樂化和低俗化的傾向。本文認為,“限娛令”政策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對電視市場實施人為的管控,會引發諸多負面因素。
關鍵詞 限娛令;收視率;娛樂節目;電視市場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7)200-0185-03
從2011年7月廣電總局召開“關于防止部分廣播電視節目過度娛樂化座談會”開始,針對電視節目過度娛樂化開始出臺相關政策,最終在10月下旬正式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節目管理的意見》,自2012年1月1日起對34個地方上星綜合頻道實施調控,被業內稱為“限娛令”。
“限娛令”包括以下5方面要點:1)明確地方上星綜合頻道的性質是以新聞宣傳為主,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2)節目比重調整。擴大新聞、經濟、文化、科教、少兒、紀錄片等多種類型節目播出比例;必須開辦思想道德建設欄目,以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壓縮娛樂節目(婚戀交友類、才藝競秀類、情感故事類、游戲競技類、綜藝娛樂類、訪談脫口秀、真人秀等類型節目)3)節目播出時間計劃調控。確保新聞類節目播出時間:6:00至24:00時段不得少于2小時,18:00-23:30時段必須有兩檔以上不少于30分鐘的自辦新聞類節目;娛樂節目播出總量控制:每晚19:30-22:00各上星綜合頻道播出娛樂節目總數不超過9檔,每個上星綜合頻道每周播出娛樂節目不超過2檔、時長不超過90分鐘。4)廢除收視率評價體系,建立科學客觀公正的節目綜合評價體系。實行“三不”原則,即不得搞節目收視率排名,不得單純以收視率搞末位淘汰制,不得單純以收視率排名衡量播出機構和電視節目的優劣。5)強化監督機制。要求實行“一把手責任制”、在省級廣播電視行政管理部門建立專門收聽收看機構、強化處罰等措施,確保上述政策實施。
應該說“限娛令”頒布的初衷是好的,對防止電視節目過度娛樂化和低俗化傾向,對主流價值觀和道德體系的建設將起到積極作用。但是也應該看到,“限娛令”的系列政策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甚至會產生一定負面因素。
1 對收視率評價應該全面審視
為了爭奪廣告收入,電視臺實施“唯收視率”管理模式,為爭奪收視率用“過度娛樂化”吸引眼球,最終導致節目低俗化。由此,廢除收視率評價體系,實行“三不”原則,要求考察節目的“滿意度”、考察對主流價值觀和道德宣傳的力度,成為“限娛令”試圖從制度上鏟除“過度娛樂”滋生土壤的重要舉措。但是我們應該冷靜地看到,“唯收視率”是錯誤的,放棄收視率評價同樣會產生負面效果,我們應該全面審視收視率的意義。
1)收視率是電視業存在的基礎。電視必須要有人看才能稱之為電視,一個大家都說好,但是都不看的電視臺還有多大的生存意義?收視率代表人民群眾和收視市場對電視節目的認同度,我國廣播電視事業30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表明,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創造群眾喜聞樂見的電視節目是廣播電視事業發展的基礎所在。
2)收視率和主流價值觀、主流道德體系不應該是對立的。弘揚“主旋律”的節目同樣需要收視率,只有創造喜聞樂見的形式吸引大眾觀看,才能彰顯其“主流”的地位。不能形成這樣的思維定式,高雅的主流的一定沒收視率。恰恰相反,電視工作者的使命就在于創造有效溝通的橋梁,在高雅主流的意識形態和人民大眾之間建立有機聯系。如果不顧收視率的話,節目制作極有可能出現不顧收視率的傾向,節目成為缺乏互動“自拉自唱”式的“陽春白雪”。
3)娛樂節目的高收視率并不可怕。對“唯收視率”的口誅筆伐,一些文化名人甚至說“收視率是萬惡之源”,大有把收視率“妖魔化”的趨勢。一些娛樂節目通過低俗手段博取收視率是當前的現實,但并不能反過來認為高收視率的一定是低俗的。在不違反法律法規、在弘揚主流價值觀和道德的前提下,娛樂節目是應該追求高收視率的。
4)科學發揮收視率在電視節目評價體系中的作用。基于對收視率的重新審視,未來電視節目評價體系的重構必須在“唯收視率”和“棄收視率”之間找到支點。筆者認為,比較現實的解決方案是對電視臺節目實施分類管理,例如把節目分為政治類、公益類和商業類,針對不同類別的節目合理應用收視率指標。對于政治類節目,在當前媒體生態環境下,可放棄收視率評價,但是也需要把收視率作為參考;對于公益類節目需要設置收視率底線,同時設置多元化評價指標;對于商業類節目在加強節目合法合規審查的同時,可以放手讓其博取收視率接受市場檢驗。
2 避免地方上星綜合頻道辦成“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
1)“新聞宣傳”為主的職能定位利弊分析。“限娛令”明確提出以社會效益為主,以新聞宣傳為主的職能定位,試圖把地方上星綜合頻道打造成公益頻道,其初衷無疑是好的。但如此的職能定位并配合節目比重和欄目的硬性調整,卻有可能搭建一個使得地方上星頻道成為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的制度性誘因。例如自辦新聞節目可能會異化為各地方政府千篇一律的政績彰顯平臺。
2)廢除收視率考核加大財政負擔。廣播電視事業需要資金投入,財政劃撥行政事業費、廣告收入和政府專項撥款是電視臺的收入來源,其中行政事業費和廣告收入這兩項占絕大部分。廣告收入無疑是和收視率密切相關的,在網絡媒體、廣播、報紙和戶外媒體等多元化競爭的格局下,收視率下降必然導致廣告收入減少。廣告收入和財政撥款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收視率下降勢必增加財政負擔。從全國的情況看,2010年僅前10名省級電視臺的廣告收入就將近270億元,而2009年我國地方財政在文化、體育和傳媒三方面的支出總額只有1 200多億元,可見廣告收入對于廣播電視事業發展的重要性。收視率下降帶來的財政負擔是“后限娛令時代”需要面對的問題。endprint
以國內某省級衛視頻道為例,該臺在2006到2008年收視率高的時候一度達到省級衛視第3名。在2011年1月和3月該頻道進行兩次改版,先人一步采取類似“限娛令”的措施,打造公益電視臺。其措施是實施“一不二減三增”:不播商業廣告;減少電視劇和外包節目播出量,將電視劇清出黃金檔;增加公益廣告片、城市宣傳片和一系列自辦新聞、紅色文化節目。據《北京日報》報道,改版后收視率大幅下滑,在省級衛視中排名下滑到第22名,和2010年相比,改版后該臺廣告收入減少3億。經費缺口需要該頻道所屬的廣電集團綜合經營自身平衡掉1.5億元,剩下的1.5億元由政府財政填補。據報道該臺衛視廣告中心裁員20%左右,其所屬的廣電集團也面臨工資集體下調的壓力。
3)博弈結構改變的負面影響。如果說廣告收入的削減形成的新增財政支出,財政愿意負擔也能負擔得起,這導致兩方面結果:一方面使得財政支出效率下降,另一方面也使得電視臺節目制作的激勵機制發生轉變——從追求市場認同轉變為追求財政劃撥單位即上級主管部門的認同。
一旦這樣的博弈結構構建完成,就有可能演變成“虧了財政、冷落了屏幕、削弱了廣播事業發展”的誰都不愿意看到的結果。由此有可能使得電視臺成為多年來飽為各界所詬病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造成是公共財政和公共資源的低效率使用。應該說在未來“后限娛令時代”,還要出臺配套政策避免這樣的趨勢發生。
3 行政命令方式對電視市場建設的負面影響
變革計劃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各行各業改革的基本價值取向。黨的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電視市場和廣播電視資源的配置也當然應該遵循這一原則。政府調控是間接性的、引導性的,而非行政命令和資源絕對控制。
針對當前“過度娛樂化”采取的“限娛令”是“急癥下猛藥”,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限娛令”采取的是類似計劃經濟的手段,對節目欄目的設置、播出時段時間,用行政命令和計劃指標的方式實施干預。這不可避免帶來一定負面因素。
1)市場秩序和資源配置行政性洗牌。電視頻道節目設置和欄目的特長是在收視市場長期選擇中逐步形成的,需要歷史傳承和厚重底蘊。例如某些臺擅長國學文化、有的臺擅長綜藝文藝、有的臺擅長新聞報道,在市場選擇的過程中,管理資源、創意資源和資金等資源會得到高效率配置。即便是諸如NHK、BBC、CNN等國際知名公益電視臺,也是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也不是行政干預的結果。
“限娛令”對欄目設置、播出時間都做出“一刀切”式的細致規定,打破了既定的市場選擇結果,從而引發資源配置的人為干預,難免導致資源低效率使用。例如某些頻道娛樂節目資源豐富,被迫向其他臺轉移,這樣的轉移不是市場自發的資源并購、重組的結果。
2)創租和尋租帶來的困擾。通過行政命令而非市場競爭的方式創造的收益,被經濟學家成為“租金”。例如“限娛令”使得娛樂節目播出的時間變得非常稀缺,而廣告收入主要依靠娛樂節目獲取,由此播出娛樂類節目的權力就成為“租金”。人為制造這樣稀缺性的行政命令稱為“創租”、對這種收益的追逐(例如向行政部門申請娛樂節目的開辦權力的種種“公關”行為)稱為“尋租”。
首先,由于央視有專門上星綜藝頻道,“限娛令”并未對央視的娛樂節目做出限制,由此難免導致娛樂節目帶來的廣告收入從地方臺流向央視,“限娛令”為央視創造出“租金”;其次,地方臺對娛樂節目“配額”的爭奪,會導致競相向主管部門“尋租”,獲取節目“準生證”。“創租”和“尋租”帶來的困擾是:主管部門的行政行為忙于制造人為稀缺性,而淡化監管和行政水平的提高;衛視頻道不是通過提高節目水平獲得觀眾認可來保持欄目的長期播出,而是通過跑關系、走門路獲得節目的審批,造成廣播電視資源低效率使用甚至流失。
3)監管難度加大、監管成本上升。首先,“限娛令”的實施除了要求必備的“一把手責任制”“建立專門收聽收看機構”“強化處罰措施”等措施,還必須出臺大量配套措施。例如近期出臺了2012年針對選秀節目的管制細則:“要求唱歌比賽以唱為本,選拔內容必須占整場節目的80%以上;嚴格控制主持人串詞、評委點評、選手感言、插播畫面、親友抒懷的時長,不得超過20%;在評委、嘉賓方面,廣電總局要求這些人應具有良好的社會公德,點評要公正、專業、恰當、簡短;此外包括手機、網絡、電話等任何場外投票方式依舊被禁止。”這些細則使得監管部門的操作難度不斷加大,而且隨著配套措施越來越多,節目制作的難度和監管成本都會提高。
其次,地方臺和“限娛令”開展“管制游戲”將使管制難度進一步加大。各省在上星綜合頻道受到嚴厲管制限制之后,為了彌補廣告收入下滑,勢必把非上星的地面頻道市場化運作。例如有媒體報道,重慶廣電集團為了彌補上星綜合頻道廣告收入下滑,通過將11個地面頻道市場化運作彌補。這種格局下,“過度娛樂”的問題勢必向地面頻道蔓延,“限娛令”也難免進一步擴大。如此龐大的監管體系,運轉成本將不斷上升;即便有效管制住了,“過度娛樂”的傾向便有可能向廣播、網絡等其他媒體蔓延。
4 引導和鼓勵娛樂節目傳播主流價值觀更為關鍵
“限娛令”是從整治娛樂節目低俗引發的,其采取以“堵”為主的策略雖然是形勢所迫,但可能產生諸多問題。在此我們有必要重新考量對娛樂節目的治理策略,變“堵”為“疏”,力爭達到“娛樂和主流價值觀共贏”。
1)“寓教于樂”是娛樂節目的功能定位原則.娛樂節目是一種群眾喜聞樂見的電視欄目形式,這樣的欄目形式既可以反映低俗的,也可以反映高尚的內容。在革命戰爭年代、在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乃至抗美援朝的戰場上,大量主流價值觀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正是通過各種娛樂化的形式,傳遞到人民群眾和干部戰士當中的,如快板書、相聲、各種曲藝、話劇和電影等。在我國改革開放的今天,也不應把娛樂節目看作是主流價值觀的對立面,應考慮把娛樂節目作為傳播主流價值觀的重要手段。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不是盲目限制娛樂節目的發展,而是應該讓娛樂節目承擔傳播主流價值觀的職能。采取“寓教于樂”的方式,主流價值觀才能更便于群眾所接受。例如完全可以通過婚戀節目這樣年輕人易于接受的方式,把婚戀道德、婚戀文化和婚戀法律法規等很好的傳播,這不是一件雙贏的事情嗎?試想如果板起面孔講大道理,收視率又不高,這樣的模式對于主流價值觀傳播的效果就大打折扣。
2)娛樂節目的改造需要正確引導和創新。從政府管理當局的角度看,在“后限娛令時代”應該更注重制度性引導。一方面,從限制娛樂節目發展的制度環境,轉變成主動去幫助、引導娛樂節目健康發展的制度環境,更多從業務上指導娛樂節目如何更好地反映主流價值觀;另一方面,管理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應以提高節目水準、制作引人向上的節目為宗旨,并且鼓勵娛樂節目創新。
從娛樂節目制片人和電視臺的管理者看,應該增加對主流價值觀的自信心,不斷探索和創造出承載主流價值觀的節目表現手法,力爭發揮娛樂類節目的教育功能,創立“健康娛樂”的新理念。
3)對娛樂節目的成功改造有助于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限娛令”中提出“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有機統一”的政策目標,這就需要我們放棄“把娛樂和主流價值觀對立起來”的思維模式,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認識到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不是此消彼長的互相替代的關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滲透和相互促進的共贏關系。
對娛樂節目成功改造易于達到如下多方共贏:(1)“寓教于樂”、把主流價值觀滲透到娛樂節目中被大眾廣泛接受;(2)電視頻道博得收視率獲取高額廣告收入;(3)企業因此樹立良好的形象增加銷售收入和股東價值;(4)財政負擔隨著電視節目經濟效益的增長得以減輕,全社會財政支出的整體效益獲得提升。
參考文獻
[1]周小普,孫媛,劉柏煊.電視節目收視率價值再辨析[J].現代傳播,2015,37(9):1-6.
[2]呂巖梅,周菁,雷蔚真.發達國家收視率調查的基本格局、主要方法及監管機制研究[J].東岳論叢,2011,32(8):102-108.
[3]楊皓暉.“限娛令”后電視媒介生態環境的危機與重建[J].當代傳播,2012(2):49-5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