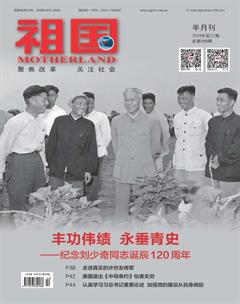從孔門師生關系到中國現代性精神危機運思
摘要:在中國社會語境的現代化進程中,經濟技術飛速發展、制度理念日新月異,然而先進性背后是由上到下的結構重組,人與人之間的依賴打碎,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破裂,個體價值判斷受到沖擊,逐漸積聚為社會價值規范系統問題,個體甚或文明的意義失落。簡言之,社會文明面臨精神危機。而驅散表面的“煙霧”,終極問題在于“關系”的處理不當。本文從儒家倫理中微觀一角“師生關系”入手,試圖為“人”之“關系”處理尋求借鑒,以期融合傳統價值與時代話語。
關鍵詞:儒家 師生觀 危機 對話
一、孔門師生狀
《論語》開篇第一章第一句即“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緒言即通過描繪不同場合、情境之下的得體回應,以一片和諧之景從學習角度闡明君子之要求。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表示:“朋,假借也,表示群鳥聚在一起的情形。”所謂“同門、同師為朋”,由此可見,孔門師生及同門之間一開始的基調便是和諧。
當然,《論語》中提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意即廣泛的人際交往中形成的不穩定的學習關系,并未形成傳統意義上的“師生倫理”,本文暫且不作討論。專就孔子與其弟子關系處理而言,大致可用幾個關鍵詞概括:位平、境通、志同。
(一)位平
所謂“位平”,并不是泯滅師生之界限,喪失對師長的尊敬,而是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師生平等交流、教學相長,即師生在深層意義上的平等。固然儒家強調“禮”,強調尊師重道,但就其深層設定來看,正如上文所提,孔子所言:“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孔子是老師,但他首先承認自己是學生,要不斷取人“善者”而從之或擇人“不善者”而改之。在此前提下,孔子授習采用互動式交流法,師生同坐、同游以論道。如第五章《公冶長》中孔子與子路、顏回談論各自的志向,孔子曰“各言爾志”,給予弟子充分自由的表達空間;弟子言“愿聞子之志”,就是孔門師生平等交流、互動式教學之例。孔子從不端持師道權威,而主張“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他尤其注重學生中的不同意見及聲音,并將此作為共同進步的基礎,而對學生“對吾言無所不悅”(《論語·先進》)的態度大加斥責。例如當子貢向孔子請教:“貧而無諂, 富而無驕, 何如?”孔子的回答是:“可也, 未若貧而樂, 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告諸往而知來者” (《論語·學而》) 師生二人彼此切磋討教,相互啟迪,便是孔門師生開放平等關系、理解接納之勢的典范。
(二)境通
所謂“境通”,即“境遇相通”,指面對異己之不同遭遇時的感同身受,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年譜》陸九淵),設身處地是“愛”的前提。孔子師生仁愛共濟,感情篤深,這不僅是孔子獲眾多弟子追隨的重要原因,也是孔子給學生上的重要一課。這份“通”體現在生活與教育的各個角落。例如孔子客觀理解公冶長,《論語·公冶長》中孔子認識到其“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并將自己的女兒嫁于他;又如孔子如家長般深切愛護學生,《論語·先進》中孔子因顏淵之死而“哭之慟”;在教學活動中,孔子細致深入地了解每一位學生的特點,把握其獨特性,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 由也彥。”(《論語·先進》)并且孔子站在學生角度由淺入深循循善誘,而不是站在長者角度的空泛闊談。如《論語·憲問》中孔子對子路“問君子”的回答:從“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再到“修己以安百姓”,層層深入以期子路更好領悟;并且孔子善于因材施教,同一問題對不同學生作出不同指導。如不同弟子提出“聞斯行諸”之問題,孔子根據不同的性格特點及不足之處作出不同回答。子路之“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之“聞斯行之!”加上孔子對不同弟子作出的“仁”的不同回答,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三)志同
所謂“志同”,即“志道相同”。在平等交流、互動啟迪、仁愛共濟基礎上,孔門師生追求共同的道德境界,追隨真知正義。孔子尤其注重為人師表,《論語·顏淵》中“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孔子以身作則,以己之“正”率學生之“道”。孔子有所戒絕,《論語·子罕》中,“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有所追求,有志于“仁、義、禮”,有志于勇,有志于“君子不器”(《論語·為政》)……最終達致“大同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但孔子不是“填鴨式”灌輸一己之價值觀與學生,而是以身作則、以身正道之后的自然吸引,或者說儒家之志是孔門師生在互動交流中共同積淀不斷完善的。正如《孟子·公孫丑上》中評論:“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二、微觀到宏觀:現實之摹寫與運思
(一)摹寫現實
聯系社會現實危機,市場邏輯泛化,價值被外化為“物”,用“多少”而不是“好壞”來粗暴評判。世間萬象紛繁復雜,社會和人卻難逃“單向度”的命運——人們雖然過上了舒適、優裕的物質生活,其精神生活卻是貧乏的、空虛的。人們對“意義”呈現前所未有的焦躁探尋正是意義喪失的鐵證,正如尼采的吶喊:“呼喚意味著缺少。”生命的意義,成為一個真正空泛而無解的問題。
除此之外,處在轉型跨越時期的社會,各領域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尤其是精神危機。“貴族”文化盡失,假冒偽劣產品層出不窮,“更高、更快、更強”的強者邏輯成為“共識”,鄉村被裹挾進城市,傳統建筑讓步于城市大道;“老人該不該扶”引發社會論戰,道德準則成為自我標榜的工具,金錢績效成為萬事萬物的衡量標準,綠水青山難敵金山銀山……當然危機存在,應對之策也在路上,相關深思從未停止!
(二)現實運思
驅散表面層層煙霧,歸根結底在于“關系”的處理不當。“人”不是高度抽象的先驗理性也不是形而上的存在,而首先應該是活生生的“在世者”,是“活”的過程。但人從不能單獨存在,而必須借助于外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又是“關系”的載體,其形態是以“人”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的“關系網”,因此重新審視人與自己、與人、與自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模式,對危機轉化大有裨益,孔門師生關系處理便能為我們提供一面鏡子:
1.位平
位置相平是對話的前提。首先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人之為人,一半是動物一半是神,前者乃因為人均有“食色”之欲,后者乃因為人之“動物性”有所節制。每一個人都應該認識到自己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我”,共處于世,我你他都是同行者,平等而無差。認識到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是改善人際關系的前提。
人來自于自然界最終歸于自然界,可以絕對地說,人之一切均倚仗于自然界。那在自然界面前不妨打破“萬物之靈”的驕傲,以自然為師,尊師重道的同時,不憚權威,與自然互動式交流,共進式發展。
2.境通
感同身受是仁愛的基礎,“深有同感”應該是“出手相助”的最大動力。孔門皆有志于“仁”,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仁”是從“親”到“民”再到“萬物”的推擴,是包括對己之仁、對人之仁、對物之仁、作為本體之仁的一整個動態體系,所以“如何推擴”或者“如何境通”就成為問題。我認為“對己之仁”是基礎,唯有修己之身才有可能肯認“類”,進而推至“萬物”;唯有自身認知提升,自身感情培育,才有滿溢至他者的可能性。因此要想互助共進,必要感同身受,必要首先修己。
3.志同
志趣相同是結伴而行的保障,唯有共同的旨趣才可構建牢固的命運共同體。孔門共同的追求構建了牢固和諧的師生共同體,在共同志向的指引下師生同心同德各盡其力;同理對未來共同的期許將構建緊密堅固的紐帶防線,在價值取向日益多元的今日,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夢想勢必成為改善社會現實危機的精神指引以及防護劑。
綜上,錯綜復雜之局面可落實至“關系”之處理。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之主干,其倫理體系積淀而成為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之血液。在當今現代性精神危機語境下,關鍵在于能否從傳統儒家倫理體系本有的內容中引申出具有現代價值的倫理內涵。本文旨在從微觀角度的孔門師生關系處理為現實危機之轉化提供有益運思,但其深層價值仍待我們挖掘、深思。
(作者簡介:李俏,東南大學本科生,專業:哲學與科學系。)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