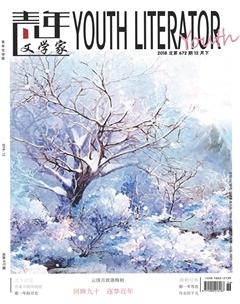談張愛玲小說創作中的女性敘事
摘? 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張愛玲是一個有著獨特個性的作家,她用女性視角觀察社會,寫世間百態,以上海和香港為背景,塑造了特定時代里不同的命運、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精細刻畫了兩性糾葛中女性的情感問題,表達了對女性命運的深切同情,可以說,張愛玲是女性文學的代表。
關鍵詞:張愛玲;女性;敘事
作者簡介:李宇馳(1990.6-),女,漢族,遼寧鐵嶺人,碩士學位,沈陽大學文學院16級在讀研究生,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6-0-02
一、什么是女性敘事
女性敘事并非指文學概念,只是用來分析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角色時為了便于分析而采用的說法,主要用來探討小說的寫作方法、寫作意圖,以及小說中女主人公的生存現狀。
在文學理論中,在敘事學里,敘事模式一向是重點關注部分。俄國文學理論家普洛普在寫的《民間故事的形態》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功能”一詞,并將其解釋為“人物的行為,服從人物行動意義的行為”。他鑒于以往劃分民間故事類型的方法和標準是根據人物特征的做法的缺陷和弊端,認為“因為故事中的人物千變萬化,很難找出供分類用的不變因素”。他站在結構主義的角度研究了上百個俄國民間故事,“指出了民間故事的基本單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行為功能”。并從中總結出31種敘事功能。
普洛普的這一做法,其實就是在具體劃分故事結構和內容時,發現了在文學作品中,故事情節是高于故事的結構的。如果把這一理論放到張愛玲小說中,我們就會發現,從功能上看,張愛玲小說不管是寫在什么時間,創作背景是哪里,作品所講述的故事都是男女之間的情感關系。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看:
《沉香屑·第一爐香》,這是張愛玲的成名作,是她的第一部小說。講述的是葛薇龍由清純的大學生自愿轉變為“妓女”的過程。葛薇龍是個上海女孩,在香港讀大學時,被姑媽引誘,周旋于各種各樣的人以滿足自己的經濟和肉體需要。后來,葛薇龍愛上了紈绔子喬琪,最終墮落成自愿出賣肉體的高級妓女。
《傾城之戀》,講述的是家道敗落、自己又遭遇離婚變故的白流蘇投奔娘家,受盡親戚白眼和冷嘲熱諷,最后因被嫂子排擠而被迫離開,在認識了有錢的范柳原后,離開上海去香港和范柳原同居的故事。
《色戒》講述了女大學生王佳芝奉命鋤奸,在執行任務時與漢奸易先生弄假成真,發生感情糾葛,導致暗殺時放走了易先生。但是易先生逃生后,還是殺掉了王佳芝等人。
從上述個例子可以看出,張愛玲小說都是以女性為主要人物,講述的其實都是各種環境下的情感故事。小說的主題也都是男性和女性之間的情感糾葛。從普洛的功能說角度看,張愛玲小說是通過“男性”和“女性”這些各有特點的不同符號,表達了張愛玲自己對女性命運的思考:女性的命運為何如此不幸和痛苦?為何如此無奈和愴然?
在張愛玲的作品中,這些問題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答案,那就是在男權社會統治一切的情況下,女性不管怎么反抗,如何掙扎,都逃脫不了男權社會的統治。要解決女性問題,改變女性的不幸命運,只有先尋求女性自身的解放。所以,張愛玲寫的故事里寫的是戰爭、動亂、革命、政治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故事,寫的是小到的灰色陰暗的家庭成活、大到敗落解體的大家族,還有正在發生變化的時代,這些其實都是在為故事里的女性不幸命運進行鋪墊,探討女性的問題。
二、張愛玲小說的兩性糾葛
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在女性愿望的實現過程中,男性都是處于阻礙的角色。在男權社會里。由于男權處于統治地位,因此不管女性怎么掙扎反抗,用情也好,用計也罷,哪怕是用力,最終都歸于失敗。
《創世紀》張愛玲寫的一個充滿悲傷的故事。故事描寫的是一個清末敗落的貴族家庭里的由祖到孫三代婦女的一生命運。家中的第一代女性是祖母紫薇。她出身富貴是家人的掌上明珠。戰亂中,父親的一封電報把她嫁給了一個素不相識、完全不了解的陌生男人。這個男人全無責任感,也無謀生自立的能力,是個長不大的孩子。從出嫁開始,紫薇就要一個人支撐起全家的生活,到年老時還要通過典當來養活一家老小成群的子孫。家中的第二代女性是全少奶奶,紫薇的媳婦。全少奶奶生了一堆孩子,嫁的丈夫是個典型的“八旗子弟”,終日閑在在家中,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不考慮養家,總說窮的過不下去了“就送兩個大女兒去當舞女”。全少奶奶忙得沒梳洗打扮就給紫薇做過生日吃的飯菜,他不僅袖手旁觀,不幫忙,還當著眾人的面嘲笑謾罵。看到兒子不爭氣,紫薇卻只責怪全少奶奶,說兒子不學好,不爭氣是因為兒媳婦不懂事,不會勸鑒。第三代女性是瀠珠,全少奶奶的女兒,因為是女兒,在家中地位低下,不受重視,奶奶找茬訓斥她,出去找工作,又被責怪認識了陌生人,反正不管瀠珠怎么做,都會被責怪。
紫薇是不幸的,其原因是失敗的婚姻和父親的愚忠;全少奶奶也是不幸,不幸的原因也是失敗的婚姻;而瀠珠的不幸,正是其祖母、母親不幸的婚姻的延續。三代女性的不幸實質都是源于男權社會的桎梏,她們在男權和夫權的壓迫下,無力也不敢抗拒,淪為犧牲品,她們的一生讓人充滿無奈和嘆息。
從這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在男權社會的壓迫下,在夫權和家族長輩的壓迫和控制下,深陷不幸婚姻,沒有話語權和社會地位,沒有自己的思想和自由空間,沒有自我,只能在無奈和痛苦中選擇屈服。因此,這些女性不管其出身于哪個階層,也不管家庭條件如何,都有著封建傳統的“婦德”面對來自各方的壓迫與控制,她們只會選擇服從、馴順,或者試探性的反抗一下后又重新歸于原位,變本加厲地討好順從。幾千年的傳統,使她們所謂的聰明才智只是體現如何討好男人以求得自己在家庭中的生存上來。
除了表現女性在情感糾葛中的無奈和悲哀,張愛玲還在部分作品中表現了一些因為社會和個體性格等原因造成的個人悲劇。如代表作品《小艾》。小艾是舊社會一個大家庭的婢女,是一個丫頭。她秉性內向,地位低下,寡言少語。再被主人五老爺強奸后,面對強大的舊勢力的壓迫威逼,她無力反抗,只能任人擺布,由人欺凌。這是一個典型的男權社會下權勢階層對女性的迫害,五老爺是權力者,他依仗自己的權力和地位隨意玩弄、迫害小艾,視女性為玩物和泄欲工具,是男權的代表。
其實,張愛玲的筆下都是一些小人物,其性格和其他方面都是有缺陷的,不徹底的。但是,與筆下的男性角色所反映的虛偽、冷酷、懦弱和絕情相比,女性角色中總會閃現出一抹亮色,出現一絲溫情,這也反映出作者對人性的肯定與追求,也是對筆下女性形象的一絲肯定。
三、張愛玲小說的女性敘事
結構主義認為,“事物的真正本質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們在各種事物之間構造,然后又在它們之間感覺到的那種關系”。在結構主義者看來,事物的結構可以為分兩部分:表層和深層。可以被直接觀察就是表層結構。而不能被直接觀察的就是深層結構。也就是說,深層結構反映的是事物的內在聯系,要想發現或者感知事物的深層結構只能以某種形式的認知才能發現或感知。所以,“成雙的功能性差異的復雜格局這個概念,或曰二元對立概念顯然是結構概念的基礎”。
張愛玲小說在講述兩性故事的時候,就是追求這種男女二元對立的張力,這是作者內心深處的情感活動,它與心理、社會、政治等的外部因素結合在一起,由內向外的擴展,讓故事變得更加的生動和豐富。那么,張愛玲是怎樣表達出她的創作動力的呢?我們結合以《紅玫瑰與白玫瑰》進行分析。
《紅玫瑰與白玫瑰》講述了佟振保與嬌蕊和孟煙鸝的兩段情感故事。佟振保結識了朋友妻嬌蕊,與之開始了一段戀情,當他發現嬌蕊動了真情的時候,卻害怕了,退縮了。多年以后,他在遇到嬌蕊的時候,得知嬌蕊為他離婚,兩人的舊事卻已成幻影,面對靜靜訴說的嬌蕊,佟振保只能流下難以訴說的淚水。
在多年以后相遇的佟振保,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成功人士。但是,這樣的一個人在面對舊日情人時,為何只是流下淚水?昔日的弱女子,如今已經人到中年、歸于平靜的嬌蕊,反而沒有了激情,變得鎮定和沉默了許多,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經過那段激情的歲月,嬌蕊成熟了許多,清醒了許多,也增加了智慧。她還有愛,還認識到除了愛,還有其他有價值的東西,如勇敢面對生活的膽量。與她對比,佟振保在離開嬌蕊后,事業雖然成功了,物質生活也頗為滿意,妻子也符合大眾眼光,但是缺失了愛的能力。他為自己建立的生活狀態成為了一個虛幻的人生狀態,在這個狀態里,他迷失了自我,變得放浪形骸,當他面對變得堅強的嬌蕊時,佟振保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懦弱,發現了自己人格的殘缺處,但是過去的已經永遠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告訴人們要珍惜已有的啊。
從《紅玫瑰與白玫瑰》的故事情節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這部小說中,還是一如既往地表達了作者對男權社會的批判。在作者對男性表示失望的同時,作者對嬌蕊感情受傷后的蛻變給予了肯定,表示了一定的贊賞。面對男權社會的傷害,嬌蕊以淡定相對,選擇了勇敢的面對生活。這時作者用鮮明的筆觸傳達出的對女性態度的贊美,這就是張愛玲小說的敘事動力。她筆下的眾多女性角色,無論是虞家茵和顧曼楨,還是成長中的嬌蕊,還有那些男權社會下無助無望的眾多小人物,像霓喜、紫薇、葛薇龍、白流蘇等,她們用女性特有的、比男性更為強大的勇敢,支撐起更大的生存空間,頑強地在男權社會里堅持著。
四、結語
總的來說,張愛玲小說講述的始終是男女兩性的情感糾葛,是糾纏不清的兩性戰爭,對于這場戰爭的結果,張愛玲沒有給予明確,也沒有指出女性解救自己的道路,而是在反復的強調女性又回到灰暗中去。但如果深入剖析這些故事我們會發現,從女性敘事角度,從人物承載的“功能”上看,已經表達出對女性的肯定,再深刻描摹現實生活的基礎上,也表達出對女性不幸命運的深深地嘆息,而這大概也是張愛玲所述故事的本意所在。
參考文獻:
[1]劉柯,張香萍.論張愛玲小說創作中的設色藝術[J].淮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05).
[2]金順珍.張愛玲小說的童話式結構空間[J].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02).
[3]賀玉慶.張愛玲小說中服飾符號意蘊探析[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03).
[4]崔建敏,唐培,張志蔥.論張愛玲文字的基本風格[J].網絡財富. 2010(18).
[5]張冬梅.性格的扭曲 精神的病態——試從神經質性格視野看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J].名作欣賞. 2016(30).
[6]龔光宇.華麗與黯淡:張愛玲筆下的色彩世界[J].銅陵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