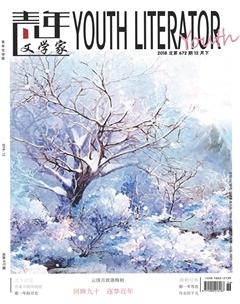大江健三郎小說《聰明的“雨樹”》中的邊緣意識(shí)
史小華 龍臻
基金項(xiàng)目:2017年度江蘇省高校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項(xiàng)目《大江健三郎小說美學(xué)特質(zhì)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2017SJB1223。
摘? 要:大江健三郎素有“邊緣意識(shí)”作家之稱,他把“邊緣意識(shí)”作為在文學(xué)領(lǐng)域開疆辟土的支點(diǎn),立足政治邊緣,追求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自由風(fēng),從而締造出大江文學(xué)獨(dú)有的美學(xué)高度。短篇小說《聰明的“雨樹”》借助精神病患者的視角深入探索邊緣人物的生存困境,以復(fù)調(diào)的結(jié)局揭示邊緣人的不可期的未來(lái)。
關(guān)鍵詞:大江健三郎;邊緣意識(shí);邊緣人;復(fù)調(diào)
作者簡(jiǎn)介:史小華(1979-),男,江蘇南通人,南通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副教授,碩士,主要從事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龍臻(1975-),男,江西永新人,南通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副教授,碩士,主要從事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
[中圖分類號(hào)]:I1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8)-36--02
一、引言
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得主大江健三郎以日本傳統(tǒng)文學(xué)思想為基石,并借以豐富的想象力,結(jié)合日本式獨(dú)特的語(yǔ)言文體,將東西方文學(xué)互融,使得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呈現(xiàn)東西合璧的藝術(shù)特色。大江先生通曉西方文藝創(chuàng)作的思想,通過對(duì)其創(chuàng)作的諸多作品的解構(gòu),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大江小說敘事上的互文性特征,與此同時(shí),“邊緣意識(shí)”更是大江先生諸多作品中不容忽視的一個(gè)共通的關(guān)鍵詞,東方式的“邊緣意識(shí)”滲透在西式文本中,用西式理論闡釋東方式的“邊緣意識(shí)”,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豎起一道新的豐碑。大江先生堅(jiān)持主張?jiān)谥髁魑幕涞慕Y(jié)構(gòu)中,邊緣人的聲音無(wú)疑是被壓抑著的,作家通過創(chuàng)造可以使得邊緣人的形象凸顯出來(lái),由此可以喚起人們對(duì)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再認(rèn)識(shí)[1],從小說《聰明的“雨樹”》中便可窺一斑。本文通過短篇小說《聰明的“雨樹”》中第一人稱“我”的觀察,深入探索邊緣人物的生存困境,以復(fù)調(diào)的結(jié)局揭示邊緣人的不可期的未來(lái),從而引發(fā)人們對(duì)社會(huì)的反思,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抨擊。
二、《聰明的“雨樹”》中的邊緣意識(shí)
《聰明的“雨樹”》是大江健三郎先生于1980年1月發(fā)表于《文學(xué)界》上的一篇短篇名作,并且以此篇為開端,相繼發(fā)表了以“雨樹”為主題的系列小說。可以說“雨樹”系列小說的創(chuàng)作是大江先生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領(lǐng)域的一次重大突破,即,同主題系列小說促成大江文學(xué)中“類長(zhǎng)篇”的誕生。大江先生在“類長(zhǎng)篇”作品中從“邊緣意識(shí)”出發(fā),試圖建立一種與中心文化對(duì)峙的圖式,揭示邊緣·中心價(jià)值相當(dāng)?shù)男挛膶W(xué)范式。《聰明的“雨樹”》以敘事者“我”作為觀察者,借助精神病患者的視角展開敘事。“我”作為一名參加夏威夷大學(xué)東西方文化中心研討會(huì)的學(xué)者,在研討會(huì)和酒會(huì)上以公正的眼光,冷靜客觀地觀察周圍形形色色的邊緣人物間發(fā)生的邊緣人事件,揭示邊緣人物的生存困境,喚起社會(huì)的反思。
(一)精神病人的視角
對(duì)于“邊緣意識(shí)”的再認(rèn)識(shí)是解構(gòu)大江健三郎作品的一個(gè)重要抓手,顯現(xiàn)于文本中的邊緣意識(shí)無(wú)論從思想方面或是藝術(shù)技巧方面都堅(jiān)持與“中心文化”相牽制,這也是促使大江先生不斷嘗試運(yùn)用相關(guān)敘事手法的原因之一,從其諸多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軌跡中隱然可現(xiàn)。邊緣人物的塑造契合大江先生東西合璧式的寫作風(fēng)格,通過對(duì)邊緣人物的設(shè)定的另類特質(zhì),即,與所處環(huán)境的不協(xié)調(diào)性,凸顯人物形象的張力以達(dá)到別具一格的藝術(shù)效果。這里我們所探討的邊緣人特指社會(huì)學(xué)意義上的概念。簡(jiǎn)而言之,處于社會(huì)的邊緣,社會(huì)地位低下,甚至從某種意義而言毫無(wú)社會(huì)地位,這類人往往毫無(wú)歸屬感,有別于正常人的個(gè)性。《聰明的“雨樹”》在邊緣人物設(shè)定方面將目光投向精神病患者,著眼于精神病人的視角深入探討邊緣人的無(wú)可奈何以及內(nèi)心的孤獨(dú)。縱觀整篇小說的文本,不難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邊緣人物精神病患者的著墨并不多見。其中對(duì)于一位由于間諜記憶而痛苦不堪的美國(guó)青年精神患者的敘述,讓敘述者在冷靜地觀察中產(chǎn)生憐憫,但卻不知如何安慰那個(gè)凄苦掙扎,渾身煙塵油漬,滿臉憂傷的矮小人物。“身體矮小”、“面部神經(jīng)害病”、“苦惱不堪的神情”等一系列具有負(fù)面意義的詞語(yǔ)的描述,使得邊緣人物的形象躍然紙上。小說最后通過酒會(huì)的參與者在得知酒會(huì)竟然是由一群叛亂的精神病患者舉辦時(shí),紛紛惶惶離去。原先喧鬧無(wú)比的酒會(huì)頓然變得死一般的寂靜,戲劇性的轉(zhuǎn)變讓小說充滿反諷的意蘊(yùn)。從研討會(huì)上學(xué)者間的學(xué)術(shù)探討,酒會(huì)上的激辯狂歡到真相大白后的逃離,使得整部小說自然形成一個(gè)反諷的鏈環(huán)。
(二)邊緣人的生存困境
大江先生主張對(duì)于當(dāng)前的日本而言,主流文化缺少真實(shí),不具備代表性。[2]正因如此,大江先生常常將邊緣人置于小說表達(dá)的中心,闡釋邊緣文化的必要性,在此基礎(chǔ)之上建立與主流文化對(duì)峙的圖式,通過對(duì)邊緣人思想生活的探索,揭示邊緣人自始至終無(wú)法擺脫生存困境的本質(zhì)。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相較于主流文化,邊緣文化更具開放多樣的特性。大江先生正是通過邊緣文化,邊緣人物的書寫建構(gòu)起獨(dú)具匠心的大江文學(xué)的范式。例如,《萬(wàn)延元年的足球隊(duì)》以森林山村作為創(chuàng)作背景,通過詩(shī)意的想象以及高超的藝術(shù)手法勾勒出人類面臨困境而不安的圖式。森林曾經(jīng)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是主流文化的發(fā)源之地,而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使得人類離開了最初的棲息地,漸而成為被人忽視的邊緣之地。作品中的人物蜜三則是邊緣人的典型,是大江小說“邊緣意識(shí)”的重要體現(xiàn)。大江先生以邊緣人為小說的主角,將其置于與主流文化相隔絕的森林中,試圖借助邊緣文化及主流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揭示邊緣人的生存困境,來(lái)尋求民族文化發(fā)展的動(dòng)力。[3] 《聰明的“雨樹”》則以敘事者“我”作為觀察者,通過“我”的所見所聞,揭示邊緣人群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現(xiàn)狀,并以高超反諷的藝術(shù)從側(cè)面烘托邊緣人的生存困境。整部小說中既有直接對(duì)美國(guó)青年這一邊緣人的外貌描寫,也有通過敘事者“我”的內(nèi)心獨(dú)白進(jìn)行側(cè)面敘事。“雨樹”是敘事者“我”和美國(guó)女人婀嘉德的談話中的一個(gè)重要元素,小說借以“雨樹”的敘述與邊緣人物進(jìn)行巧妙關(guān)聯(lián),為后文情節(jié)的發(fā)展埋下伏筆。在敘事者“我”的眼中,“雨樹”位于黑色的邊緣,卻有一個(gè)深不可測(cè)且擁有足夠強(qiáng)大力量的黑暗深淵。這深淵般的黑暗足以懾人魂魄,讓人產(chǎn)生質(zhì)疑:如此環(huán)境怎能收容精神病患者?美國(guó)女人婀嘉德在小說中是一個(gè)主流人物的存在,她并不懂得如何理解邊緣人物內(nèi)心的煎熬,邊緣人物的生存困境,只能借助敘事者“我”的微弱發(fā)聲以喃喃自語(yǔ)的內(nèi)心獨(dú)白喚起人們的關(guān)注。
(三)復(fù)調(diào)的結(jié)局
《聰明的“雨樹”》整部小說在情節(jié)設(shè)定上以研討會(huì)以及酒會(huì)上的討論、激辯式的人物對(duì)話作為鋪墊,輔以敘事者“我”將“雨樹”的巧妙介入,賦予看似情節(jié)簡(jiǎn)單的小說以懸疑與神秘感。關(guān)于小說的結(jié)局最終并沒有一個(gè)確切的交代,只是在結(jié)尾處再次提及“雨樹”。但是,敘事者“我”至今無(wú)法追究清楚“雨樹”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樹木。故事的最終走向作者似乎無(wú)法進(jìn)行把控,無(wú)法將自己的意志凌駕小說之上,開放式的結(jié)局體現(xiàn)了復(fù)調(diào)小說的藝術(shù)特征。整部小說看似荒誕離奇,加之毫無(wú)定論的小說結(jié)局,不免讓讀者感覺大江健三郎對(duì)待現(xiàn)實(shí)和責(zé)任的態(tài)度是曖昧的,但是,恰恰是這樣一個(gè)開放性的結(jié)局,揭示邊緣人物未來(lái)的不可期性。事實(shí)上,大江先生在小說高潮部分通過巴士和分乘摩托車離去的年輕人惶恐逃竄的窘樣以及美國(guó)詩(shī)人的憂郁愁容的著墨,為開放式結(jié)局做下鋪墊,以反諷藝術(shù)手法指向社會(huì)真實(shí),揭示社會(huì)的陰暗和病態(tài)。經(jīng)受主流文化結(jié)構(gòu)壓抑的邊緣人似乎只能在無(wú)底的深淵發(fā)出微弱的呻吟,在多舛的命運(yùn)中接受現(xiàn)實(shí)的摧殘,大江先生在小說中種下邊緣情節(jié)的種子,試圖在小說中建構(gòu)一個(gè)矛盾的世界,將小說的敘事在矛盾重重中頑強(qiáng)展開,通過對(duì)邊緣人物的敘事為讀者認(rèn)識(shí)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打開一扇智慧之門。
三、邊緣意識(shí)形成的原因
(一)森林、峽谷村莊的不解之緣
批評(píng)家從語(yǔ)言解構(gòu)、文本批判以及文化批判視角解讀大江文學(xué),都會(huì)有一個(gè)共同的發(fā)現(xiàn):大江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從思想內(nèi)涵到價(jià)值取向都極具鮮明的個(gè)人特色,他在諸多作品中融入想象力和邊緣化意識(shí),而邊緣意識(shí)或多或少都會(huì)跟森林、峽谷村莊甚至一棵“雨樹”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關(guān)聯(lián)。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國(guó)島愛媛縣一個(gè)被茂密森林和峽谷所環(huán)繞的偏僻山村,這里是他進(jìn)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出發(fā)地,而森林自然成了他創(chuàng)作的源泉。東京是一個(gè)國(guó)際化的大都市,是日本主流文化的引領(lǐng)之地,而這對(duì)于大江先生而言是一個(gè)完全陌生的世界,他試圖建立與主流意識(shí)相抗衡的邊緣世界,構(gòu)建大江文學(xué)中的邊緣森林社會(huì),成為其致力于文學(xué)美學(xué)追求的一條基線。小說《聰明的“雨樹”》以“雨樹”為開端和結(jié)尾,這一首尾呼應(yīng)的嚴(yán)謹(jǐn)解構(gòu)在現(xiàn)代日本文學(xué)中時(shí)有所見,這樣的創(chuàng)作能使整部小說彰顯“脈絡(luò)貫通”之勢(shì),保持小說的前后勻稱。“雨樹”系列的創(chuàng)作是大江先生對(duì)森林意識(shí)的延續(xù),盡管他十五歲時(shí)離開家鄉(xiāng),根植于其心中的森林意識(shí)不時(shí)再現(xiàn)于文本創(chuàng)作中,即便是“雨樹”以個(gè)體存在,亦能喚起大江先生對(duì)森林意識(shí)的不解之緣。基于森林、峽谷村莊而形成的獨(dú)特宇宙觀、世界觀是大江先生“邊緣意識(shí)”的衍生,從其諸多文學(xué)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試圖凸顯與主流文化相抗衡的邊緣文化的信念和使命。
(二)對(duì)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再認(rèn)識(shí)的使命感
大江健三郎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立足于現(xiàn)實(shí),又超越現(xiàn)實(shí),將現(xiàn)實(shí)與象征世界融為一體,使傳統(tǒng)與西方的文學(xué)理念和方法一體化,從而創(chuàng)作出大江文學(xué)的獨(dú)特性。[4]應(yīng)當(dāng)說,大江先生是一個(gè)有著強(qiáng)烈使命感的作家,他總能將遠(yuǎn)視歷史的目光拉回到以他的“邊緣意識(shí)”為主導(dǎo)的生活空間。《聰明的“雨樹”》將目光投向邊緣人物精神病患者,在大江先生對(duì)小說凝練的敘事中,所謂的邊緣人物精神病患者之外的主流世界其實(shí)也是病態(tài)的,在那樣的氛圍中,似乎每一個(gè)人都已經(jīng)病入膏肓。誠(chéng)然這并非生理意義或心理層面的闡釋,而是基于社會(huì)壓制而外顯的時(shí)代的病癥,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不合理之癥。大江先生認(rèn)為,被主流意識(shí)支配的一方,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中往往處于邊緣位置。他立足森林意識(shí),以森林為創(chuàng)作原點(diǎn),始終堅(jiān)守邊緣,力求喚起讀者對(duì)社會(huì)文化結(jié)構(gòu)的質(zhì)疑與再認(rèn)識(shí)。
四、結(jié)束語(yǔ)
大江健三郎深諳東西方文學(xué),以詩(shī)一般的想象力在東西方文學(xué)互碰互融中呈現(xiàn)出匠心獨(dú)運(yùn)的藝術(shù)作品。邊緣情結(jié)在其作品中的顯現(xiàn),是大江先生森林意識(shí)在記憶中的永久延續(xù)。通過對(duì)大江諸多作品中邊緣人物設(shè)定的歸納,可以深刻感受到大江先生對(duì)于邊緣人的那份濃烈的人道主義情懷。他堅(jiān)持以創(chuàng)作堅(jiān)守信念,從作家的歷史使命和社會(huì)責(zé)任出發(fā),試圖建立邊緣與主流相抗衡的圖式,構(gòu)建大江文學(xué)獨(dú)有的美學(xué)特質(zhì)。
參考文獻(xiàn):
[1]黃峻菠. 一生要認(rèn)識(shí)的100位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得主[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3:165.
[2]楊月枝. 大江健三郎文學(xué)作品藝術(shù)特色研究[M]. 石家莊:河北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 2013:148.
[3]羅文敏,韓曉清,劉積源. 外國(guó)文學(xué)經(jīng)典導(dǎo)論[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3:327.
[4](日)大江健三郎著;葉渭渠編;李文俊主編. 人羊 大江健三郎作品集[M]. 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7: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