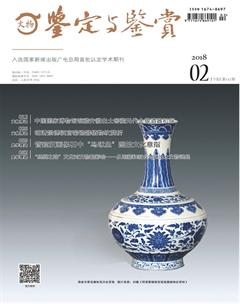玉樹通天河流域牦牛巖畫的風(fēng)格研究
張倩 唐邦城
摘 要:巖畫是古代文化的重要載體,記錄了當(dāng)時(shí)人們生產(chǎn)、生活等多方面的信息。文章對(duì)玉樹通天河流域牦牛巖畫的藝術(shù)風(fēng)格進(jìn)行分類研究,并與同屬青藏高原巖畫系統(tǒng)的西藏巖畫進(jìn)行對(duì)比分析,試圖探討通天河流域牦牛巖畫各風(fēng)格類型的文化內(nèi)涵與時(shí)代特征。
關(guān)鍵詞:通天河;牦牛;巖畫;風(fēng)格
通天河為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境內(nèi)的長(zhǎng)江干流上游段,位于青藏高原東部,青海省南部。流域內(nèi)巖畫分布相對(duì)密集,數(shù)量豐富,據(jù)《玉樹巖畫——通天河卷》一書中公布的資料,截止到2016年,流域內(nèi)共發(fā)現(xiàn)24處巖畫點(diǎn),1700多個(gè)單體圖像。這些巖畫分布在通天河兩岸的玉樹市、曲麻萊縣、稱多縣、治多縣境內(nèi)(圖1),巖畫內(nèi)容大致包括自然物、動(dòng)物、人物、建筑、工具、符號(hào)、生殖器及其他等8類。其中,動(dòng)物占絕大多數(shù),而在動(dòng)物巖畫中,牦牛單體數(shù)量最多,共計(jì)575個(gè),占巖畫單體總量的32.54%[1],遠(yuǎn)超其他巖畫單體的數(shù)量,由此可見,牦牛巖畫在通天河流域巖畫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依據(jù)通天河流域牦牛巖畫的風(fēng)格特征,將牦牛巖畫分為三種風(fēng)格,并探討各種風(fēng)格的面貌及時(shí)代,深化對(duì)通天河流域巖畫的認(rèn)識(shí)。
1 牦牛及牦牛巖畫的分布
野牦牛主要分布在廣袤的青藏高原及其邊緣地區(qū),棲息地域以大陸性氣候?yàn)橹鳌G嗖馗咴S多區(qū)域的海拔是在800萬(wàn)年以前形成的,其中,海拔高于3000米的地域面積占整個(gè)高原的85%以上,海拔高于4500米的地域面積在50%以上[3]。高海拔使得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區(qū)是嚴(yán)酷的大陸性氣候,因此,耗牛成為了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種,具有地域性特征。
牦牛圖像是青藏高原巖畫經(jīng)常表現(xiàn)的對(duì)象,也是青藏巖畫系統(tǒng)中最具本土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圖像類型之一。牦牛巖畫在我國(guó)的分布以青藏高原為中心,與青海鄰近的新疆昆侖山和阿爾泰山、甘肅祁連山和黑山、寧夏賀蘭山、內(nèi)蒙古曼德拉山等地也發(fā)現(xiàn)有少量的牦牛巖畫[4][5]。
2 通天河流域牦牛巖畫的風(fēng)格
藝術(shù)“風(fēng)格”是指通過(guò)藝術(shù)作品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相對(duì)穩(wěn)定的、反映民族或時(shí)代的內(nèi)在特性,是某個(gè)時(shí)期藝術(shù)特征的集中反映[6]。通天河流域發(fā)現(xiàn)的牦牛巖畫共計(jì)575個(gè),流域內(nèi)每個(gè)巖畫點(diǎn)基本上都含有牦牛圖像,這些牦牛圖像體現(xiàn)著通天河流域巖畫的發(fā)展脈絡(luò)。根據(jù)筆者的研究,將通天河流域牦牛巖畫的風(fēng)格分為A、B、C三種類型。
A型風(fēng)格為剪影式風(fēng)格,其特點(diǎn)是制作技法以通體敲鑿為主,牦牛體形健碩,多成群的出現(xiàn),場(chǎng)面多為狩獵牦牛、放牧牦牛、騎行牦牛。伴隨剪影式牦牛而出現(xiàn)的最常見的動(dòng)物是剪影式風(fēng)格的鹿,此外,還有豹、鷹、馬、狼、羊等動(dòng)物。A型風(fēng)格的牦牛相較于其他風(fēng)格的牦牛而言,數(shù)量最多,是通天河流域巖畫中最早出現(xiàn)的巖畫風(fēng)格,也是最具本土特性的風(fēng)格類型,其時(shí)代貫穿整個(gè)青銅時(shí)代。根據(jù)湯惠生等人對(duì)青海其他巖畫點(diǎn)所做的微腐蝕斷代法[7]測(cè)年數(shù)據(jù)以及青藏高原地區(qū)的考古發(fā)現(xiàn)[8]等,我們推測(cè)A型牦牛巖畫的時(shí)代上限為距今3000年左右的青銅時(shí)代。根據(jù)牦牛體形的變化,A型牦牛大致可以分為早、晚兩期,早期A型牦牛拱背垂腹,四肢短粗,團(tuán)尾上揚(yáng),多呈動(dòng)態(tài)(圖2);晚期A型牦牛身軀較瘦,四肢細(xì)長(zhǎng),尾巴下垂,多為行走狀,牦牛形象呆板(圖3),且數(shù)量遠(yuǎn)遠(yuǎn)少于早期A型牦牛。
B型風(fēng)格為渦旋紋風(fēng)格,其特點(diǎn)是制作技法以敲鑿輪廓線為主,并在輪廓內(nèi)鑿出渦旋紋進(jìn)行裝飾。牦牛體形健碩,牛身飾有“S”形渦旋紋或變形渦旋紋,脊背高拱,四肢粗短,牛尾微翹,多呈奔跑狀(圖4)。渦旋紋牦牛數(shù)量較少,伴隨渦旋紋牦牛出現(xiàn)的動(dòng)物多為渦旋紋鹿,而且渦旋紋鹿的數(shù)量遠(yuǎn)多于渦旋紋牦牛。張亞莎在《西藏美術(shù)史》一書中,認(rèn)為華麗的渦旋紋鹿不太可能是青藏高原巖畫內(nèi)部逐漸發(fā)展演變出來(lái)的本土風(fēng)格,只能是一種異質(zhì)的相當(dāng)成熟的外來(lái)風(fēng)格,其進(jìn)入西藏的時(shí)間大致是在距今2500年前后[9]。對(duì)比西藏和通天河流域巖畫中的渦旋紋鹿,我們認(rèn)為通天河流域B型風(fēng)格的鹿也是一種外來(lái)的成熟的風(fēng)格。但是,B型風(fēng)格的牦牛在整個(gè)西藏僅發(fā)現(xiàn)了兩例[10],而在通天河流域中發(fā)現(xiàn)較多,我們認(rèn)為通天河流域B型風(fēng)格的牦牛圖像是青藏高原本土特色的牦牛巖畫與外來(lái)B型風(fēng)格結(jié)合后的產(chǎn)物。暗藏在背后的動(dòng)因可能是人群的流動(dòng),也可能是單純的文化傳播,體現(xiàn)了通天河流域巖畫對(duì)外來(lái)文化的包容與吸收內(nèi)化。因B型風(fēng)格的牦牛常與B型風(fēng)格的鹿相伴出現(xiàn),兩者的時(shí)代應(yīng)該大致相同,據(jù)此推斷,通天河流域B型風(fēng)格的牦牛巖畫出現(xiàn)的時(shí)間為距今2500年左右,晚于早期A型風(fēng)格牦牛出現(xiàn)的時(shí)間。并且從部分巖面中可以看到兩種風(fēng)格巖畫單體的共存現(xiàn)象,我們可以得知外來(lái)B型風(fēng)格的出現(xiàn)并未完全取代早期A型風(fēng)格,早期A型與B型風(fēng)格共存過(guò)一段時(shí)間。
C型風(fēng)格為輪廓式風(fēng)格,其特點(diǎn)是制作技法以敲鑿或劃鑿、劃磨的方式刻出牦牛的輪廓,輪廓內(nèi)不見渦旋紋裝飾,僅有部分圖像在牦牛腹下部裝飾有牛毛。根據(jù)牦牛體形、制作方式的變化,可以大致將其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C型牦牛制作技法為密點(diǎn)敲鑿法,牦牛體形肥碩(圖5),常常和早期A型牦牛相伴出現(xiàn),兩者應(yīng)為同時(shí)期的產(chǎn)物,其時(shí)代上限應(yīng)在距今3000年左右;中期C型牦牛制作技法為劃鑿法或劃磨法,牦牛體格健壯,有些牦牛劃鑿出輪廓后,在腹部下裝飾有濃密的長(zhǎng)毛,牦牛形象生動(dòng)逼真,富有美感(圖6),有些牦牛僅劃磨出輪廓,但牛身腹部可見一箭頭(圖7),似與狩獵巫術(shù)相關(guān),結(jié)合與C型中期牦牛相伴出現(xiàn)的鹿巖畫來(lái)看,此時(shí)的鹿形象已不再是渦旋紋式的鹿,雖僅刻出鹿的輪廓,但又較晚期輪廓式樸素風(fēng)格的鹿富有動(dòng)態(tài)美。因此,我們推測(cè)中期C型牦牛巖畫介于C型早晚兩期之間;晚期C型牦牛制作技法亦為劃鑿法或劃磨法,只是刻畫的牦牛身軀瘦長(zhǎng),尾巴下垂,多為行走狀,牦牛形象簡(jiǎn)單素樸(圖8)。在此階段,牦牛巖畫的數(shù)量增多,和牦牛組合出現(xiàn)的動(dòng)物有馬、鹿、羊等,而且人的坐騎主要是馬,幾乎不見人騎牦牛的現(xiàn)象,和其相伴出現(xiàn)的鹿巖畫與西藏巖畫中“樸素風(fēng)格”的鹿形象相似[11]。因此,我們認(rèn)為晚期C型牦牛巖畫出現(xiàn)的時(shí)代大致在距今2200年至2000年間。與此同時(shí),晚期A型牦牛仍然存在。
3 總結(jié)
目前我國(guó)的巖畫研究往往只能做到圖像分析、年代考證,對(duì)藝術(shù)風(fēng)格的研究和分析很少[12]。本文嘗試著對(duì)玉樹通天河流域的牦牛巖畫進(jìn)行風(fēng)格研究,并與鄰近同屬青藏高原巖畫系統(tǒng)的同時(shí)期西藏巖畫進(jìn)行對(duì)比分析,通過(guò)我們的研究,本文將通天河流域牦牛巖畫分為三種風(fēng)格類型:A型剪影式、B型渦旋紋式、C型輪廓式,A型又可分為早、晚兩期,C型可分為早、中、晚三期。
剪影式牦牛與輪廓式牦牛巖畫貫穿通天河流域巖畫始終,是通天河流域巖畫的本土風(fēng)格類型。早期剪影式牦牛與早期輪廓式牦牛出現(xiàn)的時(shí)代約為距今3000年左右的青銅時(shí)代,晚期剪影式牦牛與晚期輪廓式牦牛并存,出現(xiàn)的時(shí)代約為距今2200年至2000年間。此外,中期輪廓式牦牛的時(shí)間介于早晚兩期輪廓式牦牛之間。渦旋紋式牦牛是通天河流域巖畫對(duì)外來(lái)文化的內(nèi)化,其出現(xiàn)的時(shí)間為距今2500年左右。
參考文獻(xiàn)
[1]尼瑪江才.玉樹巖畫[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418,490.
[2][6]王永軍,孫曉勇.玉樹通天河流域巖畫的多樣性風(fēng)格研究[J].青海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39(3):75.
[3]姚軍,楊博輝等.中國(guó)野牦牛棲息地環(huán)境及種群行為分析[J].草業(yè)學(xué)報(bào),2006,15(2):124.
[4]喬虹.青海高原動(dòng)物巖畫初探[J].青海民族研究,2013(3):171.
[5]黃亞琪.牦牛巖畫與民族文化的融合[J].內(nèi)蒙古社會(huì)科學(xué),2014,35(1):144-147.
[7]湯惠生,張文華.青海巖畫[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1:182-184.
[8]湯惠生,高志偉.青海高原巖畫年代分析[J].青海社會(huì)科學(xué),1996(1):81-82.
[9]張亞莎.西藏美術(shù)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2006:45.
[10]張亞莎.西藏的巖畫[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79.
[11]張亞莎.西藏美術(shù)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2006:206.
[12]陳兆復(fù).西藏的巖畫(序)(張亞莎著)[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4.
◆資訊◆
吉林長(zhǎng)山遺址發(fā)現(xiàn)新石器時(shí)代一座近百平方米房址
考古專家近日公布了吉林長(zhǎng)山遺址近兩年的發(fā)掘成果,在遺址內(nèi)共發(fā)現(xiàn)20余座房址和大量墓葬、灰溝等遺跡,其中一座房址的面積達(dá)到近百平方米。專家表示,同時(shí)發(fā)現(xiàn)如此大量且面積較大的房址,將有助于更好地揭示古代東遼河流域的歷史面貌。在2017年秋季進(jìn)行的發(fā)掘中,考古人員在長(zhǎng)山遺址共發(fā)現(xiàn)23座房址和10座墓葬,還發(fā)現(xiàn)了299個(gè)灰坑和10條灰溝,遺跡年代主要分為新石器時(shí)代、青銅時(shí)代和遼金時(shí)期。
在編號(hào)為F001的新石器時(shí)代房址中,考古人員測(cè)量該房屋面積達(dá)到近百平方米,是所有房址中面積最大、房?jī)?nèi)遺跡發(fā)現(xiàn)最多、堆積中包含物最為豐富的房址。在該房址中,考古人員發(fā)現(xiàn)了大量陶片、動(dòng)物骨骼、石器、骨器、可復(fù)原陶器、玉器以及陶塑人像,房址內(nèi)還發(fā)現(xiàn)了18個(gè)灰坑和8個(gè)灶等遺跡。對(duì)于這座“家底”如此豐厚的房址,方啟表示,面積達(dá)到近百平方米的房址在新石器時(shí)代并不多見,在同一房址內(nèi)發(fā)現(xiàn)如此豐富的遺物和遺跡,在該地區(qū)考古發(fā)掘中也實(shí)屬難得。“從房址的結(jié)構(gòu)、出土的文物等分析,推測(cè)這座房址是幾代人長(zhǎng)期居住并使用的房址,”方啟說(shuō)。
除了“祖?zhèn)鳌钡摹鞍倜状笳保脊湃藛T還在發(fā)掘區(qū)域內(nèi)發(fā)現(xiàn)了面積不等的20余座房址,每座房址的推測(cè)使用功能也不盡相同。“在一個(gè)遺址內(nèi)發(fā)現(xiàn)20余座房址,這對(duì)于東遼河流域考古具有重要意義,”方啟說(shuō)。通過(guò)比較房址的形制、房?jī)?nèi)遺跡及包含物等情況,連同發(fā)現(xiàn)的灰坑、灰溝和墓葬等遺跡,有利于了解古代東遼河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形態(tài)、環(huán)境演變以及人類生活環(huán)境、人地關(guān)系演變等內(nèi)容,為探討東遼河流域與周鄰地區(qū)的文化互動(dòng)關(guān)系提供了新的材料。(來(lái)源:新華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