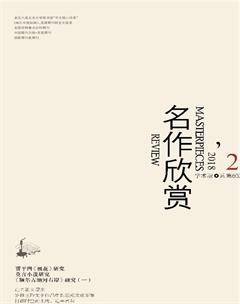元上京紀行詩的繁榮與多元文化的融合
劉揚
摘 要: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元代文學的重要特色。元代文壇,少數民族文士大量涌現,他們有著四海為家的民族性格,所作上京紀行詩,多為親自游歷,有感而發。且詩風多質樸自然、清麗喜人。上京紀行詩的繁榮有特殊的政治原因,元代海宇混一,華夷一體的背景下少數民族詩人群體與漢族文人群體共同促進了元上京紀行詩的繁榮,游牧文明、草原文明在詩歌中得以盡情展示,多民族文人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元代的詩壇。
關鍵詞:上京紀行詩 少數民族文人 多元文化
上京又名上都、灤京。蒙古統治者建立元朝后定都大都(今北京),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在開平繼位,中統四年(1263)下令將他的藩府開平府升為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正藍旗)成為元朝的陪都。此后元朝開始實行兩都巡幸制度,每年陰歷二月,皇帝都要帶領文武百官、妃嬪公主等來到上都,避暑及處理政事,到八、九月間再回歸大都。其中跟隨皇帝巡幸的侍從文人多是在翰林院、國子監任職的清要大臣,公務之余,這些文人們吟詠詩歌,在上都進行著各種文學活動。可以說,朝中的文臣們幾乎都參與了上京紀行詩的創作,這也是這些館閣文人的必修課。上都的文學活動與元朝的命運相始終,歷時百年之久,成為一種中國歷史上特殊的文學現象,上都作為一個文學中心,又由于其政治中心的地位所形成的文學觀念、風氣、思想對元代文學都有很重要的影響。此外,每年聚集在上都的文人群體數量之大、層次之高,構成多元,充分體現了元代文化多元的特征,也是上都文學能夠持續百年之久的必要條件。
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元朝,海宇混一,文化多元,種族繁雜,促成了中國歷史上華夷一體的局面,元代的文壇,少數民族詩人大量出現,并且與漢族文人交往密切,相互融合,形成了多民族的文化圈子。據統計,元代有作品流傳至今的蒙古詩人有二十余人,色目詩人約一百人。雖然,并非所有這些少數民族文人都參與創作了上京紀行詩,但上京紀行詩對他們的影響一定是有的。他們自身的民族性格、心理、審美情趣多少對當時的詩歌創作產生影響,正是這些少數民族詩人與漢族詩人共同促成了元代詩壇多元文化交融的局面。
一、文人群體多元,胡漢一家
巡幸上都是元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大事,對元代的詩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兩都巡幸一般需要七八個月左右,時間相當長,參與巡幸的各級官吏,目睹了巡幸的巨大規模、隆重的儀式,沿途的山川景物,感由心生用紀行詩的形式記載下了詩人們獨特的感受,從而促成了元代上京紀行詩的大繁榮。據《元詩選》《元詩選癸集》《元詩選補遺》記載,共收錄上京紀行詩497首,涉及50位詩人。其實這只是上京紀行詩的一部分,無論是詩人還是作品都有很大的增補空間。據當代學者統計,上京紀行詩共有973首,詩人58位,當然這也不能涵蓋所有作家作品,仍有增補空間。參與上京紀行詩創作的詩人大致可分為幾類,一類是館閣文臣,還有大量的隱逸之士、遺賢、尋找機會的人來往于上京,再者就是一些宗教人士。文臣必須要隨駕至上京辦公,其中隨幸的文臣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漢族文人,如翰林國史院的官員袁桷,曾四次扈從至上都,作品保存在開平四集中,共227首;此外虞集、周伯琦、貢師泰、王士熙等人也多次陪駕隨行,一睹異域景觀,領略草原風貌,從而激發了文人們的創作靈感,給后世留下了大量的上京紀行詩;還有郝經、王惲、張養浩、柳貫、王沂、黃 、陳孚、柯九思、張翥、胡助、楊允孚等人都有上京紀行詩留傳,多收入在各自的別集和《元詩選》《永樂大典》中。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一些頗有聲望的少數民族詩人,如薩都剌、馬祖常、 賢等人的上京紀行詩的創作。在元代,游牧文化、農耕文化、商業文化齊聚中土。游牧文化重遷徙、流動性強,少數民族詩人大多一生游歷四方,詩歌中洋溢著一種大元一統、四海為家的豪邁之情,給元代詩壇帶來了明顯的異質特色。如西域詩人馬祖常(1279—1338),字伯庸,號石田,靜州天山人,他一生宦游南北,既出使塞外,也曾寓居江南。“如今天子皇威遠,大積金山烽燧鮮。卻將此地建陪京,灤水回環抱山轉。萬井喧闐車戛輪,翠華歲歲修時巡。親王覲圭荊玉盡,侍臣朝紱螭珠新。高昌句麗子入學,交趾蠻官貢麟角。”(馬祖常《北歌行》)這首詩即是馬祖常陪皇巡幸上都之作,詩中充滿著對元朝一統天下的贊頌。不僅馬祖常如此, 賢的《塞上曲》五首,其一表現的是北方民族夜獵的場面,歡快豪情,諸人騎馬踏月吹笳而歸;其二表現游牧部落遷徙場面,氈車雜沓,大雪天氣涉過灤河;其三寫的是一個頭挽雙鬟的小姑娘愛美插花的意態;其四描寫草原人民踏歌狂舞、盡醉至晚的豪放場面;其五寫塞上風景,把人與自然的和諧展現得淋漓盡致。薩都剌的《上京即事五首》,描寫塞外風情,充滿了“歸人”的愜意。游牧民族轉徙隨時,車馬為家,常表現出對新異風光的熱愛。元代少數民族詩人群體創作的上京紀行詩,多為親自游歷,有感而發。他們本身受中原文化影響較深,但在詩風上仍保留了游牧民族豪情奔放的氣質。在風格上,不同于唐代邊塞詩的雄奇壯偉,也不同于清代邊塞詩的幽憤凝重,而是多質樸自然、清麗喜人。
薩都剌,字天錫,號直齋,是元代文壇大家,一生四處經商、為官。遍游“荊、楚、燕、趙、閩、粵、吳”。 賢,字易之,自幼生長在江南,少年時北上大都學習,曾隨駕上都,至正二十四年(1364)受朝廷之命祭祀南鎮、南岳、南海到達福建一帶。民族性格是這些少數民族詩人四處游歷的重要原因,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也使他們的詩歌更富有詩情。他們的北上南下一方面擴大了傳統邊塞、山水詩歌的范圍,另一方面也促進了文化的交融,豐富了元代詩壇。
此外,元代宗教人士也多有上京紀行之作,元代統治者對各派宗教基本上采取了保護政策。忽必烈重視佛教,特別是喇嘛教,上都佛教寺院眾多,著名的有華嚴寺、乾元寺。在隨皇巡幸的宗教界人士中,喇嘛教僧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宗教如伊斯蘭教、基督教的人士也有不少隨行上京,各教中留下上京紀行詩最多的是道教。自從道教領袖丘處機在成吉思汗時期應召到達西域覲見,與元帝建立了密切的關系,自此,元皇巡幸上京,也多有道士扈從。從留傳下來的上京紀行詩中可以看到上都有名的道觀有長春宮、太一宮、壽寧宮等。元代大詩人馬臻就是一名道士,他的《大德辛丑五月十六日灤都棕殿朝見僅賦絕句三首》其一:
清曉傳宣入殿門,蕭韶九奏進金樽。
教坊齊扮群仙會,知是天師朝至尊。
“大德辛丑”是元世祖之孫成宗大德五年(1031),這一年馬臻曾隨江西龍虎山張天師,朝見成宗鐵穆耳于上都多倫,詩中“教坊齊扮群仙會”的話,乃指當時內宴時演劇的情形。這些道士在上都期間與文人相互唱和,留下了大量當時文人交往的詩篇。如袁桷的《次韻李齊卿呈閑間嗣師》《贈李道士》等。
元上都宗教各個派別的存在、宗教與朝廷的密切關系、宗教人士的活躍狀況都體現出宗教在上都得了充分的發展,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元代是具有多元、開放、融合的文化特點。
二、歌頌皇元一統、描繪上京習俗、彰顯大元氣象
在中國歷史上,元代又是一個結束中國長期分裂,終成一統的龐大帝國,疆域之遼闊、草原風情之特別,文人的精神氣質也會產生與兩宋文人不同的變化。這使上都的文學作品呈現出了明顯的草原文化氣質。既不同于唐宋的邊塞、山水文學,也不同于傳統的中原文學,而是一種新異的文學,是一種具有草原文化特色的具有宏闊視野,真率自然、剛健質樸的新的文學審美特征,是一種大元氣象的彰顯。
這類詩歌在館閣文人中體現得最為突出。如周伯琦《次韻王師魯待制史院題壁》:
大安御閣執 亭,華闕中天壯上京。
虹繞金 晴浪細,龍蟠粉堞翠岡平。
眾星拱北乾坤大,萬國朝元日月明。
分署玉堂清似水,簫韶時聽鳳凰聲。
“萬里車書來上國,太平弓矢護青山。”(楊允孚《灤京雜詠》)“今日隨龍看云氣,八荒同宇正熙然。”(柳貫《灤水秋風詞三首》之一)這類詩歌多是歌功頌德之作,展現了文人對元朝這個少數民族統治下的政權的認可。上京紀行詩中還有一類是表現元朝游獵、宴飲文化的作品,這類作品極具蒙古特色,在中國詩歌史上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充分展現游牧民族的生活習俗,豐富了詩歌的內容。其文獻價值能與史書相關記載印證,做到詩史互證。對于草原文化,王惲說:“國朝大事,曰征伐,曰 狩,曰宴饗,三者而已。”這道出了蒙古統治者來上都的重要原因之一。馬背上民族的子孫雖已定都北京,實行漢法,但不能忘記和離開草原。元代皇帝在上京狩獵的地方是東、西涼亭,也是兩座行宮,西涼亭即察罕腦兒行宮,在蒙古語中指“白海子”故又稱為白海行宮。宋本《上京雜詩》之十六:“鷹房晚奏駕鵝過,清曉鑾輿出禁廷。三百海青千騎馬,用時隨扈向涼陘。”白海湖在今內蒙古沽源縣北數里處,元朝時曾在這里設有鷹房,養鷹以備圍獵。元末詩人張翥在《上都從駕幸東涼亭》中記載了元帝幸東涼亭游獵之事:“鶴禁煙華紫,龍崗草色青。羽林移曉仗,法駕幸涼亭。”還有元代詩人楊允孚的詩:“東涼亭下水溶溶,敕賜游船兩兩紅。回紇舞時杯在手,玉奴歸去馬嘶風。”虞集《王朋梅東涼亭圖》:“灤水東流紫霧開,千門萬戶起崔嵬。坡陀草色如波浪,長是鑾輿六月來。”游獵之風是少數民族展現其民族性格的一種主要方式,漢族文人通過詩歌再現了草原文化。
除狩獵外,宴饗也是元帝在上都的一項重要活動。宴會主要有“詐馬宴”和“馬奶子宴”,詐馬宴又稱質孫宴,“質孫”在蒙古語中指“顏色”“毛色”等義。指皇帝賜給宗親大臣們清一色的質孫服而得名,質孫宴源于窩闊臺時期選汗大會,同時也是聯結諸王藩戚的一種方式。一般宴會選在六月的吉日進行。元人詠詐馬宴的詩篇很多,如貢師泰《上都詐馬大宴五首》其一:“棕櫚別殿擁仙曹,寶蓋沉沉御座高。丹鳳銜珠裝藥裊,玉龍蟠甕注葡萄。百年典禮威儀盛,一代衣冠意氣豪。中使傳宣卷珠箔,日華偏照郁金袍。”其規模之巨大,形式之隆重,場面之壯觀足以令觀者嘆止。楊允孚《灤京雜詠》中記載:“千官萬騎到山椒,個個金鞍雉尾高。下馬一齊催入宴,玉闌干外換宮袍。”(自注:“每年六月三日詐馬宴席,所以喻其盛事也。千官以雉尾飾馬入宴。”)這是說官員們將自己的馬盛裝打扮來參加宴會,換上質孫服方才入宴席。在宴會開始后還會進行“角 ”和“歌舞”等表演。如鄭彥昭《上京行幸詞》之五:“紅云靄靄護棕毛,紫鳳翩翩下彩條。武士承宣呈角 ,近臣侍宴賜珠袍。”王沂《上京十首》之九:“黃須年少羽林郎,宮錦纏腰角 裝。得雋每蒙天一笑,歸來騶從亦輝光。”這兩首詩詠角 ,就是蒙古的摔跤,表現蒙元民族的娛樂競技活動。蒙古族還是一個熱愛音樂舞蹈的民族,在上京的重大活動中都少不了音樂歌舞的表演。楊允孚《灤京雜詠》:“儀鳳伶官樂既成,仙風吹送下蓬瀛。花冠簇簇停歌舞,獨喜簫韶奏太平。”薩都剌《上京雜詠五首》之三:“涼殿參差翡翠光,朱衣華帽宴親王。紅簾高卷香風起,十六天魔舞袖長。”詩中提到的天魔舞是元朝著名的宮廷舞蹈,由十六名主要舞者,頭戴象牙佛冠,垂發數辮,執樂器,隨樂翩翩起舞,極具少數民族之風情。
除了游獵及宴饗外,上京紀行詩中還記載了元廷祭天、祭祖等重要活動。元皇每年的六月或七月上旬,會在上都進行祭天和祭祖活動,周伯琦《立秋日書事五首》:“龍衣遵質樸,馬酒薦馨香。望祭園林邈,追崇廟 光。艱難思創業,萬葉祚無疆。”(自注:國朝歲以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與后素服望祭北方陵園,奠馬酒,執事者皆世臣子弟。是日擇日南行。)由此可以看出祭祖是元廷在上都的最后一項重要活動,事后就會擇日南行回歸大都。
三、研究上京紀行詩的價值
上京紀行詩的產生是伴隨著元代政治活動而逐漸在文人群體中出現的,它反映的又不僅僅是帝王生活的實錄,詩人們吟詠的對象上都,由于政治地位、地域、風俗的特殊性,迅速成為元人詩歌創作的一大興奮點,參與文人之多,持續時間之久,與元朝命運相如終,體現了元王朝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典型特征。首先以蒙古族為主體的元上都文化是一個開放的文化體系,具有兼容并包的特點。
在宋金對峙時代,“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詩歌的吟詠對象狹窄,氣格卑弱。到了元代,海宇混一,詩人陳孚在《恒州》詩中放言:“躍馬長城外,方知天地寬。”中原及江南的漢族文人初到少數民族聚集的邊疆地區,總會被獨特的自然風光、風物異俗所吸引,創作大量的詩篇,上京紀行詩恰好應運而生。如果說元代與宋末相比較對文人詩歌創作改變最大還是氣度方面。一般認為元代詩歌的特點是“宗唐得古”。詩至于唐宋,無論體裁、表達主題都臻于完備,宋詩重視詩法,以議論、才學、文字為詩,表意之深度實為幽眇難測。元人以“復古”改變宋詩之弊,元人認為“唐詩主性情,故于《風》《雅》為猶近,宋詩主議論,則其去《風》《雅》遠矣”,基于復古理論,元人自詡本朝之詩“能得《風》《雅》之正聲,以一掃宋人之積弊”。在元詩重視《風》《雅》正聲方面,之所以能如此自信,在于他們認為本朝具有“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的優勢。元人常自比于漢唐,實則元與漢唐相比疆域更加遼闊,“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疆域的遼闊帶給文人們的是開闊的胸襟及詩歌中的雄渾之氣。在上京紀行詩中我們可以看到“江山人物之形狀,殊產異俗之瑰怪”,“莫不窮形盡相、賦詠于詩”。在元代少數民族詩人群體,他們有著不同于漢人的文化基因,自然崇拜、萬物有靈,對大自然有著強烈且深厚的感情,顯示了少數民族詩人的特色,豐富了中國山水、邊塞詩歌的創作。如高克恭的《過信州》:“二千里地佳山水,無數海棠官道傍。風送落紅攙馬過,春風更比路人忙。”這是元代特有的現象,自元以后,再難繼續。
縱觀中華民族的發展過程,文學的發展是多民族共同創作、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過程,在元代大量少數民族詩人出現,在此之前游牧文化、草原文明還從未在詩歌中得到如此充分的展示,尤其是還有大量漢族文人參與其中,使草原文明一時成為吟誦的焦點,也恰恰證實了元代開放的政策,多元文化融合的事實。
參考文獻:
[1] 顧嗣立,席世臣.元詩選癸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1.
[2] 錢熙彥.元詩選補遺[M].北京:中華書局,2002.
[3] 顧嗣立.元詩選[M].北京:中華書局,1987.
[4] 柳貫.上京紀行詩[M].民國19年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影印本.
[5] 楊允孚.灤京雜詠[M].《知不足齋叢書》本.
[6] 周伯琦.扈從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 楊鐮.元詩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8] 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作 者:劉 揚,碩士,中北大學講師,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
編 輯: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