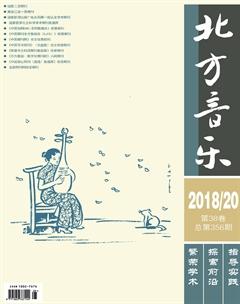初探地方民族民間音樂的分解與重鑄
【摘 要】地方民族民間音樂是由當地的普通民眾在勞動生產中創造的,與文化、民族風情相結合的,融入了地方獨有的精神內涵的音樂作品。地方民族民間音樂的傳承及其創新一直是國家文化發展的重點項目,大量的藝術家投身于對民族民間音樂文化的發掘、采集和再創作中。文章借鑒《天門狐仙·新劉海砍樵》成功范例,探討地方民族民間音樂繼承發展的新形式,從音樂劇的分析出發,分析“分解”與“重鑄”的具體方式,進一步證實了“分解”與“重鑄”是地方民族民間音樂的真實出路。
【關鍵詞】民族民間音樂;分解;重鑄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地方民族民間音樂是由當地的普通民眾在勞動生產中創造的,與文化、民族風情相結合的,融入了自己地方獨有精神內涵的音樂作品。面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民族民間音樂文化發掘力度不足、創新能力不夠的現狀亟待解決。
2017年10月,筆者至湖南、貴州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察。考察過程中,筆者有幸欣賞到音樂劇《天門狐仙·新劉海砍樵》的演出,并重點關注該作品中以湖南民族民間音樂為創新點的地方民族民間音樂新繼承形式的表達。針對地方民族民間音樂未來的發展方向,借鑒《天門狐仙·新劉海砍樵》的成功范例,筆者進行了深刻的思考。
一、音樂劇《天門狐仙·新劉海砍樵》分析
音樂劇《天門狐仙·新劉海砍樵》由蜚聲海內外的“音樂奇才”譚盾先生擔任音樂總監,青年作曲家張驍執筆作曲,中國著名山水實景演出創始人梅帥元擔綱總導演及策劃。是世界上第一部以高山峻嶺、天門洞為真實舞臺背景,以山間溪流峽谷和蜿蜒的山路為表演舞臺實景結合的劇目。它的故事主線來源于中國湖南民間傳說《劉海砍樵》,用音樂結合燈光、實景和舞美,將一個綺麗夢幻的神話故事娓娓道來。
演出的舞臺搭建于張家界天門山的下部峽谷中,坐在觀眾席處,正好可以仰視那“洞開的天門”。音樂劇運用現代最精尖的科技,將音樂、舞美、魔術等各種藝術形式巧妙地結合起來,為觀眾呈現了一場幻妙絕倫的民族音樂劇,尤其是兩個斷橋漸漸結合,百人舞蹈的宏大場面,使觀眾在贊嘆博大精深的民族音樂文化的同時,流連忘返于該劇與現代科技的巧妙結合。
桑植民歌在從其產生至近現代的生存狀態中,是一種近乎自然的狀態,表現了當代桑植人的精神內涵和他們遙遠的歷史,是極具研究價值的。它指引著桑植人民的生活方向和價值觀的確立,民歌此時的社會功效顯而易見,同時與當今現代社會也并沒有主次之分,這種文化氛圍在當今社會是難能可貴的。只有將民族民間音樂各類元素提取出來,進行深層次的加工創造,才是民族民間音樂最應該有的發展方向。地方民族民間音樂的“分解”與“重鑄”的真實意義,是在地方民族民間音樂的基礎上,將真正的音樂元素提取出來,用地方民間文化元素進行整合,完美地結合于優秀的藝術作品之中,才是真正意義上完成了“分解”和“重鑄”。
二、地方民族民間音樂的“分解”和“重鑄”
民族民間音樂根植于中國的社會文化生活中,是隨著中國的歷史不斷演進的,它代表了中國民族民間的風情和人民基于生活最樸素真實的體現,是大眾喜聞樂見的生活表達方式,也是眾多藝術家創作的最基礎的來源。隨著社會生活不斷豐富,社會財富的不斷積累,使得大量寶貴的地方性民族民間音樂難以保留原來的面貌,或者幾近失傳,如何保護和進一步發掘成為了現當代我們面臨的課題。
(一)民族民間音樂的“分解”
即使將現存的所有民族民間音樂只作為收藏整理,其職能就從體現社會生活改變成為收藏,只是能在博物館或者一些不為人知的書籍中留存,這就失去了地方民族民間音樂自我內涵中所應有的社會功效。民族民間音樂不能立足于社會中發揮其職能,那么其價值就有待商榷了。筆者了解到,桑植地區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該地區極為豐富的民歌資源。封閉的環境造就了桑植地區民族民間音樂保存的完整性,“巫楚”文化特色明顯,以歌帶語,以歌傳情的特點使得該地區音樂文化氛圍濃厚。悠長宛轉、高亢嘹亮的歌聲翻山越嶺,橫跨溪河,久久回蕩在天地間。“成禮兮會鼓,春蘭兮秋菊,傳芭兮代舞,長無絕兮終古。”屈原的《九歌》記載了楚人以歌(舞)唱節、以歌為媒的山歌文化以及巫文化。巫在遠古時代是文明的傳承者,在古老而多元的楚巫祀典活動中,巫者生生不息地傳承著桑植先民對自然、圖騰、鬼魂和祖先的崇拜。至今,在桑植偏遠的大山角落里,一些老土司為亡人超度亡魂的歌聲中,仍延續著神奇荒誕、豐富瑰麗、奔放不羈的古老歌謠舞曲。
(二)民族民間音樂的“重鑄”
民族民間音樂的“分解”是現實可行的。民族民間音樂必須立足于社會中,從社會中來,在經過藝術的加工之后回到社會中去,這才是實現了民族民間音樂的再社會化,是民族民間音樂發展的最終出路。如果說“分解”是萃取精華的話,那么“重鑄”就是精華再造。而獨具魅力的地方民族民間音樂是整個“重鑄”藝術的靈魂所在。音樂劇中,對桑植民歌《棒棰棰捶在石頭上》《桑木扁擔軟溜溜》《馬桑樹兒搭燈臺》等原始狀態民歌的改編,使得這部音樂劇的“民族味”十足,這些民歌甚至從中提取出來作為單獨的演唱曲目。
桑植民歌的唱腔唱詞是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元素中的一朵奇葩,語氣詞的運用,使桑植民歌的口語感增強,加之曲風清晰,更使桑植民歌在《天門狐仙》的重鑄下更為朗朗上口。襯詞的運用,使民歌在烘托氣氛、揭示人物內心情感等方面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境界。如譜例中的“郎在高山我打一望啰喂”“情郎哥哥喂依呦唔”等,使該曲動聽且貼近生活,畫面的沖擊感增強。
地方民族民間音樂藝術是文化的體現,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是國家發展的軟實力,是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又一突破點。“分解與重鑄”才是民族民間音樂走向世界的最根本的因素。單一的藝術傳播形式已不能滿足在此背景下地方民族民間文化的存留方式,結合現代科技,用“分解”與“重鑄”的手段完善地方民族民間音樂的繼承和發展成為當今的必須借鑒的新形式。《天門狐仙》成功了,用民族的語言告訴世界,“民族的是世界的”。真正的“分解”與“重鑄”需要剝去地方民族民間音樂陳舊的外衣,用新的形式為其穿上符合社會潮流的時尚,以真實的民族民間情感,切身感悟最動情的地方民族民間音樂。
參考文獻
[1]李煥之.當代中國音樂[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2]洛秦.音樂與文化[M].北京:西泠印社出版社,2001.
[3]居其宏.當代音樂的批評話語[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 2002.
[4]曾遂今.中國大眾音樂——大眾音樂文化的社會歷史連接與傳播[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
[5]曾遂今.音樂社會學[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4.
[6]霍步剛.國外文化產業發展比較研究[D].大連:東北財經大學,2009.
[7]鄭英杰.湘西文化的現代轉型及創新[J].株洲工學院學報,2005.
[8]楊民康.論民族音樂學雙視角文化立場的歷史演變和發展趨向(上)[J].音樂藝術,2003.
[9]伍益中.文化與旅游的完美結合——評實景音樂劇《天門狐仙·新劉海砍樵》[J].藝海,2011.
作者簡介:張佳碩(1993—),男,河北北方學院學科教學(音樂)碩士研究生,師從于喬春霞教授。2016年畢業于河北北方學院,獲學士學位。2018年考入河北北方學院攻讀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