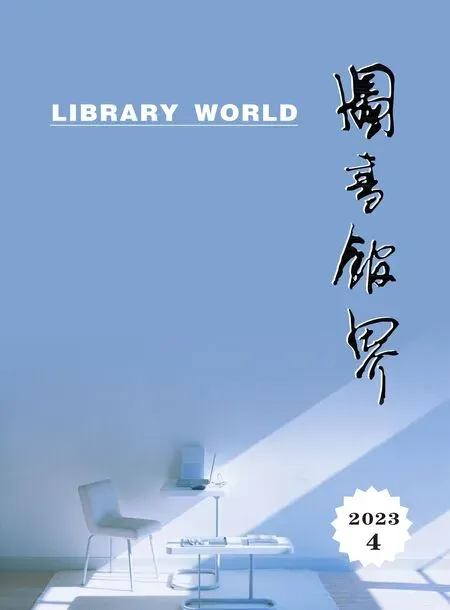地方紅色數字資源建設與服務推廣
——以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為例
梁曉嵐
(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廣西 南寧 530022)
1 引 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紅色資源是我們黨艱辛而輝煌奮斗歷程的見證,是最寶貴的精神財富。”“要用心用情用力保護好、管理好、運用好紅色資源。”[1]8《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規定,“公共圖書館應當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公共圖書館作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備社會教育職能,理應充分發揮資源收藏整理、知識服務的專業優勢,發掘好、運用好紅色資源,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在紅色資源中汲取精神滋養和前進力量,厚植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情感,不斷凝聚奮進力量。
2 概 念
紅色資源,是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所形成的具有歷史價值、教育意義、紀念意義的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2]。在我國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大地上,紅色資源星羅棋布,每一個歷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種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著中國共產黨走過的光輝歷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夢想和追求、情懷和擔當、犧牲和奉獻[1]4。這些紅色資源的地理區域、歷史時期、存在形式各不相同,具備獨特的地方特征,也具有相對獨特的歷史意義。本文所指地方紅色資源,即是指具備獨特地方特征的紅色資源。而將具備獨特地方特征的紅色物質資源或精神資源進行數字化加工并運用各種方式進行服務推廣,使之更符合現代社會人們的閱讀、觀賞習慣,得以在更廣泛的時空進行傳播,即是本文所指地方紅色數字資源建設與服務推廣的內容。
3 地方紅色數字資源建設與服務推廣的意義
3.1 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的時代需求
2021年2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通知》,就黨史學習教育作出部署安排。2022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推動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的意見》,指出推動中國共產黨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是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一項長期重要任務,要使學黨史、知黨史、用黨史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建設、利用地方紅色資源,挖掘獨具特征的地方黨史,再現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為國為民、艱苦奮斗、百折不撓、視死如歸的光輝事跡,對營造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氛圍,振奮民族精神,滿懷信心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具有重要意義。
3.2 助力地方文化傳承,發展繁榮地方經濟
地方紅色資源往往蘊含獨特的地方紅色文化,其中包含的各族人民為了共同的革命目標團結一致、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奮勇向前的精神,也是當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齊心協力發展社會經濟所必需的精神動力。通過建設和推廣地方紅色資源,再現波瀾壯闊的地方革命史、奮斗史,對于弘揚革命精神、宣傳地方紅色文化有著重要意義。同時,把紅色文化宣傳與當地革命舊址、遺跡、紀念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相結合,精心設計推出紅色旅游和紅色研學線路,可以增加就業機會,助推當地經濟的發展。
3.3 大眾教育的需要
當今國際環境復雜多變,我國意識形態安全面臨新的挑戰。紅色資源展現中國共產黨的夢想和追求、情懷和擔當、犧牲和奉獻,能使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和偉大成就,從而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而地方紅色資源,更貼近人民群眾的生活,更能以身邊榜樣的力量,培養人民群眾的家國情懷和民族認同感,對于在全社會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大有裨益。
3.4 資源共享的需要
由于中國革命的特殊性,紅色資源分布廣泛,且比較大量的紅色物質資源散落在較偏遠、交通不太便利的欠發達地區,想要一一實地瞻仰顯然不太現實。在互聯網時代,更多人傾向從網上獲取信息。對地方紅色資源進行數字化建設,并利用互聯網進行傳播,可以使地方紅色資源的傳播時間、空間和受眾的范圍都更加廣泛,還可以與其他地區的紅色資源互通有無,形成互補,豐富紅色資源體系。
4 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地方紅色數字資源建設與推廣的實踐
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以下簡稱“廣西圖書館”)于2021年建設《尺素丹心——廣西黨史故事》紅色數字資源,從廣西革命先輩的書簡入手,以5分鐘專題片的形式展示人物的革命經歷、英雄事跡、家國情懷,短小精悍、寓意深刻、觀賞性強。2022年,該數字資源獲得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自治區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舉辦的2022年自治區直屬機關“八桂先鋒”優秀作品(課件)微視頻類一等獎。
4.1 建設實踐
4.1.1 統籌規劃,分步驟建設。地方數字資源建設不能“東一榔頭,西一棒槌”,會容易導致地方數字資源徒有數量、深度欠缺、重點不突出、特色不明顯,難以形成獨特的地方數字資源體系,社會價值有限。應該進行長遠統籌,加強頂層設計,分步推進地方數字資源建設。廣西圖書館于2005年開始地方特色數字資源建設,圍繞展現地域文化特色、體現地方文化精神這個目標,已逐步形成由廣西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歷史、地理等6大板塊組成的結構框架,逐年分步驟補充各板塊的內容。在這個框架體系中,廣西歷史板塊內容相對較少,只建設了廣西民國及小部分民族歷史資源,中國共產黨廣西歷史(以下簡稱“廣西黨史”)尚未涉及。而中國共產黨在廣西的歷史是一部英勇奮斗的光輝篇章,右江農民運動、百色起義、龍州起義、湘江血戰在中國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黃日葵、韋拔群、黃彰等廣西革命先輩艱苦奮斗、百折不撓、不懼犧牲的精神,是激勵廣西各族人民不斷奮勇前行的力量源泉[3]。將廣西黨史從人物、情感、信仰的角度進行挖掘,既豐富了廣西革命英雄形象,又充實了廣西黨史內容;既是2021年中國共產黨黨史學習教育的有益實踐,也是向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大慶的獻禮,同時可為后續開展中國共產黨黨史資源建設積累經驗。
4.1.2 組建團隊,各流程把關。《尺素丹心——廣西黨史故事》以歷史文化專題片的形式呈現。專業的制作團隊,可以在尊重史實的前提下,使文案、畫面更富感染力,更能引起共鳴。廣西圖書館對廣西黨史數字資源的建設相當重視,邀請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的專家作為顧問,對專題片的意識形態以及史料進行把關。為保證專題片的呈現效果,邀請新聞及影視傳播藝術類正高級職稱專家擔任編導以及監制。廣西黨史故事人物的選取均通過聽取有關專家、學者意見和現場踩點予以確定。需要對人物進行采訪時,均嚴格篩選出鏡人物,同時對選入專題片成片的采訪內容進行審核把關,確認其專業性、權威性和真實性等。如此層層把控使專題片得以圓滿制作完成。
4.1.3 精心制作,增加吸引力。《尺素丹心——廣西黨史故事》紅色數字資源主要展現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先輩故事,距離現在已有多年,社會環境也與現在大不相同,如何激發讀者的觀看興趣并產生共鳴?首先,找準切入點。《尺素丹心——廣西黨史故事》以革命先輩的書信作為切入點。書信是人物情感最真實、最樸素的表達,其中敘述的親情、友情、愛情,古今相通。從書信的角度切入,從革命先輩的情感入手,娓娓道出革命先輩的革命經歷、品格風范,故事性強,容易引起讀者加深了解的興趣和情感共鳴。巧妙的切入點,是增加紅色數字資源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其次,突出閃光點。建設團隊選取廣西黨史中具有重要影響意義的革命先輩,包括中國第一位戴紅領巾的龍業鼐,廣西共產主義啟明星黃日葵等,通過查閱文獻資料,前往貴港、梧州、賀州、百色、桂林等多地實地走訪拍攝每一位革命先輩的故居、紀念館以及所在地黨史辦公室(研究室)等方式,搜集大量素材,挑選最能突出人物信仰、優秀品格的部分,精心制作專題片,務求角度獨特、畫面精美、內容翔實、情節感人。再次,把握時間點。為了符合現代讀者的閱讀觀賞習慣,把專題片的時長控制在5分鐘左右,短小精悍、以小見大,更利于專題片的傳播推廣。
4.2 服務推廣實踐
為提升《尺素丹心——廣西黨史故事》紅色數字資源使用率,廣西圖書館采取多平臺多頻次發布、線上線下結合推廣的方式對其進行宣傳與推介。
4.2.1 多媒體平臺宣傳。《尺素丹心——廣西黨史故事》除了制作專題片,還制作了一個100秒的宣傳片,宣傳片和專題片分別在廣西圖書館官方網站和官方微信公眾號、廣西機關黨建網、廣西廣播電視臺、學習強國App、南寧市人流量最大的地鐵1號線及2號線以及嗶哩嗶哩視頻網(www.bilibili.com)、廣西視聽App等平臺上多頻次、多時段播發,吸引各年齡段、各層次的人群關注,極大地擴大了資源的社會影響。多平臺聯動的傳播矩陣,拓寬了紅色資源的服務半徑,提升了地方紅色數字資源的媒體曝光度,讓網絡正能量傳播不斷疊加。
4.2.2 利用活動推廣。為了多角度宣傳推介《尺素丹心——廣西黨史故事》,廣西圖書館還結合重大節日舉辦線上互動活動,以增進讀者對廣西黨史的了解。2022年“七一”建黨節,廣西圖書館舉辦“歲月崢嶸應有憶”線上活動,列出專題片的資源地址,引導讀者觀看,并根據專題片的內容進行線上問答,同時設置《紅船啟航》等書籍為獎品。該活動有2 300多人次參加。今后,利用地方紅色資源開展的閱讀推廣活動,將成為廣西圖書館的常規活動。
4.2.3 與黨建工作融合。紅色資源是推進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堅定理想信念、增強黨性修養的生動教材。《尺素丹心——廣西黨史故事》由于選材獨特、故事性強、立意深遠,自2021年以來多個黨支部在開展主題黨日活動時組織黨員觀看該專題片。例如,2021年5月廣西電網公司開展“紅船精神 代代相傳”線上主題音樂黨課活動時,組織大家觀看《尺素丹心——廣西黨史故事》之分集《黃日葵》,活動中,主持人生動講述“紅船精神”的故事,還結合詩朗誦、音樂劇、紅色舞蹈表演等,重溫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共有3.7萬多人次觀看。該活動也在線下同時進行。《尺素丹心——廣西黨史故事》作為業務建設成果,能為黨建工作提供助力,這是黨建與業務融合的良好模式。可以預見,在今后的黨組織生活中,《尺素丹心——廣西黨史故事》紅色數字資源仍將發揮巨大作用。
5 關于地方紅色數字資源建設與推廣的思考
廣西圖書館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公共圖書館開展地方紅色數字資源建設和推廣的現狀,既有一定成果,也有不足:地方紅色資源建設主體大多是某地單個公共圖書館,很少與其他地區的相關單位聯合建設,導致資源內容不夠豐富,挖掘深度欠缺;當前建設的地方紅色數字資源,大部分為多媒體資源庫及專題片,形式較為單一,且由于數據形式、時長等原因,不適宜在新媒體推廣;推廣形式大多為線上展播、經典誦讀等傳統形式,創新性不夠強,讀者關注、參與的興趣不夠高。因此,我們需要對地方紅色數字資源的建設和推廣進行不斷完善,講好紅色故事,傳承紅色基因。
5.1 關于地方紅色數字資源建設的思考
5.1.1 加強統籌,共建共享。我國紅色資源分布較為分散,各地區的地方文化科研中心、黨史研究機構、圖書館、檔案局、博物館、革命紀念館等單位都收藏有一定的紅色資源,部分民間收藏者也藏有大批珍貴資料[4]091,革命舊址更是遍布全國各地。僅靠單個圖書館,想要對紅色資源進行比較完整地收集、深挖其內涵并進行數字化建設和推廣,顯然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難以支撐。所以,公共圖書館開展地方紅色數字資源建設,需要進一步加強統籌規劃,開展跨地區、跨行業的互助合作、共建共享。首先,要聯合地方紅色資源收藏、管理機構,盤點本地紅色資源的類型、數量、建設利用情況等,為后期開展建設打好基礎。其次,結合地方紅色資源建設利用情況以及圖書館的發展方針,統籌安排,制訂地方紅色資源建設規劃,有計劃分步建設,逐步豐富地方紅色資源體系。再次,建設資源時,要吸納有關收藏、管理單位作為聯合建設單位,做到素材共享、經驗共享、成果共享,以保障紅色資源素材的供給,保障建設成果的史實性、完整性。接著,建立統一的紅色數字資源揭示平臺,允許接入其他機構建設的紅色數字資源,把分散的紅色數字資源聚合起來,進一步實現地方紅色數字資源的一體化揭示和共建共享。規劃先行,科學統籌,分步建設,可以有條不紊、集中精力、保質保量地完成特定資源建設,進而逐步完善地方紅色數字資源體系,提高資源的研究價值和社會價值。各地區各機構團結協作,可以使資源素材、技術、經費等因素得到比較高效的利用,資源體系更為豐富,更有利于挖掘紅色資源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和革命精神。
5.1.2 專業團隊,保障質量。紅色資源的重要意義和珍貴價值,就在于其承載著黨的光輝歷史和優良傳統,并在當下持續發揮精神引領的作用。所以,紅色資源必須具備意識形態性、真實性,同時為了得到更好的傳播,還需要具備觀賞性。為了使建設的地方紅色數字資源具備這些屬性,公共圖書館需要一支責任心強、專業水平高的團隊。首先,需要黨史專家對資源的意識形態以及史料真實性方面作把控,這兩項工作不容有失。其次,需要耐心細致的素材收集人員,盡量完整、全面地收集資源建設涉及的文獻、文物收藏信息等材料,為資源建設夯實基礎。再次,需要專業的視頻編導人員,對龐雜的素材進行挑選、編排,使其節奏緊湊、情節感人。專業的團隊可以確保所建設的資源能夠提供正確的思想引領、精神激勵和文化支撐。
5.1.3 豐富資源,創新形式。當前,建設的地方紅色數字資源內容多為文獻、文物和人物故事,載體形式以圖片庫、多媒體資源庫和專題片為主,稍顯單一。可以根據不同年齡、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建設不同內容、不同形式的紅色數字資源。例如,老照片、老電影、回憶錄、紅色歌舞等比較容易引起老年讀者的共鳴;對于青年,歷史事件、舊址尋蹤類的內容比較有吸引力;少年兒童則比較偏愛英雄故事。要針對當代大多數讀者習慣網絡閱讀、碎片化閱讀、休閑式閱讀的特點,為紅色資源選擇契合的表現形式。音頻、口述史、微視頻、歌舞藝術等都可以納入地方紅色數字資源的形式范圍。內容豐富、形式多樣、雅俗共賞,才能把嚴肅的紅色題材資源做得有新意、有趣味,使每一位讀者都可以找到契合自己欣賞習慣的資源,愉悅地融入愛國主義教育的氛圍。
5.2 關于地方紅色數字資源服務推廣的思考
5.2.1 常態宣傳推廣,營造紅色氛圍。建設地方紅色數字資源的目的,是為了擴大紅色資源的宣傳和利用范圍,更好地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對紅色數字資源進行宣傳推廣不僅是建黨節、建軍節、國慶節這些重大節日期間的事情,而應該成為常態化的工作。公共圖書館要充分利用傳統平臺和新媒體平臺,常規性地開展紅色宣傳推廣活動,積極打造公共圖書館紅色教育基地,營造紅色教育氛圍,使社會公眾都能從黨的光輝歷史中汲取寶貴歷史經驗和精神力量,滋養浩然正氣,努力創造不負革命先輩期望、無愧于歷史和人民的新業績。
5.2.2 多元主體參與,創新推廣形式。目前,相比其他主題的閱讀推廣活動,公共圖書館開展的地方紅色數字資源主題活動較少。在有限的活動當中,多是由公共圖書館針對自行建設的資源自行策劃組織推廣活動,單打獨斗,社會影響力有限。要想擴大效果,需要與基層黨組織、各地圖書館、黨史研究機構、紅色場館、新聞媒體等形成合力。一方面,互相借鑒紅色資源的宣傳推廣經驗;另一方面,是把宣傳推廣活動在各地各機構鋪開,各機構可以結合自身的特色資源,完善細節,最后呈現主題相同、細節相異、各具風采的宣傳推廣活動,形成規模效應。例如,可以請黨校教授、黨史研究機構的專家等在不同地區結合不同機構的特色舉辦相關專題講座,以系列地方特色紅色講座的形式對地方紅色數字資源的內涵作進一步的探討;可以結合各圖書館館藏實體紅色文獻,結合各機構的工作特色舉辦閱讀分享會,讓讀者互相交流學習心得,通過思想的碰撞,獲得新的啟發;可以利用VR技術,讓地方紅色數字資源涉及的歷史事件和靜態革命文物“活起來”,使讀者“身”臨其境,沉浸體驗紅色革命的艱辛歷程;還可以開發成桌游等年輕人愛玩的游戲形式,讓讀者在游戲中培養紅色素養。形式多樣的活動,經過媒體的宣傳,可以促進經驗交流,在社會上營造紅色教育的氣氛。多元主體的參與,新穎多樣的形式,可以擴大地方紅色數字資源的服務范圍,提高其社會認可度和利用率。
5.2.3 優化紅色空間,黨建業務融合。當前已有部分圖書館在館舍內設置了紅色閱讀區、紅色文獻書架、紅色數字圖書館等紅色文化空間,或者將館外分館設置為紅色主題圖書館[4]089。但多是紅色元素單一的展陳,缺乏地方特色,難以吸引讀者駐足停留。在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的背景下,公共圖書館應該將紅色空間建設或優化納入圖書館空間再造的規劃當中。公共圖書館的紅色空間,在設計上應該融入地方紅色資源元素,突出地方特色;除了必要的紅色專題書刊陳列,還可將本地相關紅色革命事件、人物、場景圖片作為裝飾,烘托空間氛圍;設置查詢機、投影儀、VR眼鏡等電子設備,供讀者查閱地方紅色數字資源、觀看紅色視頻、沉浸體驗紅色場景等,地方紅色數字資源應與相關的館藏實體文獻互相指向;在紅色空間持續利用地方紅色資源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紅色文化教育、專題資源服務、學習閱讀研討等活動,將圖書館業務與黨建工作完美融合,并廣為宣傳,使其成為當地“紅色打卡地”[5]。
5.2.4 紅色研學旅游,助推地方經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可依據地方紅色數字資源涉及的革命舊址、紅色場館等,開發研學、旅游路線。將地方紅色數字資源與生態游、民俗游、研學游、鄉村游等深度融合,講好紅色故事;以紅色研學旅游為契機,打造全域旅游和生態康養示范區;以紅色研學旅游帶動周邊貧困區融合發展,讓農村變景點、民居變客棧、農產品變旅游商品等,把紅色人文景觀和綠色自然景觀、觀光游覽與接受革命傳統教育有機結合,助推地方經濟發展,推進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大眾化、常態化。
6 結 語
地方紅色數字資源的建設與推廣需久久為功。在加強地方紅色數字資源建設的同時,還需要別具匠心、與時俱進的宣傳推廣,將地方紅色數字資源與社會教育、經濟發展有機結合,是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開拓紅色江山更加美好的未來需要,也是地方紅色數字資源建設與推廣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機遇。愿社會各界聯合起來,共同挖掘、弘揚好紅色資源的精神內涵,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