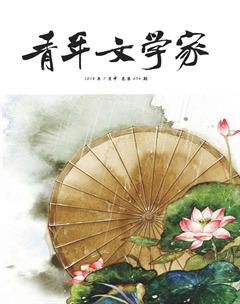《白鹿原》與《殺死一只知更鳥》的女性形象對比分析
郭小冬 韓榮 孟春月 胡榮華
摘 要:本文擬就《白鹿原》與《殺死一只知更鳥》兩部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進行對比分析,找出兩部作品在女性人物刻畫方面的異同,試圖找到分析這兩部經典作品的另一種途徑,揭示出體現在作品中深層的民族文化精神。
關鍵詞:《白鹿原》;《殺死一只知更鳥》;女性形象;傳統文化
作者簡介:郭小冬(1968-),女,浙江人,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外國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0-0-02
一、內容概要
《白鹿原》是當代中國作家陳忠實的代表作品。小說敘述了自辛亥革命以來至新中國成立這一歷史動蕩時期,發生在白鹿原上的社會生活變遷。故事描寫了以白嘉軒為族長的白鹿村,如何在天災人禍接連發生,時局動蕩不安、兵匪不斷的年代里,艱苦生存、辛勤勞動的故事;同時,在時代的大變革面前,如何彷徨不安、無所適從的困惑。作者以白鹿村為中心,創作了眾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反映了波瀾壯闊的時代變遷,是一部反映陜西關中鄉村文化的力作。
《殺死一只知更鳥》是美國女作家哈珀·李的作品。作品以美國南方小鎮梅科姆為中心,以斯庫特兄妹為視角,描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發生在這個小鎮里的故事。小說前半部分講述了阿瑟的故事,后半部分講述了黑人湯姆·魯賓遜的冤案。小說以阿瑟解救受白人痞子尤厄爾襲擊的斯庫特兄妹作為結局。小說對美國南方的舊傳統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對種族歧視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并把改變現狀的希望寄托在以斯庫特為代表的南方新一代身上。
這兩部作品都是以一個小村或小鎮為中心,深刻細膩地描繪了在這一區域內生活的人及發生的事,但通過這個窗口,讀者能感知到整個時代的氛圍,在各種矛盾沖突中,作品揭露出人物的性格、成長歷程,反映了深刻的社會問題,探究了人的本性,給予讀者以深刻的啟迪。
《白鹿原》與《殺死一只知更鳥》是在不同年代、由中美兩國作者分別創作的,但兩部作品因其塑造的美好而不幸的女性形象和反映的深刻社會生活而受到各國人民的喜愛,以白靈和斯庫特為代表的新女性形象也成為文學的經典形象,為后世所銘記。
本文擬就兩部作品中的兩對主要女性形象進行對比分析,找出兩部作品在女性人物刻畫方面的異同,試圖找到分析這兩部經典作品的另一種途徑,揭示出體現在作品中深層的民族文化精神。
二、女性形象的對比分析
1. 女性群像的對比分析
在《白鹿原》中,陳忠實以滿懷同情的筆觸,描寫了一批傳統女性生存的悲劇故事,她們生活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封建鄉村社會,她們的自我個性化的生存方式被集體拒絕,而只有以男性文化意義的規范為基礎的生存方式才能被接受。她們是男人傳宗接代的工具,女人的貞潔被看得高于一切,一旦失節就會受到所有人的唾棄,等待她們的就只有死亡。在這樣的社會,女性沒有婚姻自由,一切由父母包辦,她們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她們無權像男性一樣接受良好的教育,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綱常把她們牢牢的束縛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家庭生活中,她們燦爛如花的生命常常以悲劇告終。如田小娥、小翠、冷秋月等女性。還有像白孝文媳婦大姐這樣無我奉獻、辛勤持家的女性,卻被荒唐的丈夫拋棄后餓死。即便如白嘉軒的母親白趙氏,她是男權社會三從四德的賢淑女人的典型,她的個性早已被男權文化所置換了,這正是她個人的悲劇所在。
《殺死一只知更鳥》中也刻畫了許多女性形象,如莫迪小姐、亞歷山德拉姑媽及參加她的傳道會的小鎮上的白人女士們、杜博斯太太、馬耶拉、海倫、卡波妮等等。除莫迪小姐外,小鎮上的白人女士們持一種狹隘的宗教觀念,這種觀念使她們的信仰成為生活的桎梏。(常何 2012:91-92)她們對黑人抱有偏見,她們的言語代表了小鎮白人家庭的所思所想,是小鎮人們生活的窗口。小鎮彌漫著濃厚的種族歧視氛圍,生活中處處體現著種族隔離,白人和黑人有各自的教堂,黑人孩子無權接受教育,他們的生活區也遠離白人區,生活在小鎮的邊緣。
2. 白靈與斯科特——文化的叛逆者
白靈出生在擁有幾千年傳統文化的中國關中的一個鄉村,童年的她是幸運的,由于父親的寵愛,她得以避免裹腳,還是學堂里唯一一個女娃,但是當她想和西安城姨夫皮匠家的兩個姐姐一樣上城里的新式學堂時,卻遭到父親拒絕。白靈失蹤了,原來她自己跑到西安城上新學堂去了,說明她強烈的求知欲和想獨立主宰自己命運的強烈渴望。
在從清末到新中國建立這一歷史時期里,傳統文化與新文化發生著激烈的交融與碰撞,接受了許多進步思想的她,在西安城被軍閥圍困期間,積極投身于文藝演出隊,到守城的革命軍將士們中宣傳鼓動,之后她又參加了推翻發對國名革命的滋水縣政府的游行,這時她的反封建的思想已經確立了起來。
當父親給她定親時,她偷偷寫了退婚字條,毅然從家中逃跑,反映了她反對封建包辦婚姻、主張婚姻自主的思想。在兆鵬的影響下,她在白色恐怖的鍛煉中逐步從一個不諳世事的愛國學生成長為一個有堅定信仰的共產黨人。她相信“共產主義就是那只白鹿”(陳忠實,2001:417)。有著同樣信仰的兩個人,在患難與共中,他們的感情也日益加深,勇敢追求自己所愛的白靈首先向鹿兆鵬表明要與他做真夫妻的愿望,雖然知道對方時刻面臨生命威脅也心甘情愿。
在白色恐怖籠罩的校園里,許多共產黨學生被抓了,這時她卻選擇加入共產黨,她說,“共產黨就要發動被壓迫者推翻壓迫者,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自由平等的世界”(陳忠實,2001:282),這樣她便站在了她出身的對立面。因此,她是叛逆的。她也是純潔的,她通過艱辛而真誠的努力,尋找到了自身生命的價值和生活的幸福。
斯庫特是美國阿拉巴馬州一個叫梅科姆的小鎮一名六歲的小女孩,《殺死一只知更鳥》從她的視角,為我們描繪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這個閉塞的南方小鎮上人們的生活。
小說的前半部分,主要描述了斯庫特和她哥哥杰姆及他們的朋友迪兒的話劇扮演游戲以及引誘拉德利家的阿瑟走出房子的惡作劇,在孩子們眼中,被囚禁的阿瑟是神秘與恐怖的代名詞。但是隨著她的成長,她發現阿瑟放在樹洞中的禮物;在莫迪小姐家著火時,是阿瑟將毛毯披在衣著單薄斯庫特身上;在他們夜里潛入拉德利家被阿瑟的哥哥內森發現并開槍示警時,杰姆的褲子被鐵絲掛住,是阿瑟把褲子補好,疊整齊放在原處的;在斯庫特兄妹被白人痞子尤厄爾威脅時,是阿瑟沖上去與尤厄爾搏斗并抱著受傷的杰姆回家的。這個被父親囚禁的少年已經成長為一個有正義感并且道德高尚的青年。正是在與阿瑟的交往中,斯庫特認識到真實的阿瑟,他是一只遭到狹隘的道德和宗教觀念扼殺的知更鳥。他對斯庫特兄妹的救助是他得到社會重新認可的重生,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作者表明她對南方社會和青少年成長環境的憂慮和希望(李紅梅 2013(15):37-38)。
小說的后半部分講述的是黑人湯姆的冤案。
當時的南方,奴隸制雖然早已被廢除,但種族歧視卻浸透在許多人的思想中,成為一種思維定勢,主宰著人們的生活,種族隔離體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們,許多也抱有同大人一樣的種族歧視的看法。
斯庫特幸運地出生在一個對黑人平等相待的家庭,父親對黑人卡波妮的態度影響著斯庫特兄妹對黑人的看法——即把她當成家庭的一員。她不僅僅是女傭,而是身兼出色的廚師,孩子行為的監護人,對他們的日常行為進行教育。種族平等的觀念從小在少時的斯庫特心中確立起來。
隨著她漸漸長大,她發現小鎮上的人對待黑人的態度與自己很不一樣,他們歧視黑人、貶低他們,他們的宗教觀念沒有黑人那么純潔,宗教成為束縛人的工具,她漸漸明白鄰居阿瑟就是他虔誠父親偏執的宗教觀念的犧牲品,宗教已經異化為束縛人的工具。她在旁聽了對黑人湯姆的庭審,看到湯姆受到白人陪審團不公正的判決時,她感到不解與困惑,這只被白人殺死的知更鳥是不幸的,他的悲劇使斯庫特思考種族主義的危害是如何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實施的,這對她日后的成長起到重要的影響,使她了解到她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她學會了思考,她的勇氣也在增加,她身上的變化實際上也寄托了作者對南方的未來的樂觀的期待(韓小梅 2008(5):37-38)
白靈是白鹿原上的精靈,她代表了作者對新一代覺醒的女性的美好理想,她聰明好學,純潔美麗,樂觀開朗,向往自由平等的生活,并且擁有堅忍不拔的實現理想的勇氣,是女性美的代表;斯庫特聰明伶俐,對周圍的世界充滿好奇。她從父親對待卡波妮的態度上,學會了對黑人的尊重;在父親阻止她與哥哥對阿瑟的惡作劇中,了解到對他人不幸的同情;在與貧窮白人孩子的交往中,理解了平等待人的重要;在對無辜湯姆的有罪審判中,了解到種族主義的罪惡,她的成長與成熟代表了作者對南方未來的希望與理想。
白靈與斯科特都是新興思想的代表,是自由女性的化身,在她們身上寄托著作者對未來美好的希望。這是這兩個人物的共性。
但是兩位作家在人物的刻畫上采用的方法是不同的。陳忠實對白靈的刻畫主要是以側面描寫為主,以全能的視角和人物對話作為表現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而哈珀·李在《殺死一只知更鳥》中是以斯庫特的視角來敘述的,因此斯庫特的所思所想就自然為讀者所知,她的個性、心理活動、她從一個天真可愛的女孩逐漸成長起來的心路歷程,在她的敘述中被細膩、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這與哈珀·李的女性作家身份密不可分,使她更擅長從女性的角度來開展敘述。雖然兩位作家采用的敘述角度不同,但白靈與斯庫特的形象塑造都是很成功的,她們被廣大讀者所接受和喜愛就是最好的證明。
3. 田小娥與馬耶拉——傳統文化的殉難者
田小娥是陳忠實《白鹿原》中的一個另類女性,年輕美麗的她,她的反叛行為是傳統社會所不能容忍的,她的不貞只能遭到人們的鄙夷與唾棄,最后被這個社會所清除。她對這個社會的反抗,通過瘋了的鹿三口中喊出,她為自己所受到的不公鳴冤、抗議。
馬耶拉是鮑伯·尤厄爾的長女,承擔起照顧弟妹們的責任,包攬了所有的家務勞動,她的家庭背景使她得不到他人的關愛,只有充滿同情心的黑人湯姆,在她的請求下幫助她。母親的缺失使她過早地承受生活的壓力,南方社會盛行的種族歧視與刻板的道德標準是造成她的悲劇的社會根源。
田小娥與馬耶拉是作者塑造的道德墮落的女性,她們是傳統文化偏見的犧牲品。
三、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白鹿原》與《殺死一只知更鳥》通過眾多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作者揭示出女性成長、生活的社會問題和女性悲劇命運的社會文化因素,從而深刻反映了人性。陳忠實與哈珀·李都從自己所熟悉的現實生活中尋找到創作的源泉,以特定的文化語境為基礎,表現出人的生存悲劇。正是傳統文化對人的心靈的價值召喚與人格理想的堅守、情與理的沖突,塑造了生活在其中的人性。以生命的悲劇性,對人性的深刻揭示,尤其是對女性生存悲劇的刻畫,是這兩部作品共同之處,也是這兩部作品的魅力所在。
參考文獻:
[1]陳忠實,《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2]哈珀·李,《殺死一只知更鳥》[M].高紅梅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3]李紅梅,解析《百舌鳥之死》的意象蘊涵[J].短篇小說(原創版),2013(15):37-38.
[4]常何,小說構架與靈性之根:哈珀·李作品解讀[J].芒種,2012(12):91-92.
[5]韓小梅,論美國南方小說《百舌鳥之死》的三重主題[J].時代文學(雙月上半月),2008(5):37-38.
[6]薩克文·伯科維奇主編,劍橋美國文學史第七卷[M].孫宏主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417-424.
[7]趙錄旺,《白鹿原》寫作中的文化敘事研究[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