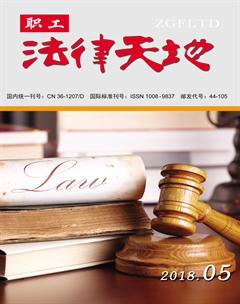觸電司法解釋廢止后的若干法律適用對策
溫林宏
摘 要:在觸電司法解釋被廢止之后,當前法律上所面臨著的最大問題是法律適用,具體來說就是《侵權責任法》第73條的具體適用。本文就當前面臨著的高壓電界定、經營者、免責事由對觸電司法解釋廢止后面對的法律適用問題進行探討,并提出了相關建議。
關鍵詞:觸電司法解釋;廢止;侵權責任法;法律適用
一、對高壓電的界定仍應采納觸電司法解釋規定的標準
在對非高壓電以及高壓電進行界定的過程中,因考慮到其直接關系到觸電人身損害賠償責任中歸責問題,故必須非常慎重。其中非高壓電所導致的人身損害主要是依據《侵權責任法》第6條來進行界定,而高壓電導致的同樣的問題,則主要根據《侵權責任法》中第73條來進行界定,這是司法鑒定過程中必須明確的問題。
在出臺觸電司法解釋之前,關于非高壓電和高壓電并無統一的界定標準,通常是依據《民法通則》中第123條中的相關要求來確定,但具體的等級卻未做任何明確。
但結合《侵權責任法》第73條中相關要求來看,其對“高壓”的界定非常的籠統,并且并未對非高壓電以及高壓電做出明確的界限。為此,《當觸電司法解釋》廢止之前,在實踐過程中,均是按照該項規定來操作;而當該《解釋》被廢止之后,此項規定隨即也就無法應用于高壓電的判斷。為此,對其進行明確非常重要,否則就只有根據《侵權責任法》中第73條規定來處理涉及到觸電人身損害的案件,這就會導致界定的分歧問題。
筆者認為,針對高壓電電壓等級的相關判斷及操作標準,《觸電司法解釋》中第1條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其不僅是對實踐經驗的審判經驗的總結,同時具有較高的法律、法規以及理論依據,對司法實踐操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應用價值,為此,不能夠單純因為將該項《解釋》廢止,而對該項判斷標準也一并否決,而是應當堅持其所確定的、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高壓電判斷標準,為觸電損害賠償責任案件提供一個統一的適用標尺,從而實現對相同案件不同審判結果的有效避免。而針對該問題,立法機關的相關專家在經過長期的實踐后得出了肯定意見,并表示當前在司法事件審理的過程中,將電壓超過1000V視為高壓電的判斷標準。
二、高壓電的經營者與電力設施產權人的概念問題
我國針對高壓電觸電損害責任主體的認定上,現有的法律、法規上并未做出任何的明確規定,即便是有相關標準但各項法律也不統一,例如:《侵權責任法》中第73條將高壓設定為“經營者”;而在《民法通則》第123條中又將高壓設定為“作業者”;而在《電力法》中第60條中則認為在電力運行事故為第三人或者用戶造成了損害的情況下,電力企業必須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要求承擔起相應的賠償責任。
在《侵權責任法》中第73條相關要求,其將責任主體界定為提供高度危險活動損害的經營者,而在司法實踐過程中,有法官認為關于電力設施產權人的相關界定,仍然應當延用《觸電司法解釋》中的相關規定;另有法官在司法處理中,則根據新法中關于責任主體界定來審理,這就導致了相同案件不同審理結果的情況。在將《觸電司法解釋》進行廢止處理之后,原本其界定的責任主體為電力設施產權人規定,也因此喪失了其司法依據作用,并使得絕大部分法院在對經營者的解釋上不再以電力設施產權人來判斷,從而導致如今大部分審理結果均是以供電企業承擔賠償責任。
在對高壓電觸電案件進行審理時,必須認識到在電能以及其交易期間本身就存在較大的特殊性。電能的所有經營權以及所有權均是以產權作為關鍵的分界點,簡單來說就是在完成了交付之后,那么其權利也就隨之轉讓。針對這種情況,經營者主要是指持有電能并進行經營的一方,其同時又是電力設施產權人,并不在單純的只是供電企業的經營方,同時其還包括了用電企業。此外,還必須認識到,供電系統無論是生產、運輸,都是一個非常復雜、龐大的過程,同時也具有較高的簡潔性,即從生產到運輸只需要一瞬間,但在這個過程中,各個環節有密切關聯。在發生觸電事故時,電力經營者涉及的方面非常廣,包含了與電網相互連接的多個主體,例如:蓄能電站、核電站、電網企業以及電力用戶等,若不對這些電力設施產權以及相關維護責任進行合理的區分,那么在發生事故時,在這條線上的每一個用戶以及輸電企業等都需要承擔起主體責任,從而致使其相應承擔的責任無法得到有效界定。而出現這種結果,也從另一方面表明了《觸電司法解釋》中提出的以電力設施產權人作為責任主體觀點的正確性。
若根據《觸電司法解釋》中提出的關于經營者的界定標準設定為電力設施產權人,那么理論上就能夠獲得更加充分的依據。有研究者表示,根據觸電司法解釋中針對電力設施產權界定來進行判斷,電力設施的產權屬于誰,那就由誰來承擔起該設施所引發的賠償責任。在高壓電導致人員發生損害的責任中,結合產權歸屬原則即可將其明確為電力設施產權人,簡單來說,也就是《侵權責任法》中第73條所確定的經營者。而在其他研究者的著述中,也對此明確了相同的立場。關于這樣的意見可以說是非常正確的。《侵權責任法》中第73條關于經營者主要是針對高壓、高空、高速運輸工具以及地下挖掘四種高度危險活動的總體情況來做出明確,可以說具有非常高的彈性,為此,將經營者確定為高壓電的電力設施產權人具有較高可行性。
根據立法機關專家的相關意見來看,在對高壓電案件的審理中,必須對輸電、發電、用電以及配電進行合理區分,并需要對其不同的主體進行明確,若是在工廠范圍內的電力生產設備勢必會導致較大的損害,責任主體主要是指該工廠的經營人員。這種解釋盡管并未采取任何電力設備產權人的概念,但最直接的區別是供電、發電以及用電三者的不同界定,而這已經與基本概念非常接近。
但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當《觸電司法解釋》在被廢止之后,使得其在電力設施產權人方面的相關解釋、界定和概念的條文也一并被完全廢止了,但在司法實踐過程中,仍然可以繼續沿用該《解釋》中針對經營者的相關界定,并將其作為觸電損害賠償責任主體的確定標準,同時將電力設施產權的分界點作為判斷的主要標準,并對供電和用電雙方在電力運行期間涉及到的相關經營權和所有權進行確定,保證供電和用電雙方均能夠更好的承擔起相應的民事責任和供電設施維護管理責任。在產權范圍中納入電力標準,那么在發生事故之后,就能夠結合產權責任來進行相關責任的確定和賠償,進而有效避免損害侵權責任。針對該項標準的實施,能夠更好維護和保障供電以及用電雙方的權益,并對觸電損害賠償案件的責任主體和產權人進行合理確定,更好實現對賠償責任的界定。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能夠根據供、用電雙方對相關供用電合同進行簽訂,并對事故造成的電力設施產權人進行確定,同時并未對產權人做出明確約定,并結合責任利益一致的情況下,對電力設施單位作為電能權利人實施推定管理,進而對侵權責任主體進行確定。
三、應當將《觸電司法解釋》規定的免責事由納入《侵權責任法》的體系
根據《觸電司法解釋》中第3條中關于免責事由,其總結出了4項,其中包括不可抗力以及受害人故意等相關規定,這些規定與《侵權責任法》中第73條的規定相一致,故不需要對其在做深入討論。
關鍵是需要對第3條中第(3)項和第(4)項這兩項不同的免責事由是否需要繼續運用做出規定,并且這方面的爭議性還非常大。有研究者表示,在《電力法》第60條中對用戶自身過錯而導致的電力事故,并因該事故使得自身的利益受到損害,電力企業無需承擔相應的責任。但由于該項規定與《侵權責任法》中第73條中的相關規定出現了明顯的沖突,為此不能夠再更好的推行。對此,在《觸電司法解釋》中所提出的另外兩項免責事由,也無法在第73條規定的影響下得到推行,并且也無法得到有效適應,更何況是該項司法解釋已經被完全廢止。
但就事實上來看,在將《觸電司法解釋》廢止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給出的理由是,其認為該項規定與《侵權責任法》的相關規定出現了矛盾、沖突。為此,我們可以了解到,在《侵權責任法》第73條中,針對減責和免責的要求,主要是針對部分具有高危險度的活動而導致損害的實踐,而針對高壓電而導致的損害卻并未做出相關規定。在《觸電司法解釋》中第3條第(3)、第(4)項的相關要求,其明確了受害人由于發生盜竊行為或者對電力設施進行破壞或者由于其他犯罪行為而導致的觸電事故的情況,或者在電力設施保護區域內,明確指出了禁止行為,而受害人遭受到損害的情況,電力設施產權人可以不承擔相應的責任,并且該項規定具有較高的獨特高壓電損害責任效果。盡管當前司法解釋已經被完全廢止,但在該項規定中,對《侵權責任法》《電力法》以及《電力設施保護條例》等相關性法律法規卻相符合,為此仍然應當堅持其所提出的免責事由。
四、仍應參酌適用《觸電司法解釋》關于特別免責事由的規定
對于擅自進入高度危險地區,供電企業采取了安全措施,而且做好警示任務,電力企業應當減輕責任。具體減少或免除供電企業的責任,法官應視情況而定。如果符合上述情況,又存在《觸電司法解釋》第3條第(3)、第(4)項規定的情形的有下面兩種適用法律的方法:
首先,如果存在觸電司法解釋第3條第(3)、第(4)項規定的受害人為了“盜竊電能,盜竊、破壞電力設施或因其他犯罪行為造成觸電事故,或者“受害人在電力設施保護區從事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行為”,要免除供電企業的侵權責任,而不是減輕責任。
究其原因,是在這種情況下,供電企業的管理行為和人身損害后果之間沒有因果關系,不構成侵權責任。基于這種條件下,作為管理者的供電企業仍應承擔侵權責任,這與《侵權責任法》的概念和責任構成規則不符。比如,隨著社會經濟和城市建設規模的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違法建筑物、構筑物或植物種植在電力設施保護區。在從事這些違法行為時,不注意供電企業的通知和警告,造成觸電事故后對供電企業提出索賠。
當事人拒絕承認供電企業的提示和制止行為,由于供電企業的提供的證據有限,法院最終決定供電公司應根據供電企業未履行的管理和警示義務承擔賠償責任,這是不正確的。供電企業承擔賠償責任的損失實際上是在供電成本中,最終將由所有的電力用戶承擔。在司法解釋被廢除后,這仍然是填補漏洞的問題。對侵權行為的賠償責任,必須根據這一解釋給予更多的關注。應當免除供電企業的責任。
其次,供電企業不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不履行警告義務的,受害人未經許可就進入高度危險區域,并具有前述免責事由,供電企業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受害人也應承擔損害一部分后果,構成與有過失,應當依照《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考慮到事故的原因和程度,雙方將承擔損害賠償的后果,降低電力企業的賠償責任。
五、結論
總而言之,在《觸電司法解釋》廢止之后,當前針對電力方面的相關法律面臨著諸多法律問題,我們在進行合理分析后發現,在《觸電司法解釋》中仍然有不少界定、解釋可以繼續沿用,這對規范和保證《侵權責任法》的推行和全面落實具有較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1]唐子騏.高壓觸電問題法律研究[J].法制博覽,2017(15):261.
[2]王文哲.觸電事故中“不可抗力”的適用[J].農村電工,2016, 24(06):9.
[3]凌超.論觸電侵權規范適用的沖突及其解決——基于若干案例的實證分析[J].貴州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14,26(03):79-86.
[4]孔維江.淺談供電企業面臨的人身觸電損害賠償法律風險及防范措施[J].家教世界,2014(04):24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