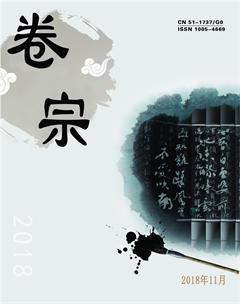博物館觀眾參觀行為的影響因素及其意義
摘 要:博物館觀眾的參觀行為可以分為參觀前、參觀過程和參觀后三個階段并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具體包括社會因素、個人因素、心理因素和參觀時的環境場景因素。前三種因素貫穿于參觀行為的全過程,環境場景因素則主要作用于具體的參觀過程。這些因素會影響觀眾對博物館的印象與期待以及其以后的參觀行為,并對博物館工作造成反向影響。這也是現代博物館觀眾自主性的體現,從而要求博物館必須注重觀眾在博物館工作中的“主體”地位。
關鍵詞:博物館觀眾;參觀行為;影響因素
1 前言
2007年國際博協對博物館的定義為:“博物館是一個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的、非營利的常設機構,向公眾開放,為研究、教育、欣賞之目的征集、保護、研究、傳播、展示人類及人類環境的有形遺產和無形遺產。”本文所討論的博物館即指傳統意義上的博物館,生態博物館、露天博物館等新型博物館不在討論之列。
博物館對藏品的征集、研究、保護都是為了向觀眾傳播展品所蘊含的歷史、文化、藝術、自然、科學等信息,以達到使觀眾在欣賞藏品的同時得到教育的目的。可以說,博物館觀眾雖然不是博物館這個機構的組成部分,但卻和博物館藏品一樣,是博物館得以存在、運轉和發展的重要組成元素。如果沒有觀眾,博物館就成了儲存各種文物、自然標本的倉庫,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因此,對博物館觀眾進行研究是博物館工作的重要內容。長期以來,博物館與博物館觀眾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博物館居于主體地位,而博物館觀眾則居于客體的地位,博物館觀眾被動接受著博物館自身對博物館及展品的解釋。而在現代社會,人們的個性得到充分的展現,自主意識不斷增強,對事物的認知更加多元化,也不再滿足于博物館對展品的有限解釋,而是以更加多元的視角對展品所蘊含的信息進行新的個性化的意義構建。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博物館觀眾對博物館的認知渠道也更加多樣化,觀眾會根據來自不同渠道的信息對博物館進行評估、選擇,而使博物館面臨更多的行業內甚至行業間的競爭壓力。觀眾自主性的增強意味著博物館與博物館觀眾之間主體與主體關系的增強。博物館觀眾的自主性不是表現在直接參與博物館的管理研究等具體工作,而是通過觀眾對博物館的參觀行為間接影響博物館工作。而觀眾的博物館參觀行為會受到社會因素、個人因素、心理因素、參觀的環境場景因素等多種因素影響。對這些因素進行分析和研究,可以幫助博物館提高工作水平,給博物館觀眾創造一個更好的參觀條件,從而促進博物館事業的發展。
2 觀眾的參觀行為及其影響因素
觀眾對博物館的參觀行為可分為參觀前、參觀過程和參觀后三個階段[1]。而影響參觀行為的因素包括社會因素、個人因素、心理因素等多個方面,并貫穿觀眾參觀博物館的前中后整個行為過程。社會因素包括觀眾接觸和使用博物館的方便程度、博物館的綜合形象以及社會整體對博物館的認知、社會文化環境等;個人因素包括觀眾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收入狀況、社會交往和生活方式等;心理因素包括觀眾參觀博物館的心里需求和參觀動機等。另外,在進行具體的博物館參觀時,還有環境場景因素在起作用,具體包括博物館基礎設施、燈光、音樂、展廳布置、陳列藝術等。
2.1 潛在觀眾的參觀選擇
在參觀博物館之前,作為潛在的博物館觀眾,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并最終決定其是否會選擇參觀博物館。隨著媒體技術的發展,博物館已不再是遠離人們視線的建筑物,人們可以通過網絡、傳媒等足不出戶就了解到很多關于博物館的資訊。人們可以通過博物館網站、網友的評價等對一個博物館的基礎設施、服務水平、展覽內容及水平等有一個較為全面的了解,從而在內心形成自己對博物館形象的整體評價,進而決定是否參觀某個博物館或某個展覽。社會文化環境則決定著博物館在社會大眾中的整體形象,如由于前段時間《國家寶藏》的熱播而在社會上掀起的博物館熱。另外,博物館作為一個文化機構,不同的人由于不用的教育水平、興趣愛好以及生活方式等,對博物館有不同的需求。相較于休閑娛樂型的觀眾及普通旅游者,那些有更多文化需求、希望到博物館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提升自我的人更傾向于主動選擇參觀博物館,并也往往對博物館抱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
2.2 多種因素影響下的“三者互動”參觀模式
在參觀博物館的過程中,這些因素會影響觀眾的參觀效果。觀眾在參觀博物館時,是通過一種互動體驗模式來獲取信息的。這種互動的對象是“物”、“觀眾”和“博物館”。而具體的互動體驗模式則是觀眾在社會因素、個人因素、心理因素以及參觀時的環境場景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具有社會性、環境性、知識性和情境性的博物館整體體驗[2]。
2.2.1 三個互動對象的關系
在“物”、“觀眾”和“博物館”三者中,物是離開了其原生環境的博物館中的展品。而一旦離開了其原生環境,物的本身屬性就發生了改變,喪失其原有的某些功能而獲得了新的功能。而物所蘊含的信息也會因此而變得不完整,盡管我們會通過場景再現的方式去還原其原來所處的環境,但是也只能做到形似,神似是無法還原的,因為這并不是物原有的樣子。但是這并不代表物的價值受到了破壞,而是一個“損益”的過程。因為這些“物”在進入博物館之前或說在我們把它們看作可以進入博物館的文物的時候,大多數就已經脫離了它最初的原生環境。即使是那些原址建立起來的遺址博物館,其位置雖未改變,但是創造它們的人、其原有的社會狀態、文化環境也早已不存在,不過是“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但是在博物館的有限空間里,我們把原本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物組合到一起,它們一相遇,述說著各自的故事,又在彼此間產生了新的聯系。這些“物”本身和它們之間建立的新的聯系便成了觀眾創造新的意義和故事的素材了。這就是博物館給物提供了一個新的文化生境。而對于觀眾,則是一個新的認知環境。在這里,時間被壓縮,空間被置換,觀眾與博物館一起對物進行著新的意義的構建,并因人而異的賦予其不同的意義和內涵,正像是“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了。
因此,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可以概括為:物賦予了博物館科學、文化內涵,使其成為知識的殿堂,給人則提供了可以欣賞的、蘊含著豐富信息的意義對象;觀眾對博物館的文化、休閑、學習的需求,賦予了博物館存在的意義,同時觀眾作為物的信息傳播的接收者,也對物進行著新的意義的構建,延伸和豐富著其內涵和價值;而博物館則賦予了物以新的文化生境,賦予了觀眾以新的認知環境,并給物和觀眾之間的互動和信息交流提供了特殊的空間[3](圖1)。
2.2.2 互動體驗模式的作用方式
而在這三者互動過程中,唯有人是最具多樣性和不確定性的。擁有不同身份、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對展品的認知是完全不同的。對同一件展品,不同的觀眾會帶著不同的審美觀、價值觀對其進行審視,從不同的角度、深度進行闡釋,從而產生不同的意義解讀。觀眾參觀博物館的心情、目的等心理狀態也會對參觀效果產生很大的影響。在愉悅的心情下參觀和煩悶的狀態下參觀一定會有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體驗。而為了學習、研究等目的而參觀和只是為了放松、游玩的參觀其關注點就會不同,自然也會有不同的收獲和體驗。博物館的環境場景也是影響觀眾參觀行為的重要因素。博物館的燈光是否讓人感到舒適、音樂是否讓人舒心并與展覽氛圍相符合、展廳的布置是否協調、陳列是否富于節奏變化、服務設施是否周全便利等都會影響到觀眾的參觀心情和舒適度,從而影響到觀眾的參觀效果。博物館作為文化休閑場所,相比于其他的公共休閑場所,最大的不同就是博物館具有文化屬性。因此博物館觀眾不管一開始是出于文化體驗的目的還是休閑娛樂的目的來到博物館,在進入博物館之后,在博物館特有的文化氛圍下,就多多少少帶有了文化體驗的因素。在置身于較為濃厚的社會文化氛圍時,觀眾在參觀時也會帶入在時下文化氛圍中的感受。在當下大力推崇傳統文化的背景下,看到穿越千年的古代精美文物時那種“一眼千年”的感觸想必會更深刻。
2.3 博物館觀眾對博物館的“使用與滿足”
李軍借鑒傳播學“使用與滿足”理論對博物館觀眾進行研究,指出人們一旦決定了要參觀博物館,就必定會對博物館產生一定的心理期待,期望通過參觀博物館得到某些方面的收獲與滿足。而觀眾在博物館的參觀行為中獲得的“滿足感”的程度,會影響觀眾對博物館的期待水平以及以后觀眾對博物館參觀行為的選擇[4]。
在參觀之后,觀眾會參照參觀前對博物館的預期期待與參觀后形成的對博物館及展覽的實際印象進行對比,從而獲得不同程度的滿足。而參觀是否達到了觀眾在參觀前的心理期待,對本次參觀是滿意還是失望則往往會影響博物館在觀眾心中的形象和期待水平,從而影響觀眾以后對博物館的參觀行為。如果觀眾對參觀感到滿意,那么在下次進行選擇的時候,就可能會優先考慮去博物館參觀。反之,如果觀眾對參觀感到失望,那么下次在做選擇的時候,觀眾就會轉而尋求其他的休閑方式與休閑場所。而且這種對博物館的印象與期待不會僅限于某個博物館和個人。觀眾對某一次博物館的參觀體驗的好壞不僅會影響到觀眾對所參觀的博物館的印象,還很有可能會把這種印象轉移到其他博物館上。并且觀眾還會把這種對博物館的印象和期待傳遞給他人,影響到他人對博物館的印象和期待。而在熟人社交傳媒發達的今天,這種傳播速度會很快、影響更為直接、且效果也更為顯著。
3 結語
在觀眾對是否參觀博物館進行判斷,形成、調整對博物館的印象和期待并把其向外傳播時,其實就是在博物館信息傳播過程中扮演了更加積極和主動的角色。博物館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令人向往的文化、知識殿堂,而不過是觀眾眾多選擇中的一個。觀眾獲取博物館信息的渠道更為廣闊,而不是只聽博物館自身的宣傳,無論博物館自身把自身標榜的多高,觀眾總會通過各種渠道把它拉回到現實中來。這并非觀眾刻意為之,而是宣傳與現實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對于博物館的物的解釋,觀眾也在向博物館發出挑戰,觀眾會根據自己的理解對物進行獨有的價值闡釋和意義構建,更加具有自主性。這就一定程度上使博物館喪失了文化權威的地位,也要求博物館在工作上更加注重如何創造一個能夠給觀眾更多自主性的空間,而非一味對物做出博物館自身的理解和闡釋。
參考文獻
[1]王啟祥.國內博物館觀眾研究知多少[J].博物館學季刊,2004,18(2)
[2]王思怡.博物館觀眾研究的反思與演變--基于實例的觀眾體驗分析[J].中國博物館,2016(2):7-15.
[3]潘寶.器物表征的建構者:博物館人類學視域中的觀眾[J].中國博物館,2016(4):84-91.
[4]李軍.使用與滿足理論視閾下的博物館觀眾研究[J].中國博物館,2016(2):16-23.
作者簡介
王夢恩(1995-),男,河南開封,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主要從事博物館與文化遺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