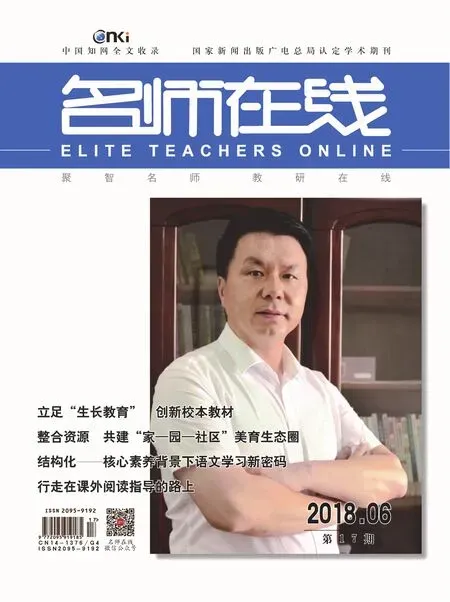與文本對話—課程視野與兒童視角下的思考
蔣 赟
(江蘇省蘇州市工業園區新洲幼兒園,江蘇蘇州 215000)
引 言
文本是教材的集中體現,但隨著新綱要理念的推行,筆者越來越認識到:教學不再是課程傳遞和執行的過程,而是課程創生和開發的過程;學生也不再是知識的接受者,而是文本的對話者。與文本對話,是作者與讀者兩種視界的不斷融合,是一種創生與更新,更是課程適宜性變革的應然追尋。因此,筆者反復思索:文本的意義是什么?“與文本對話”中應如何理解課程視野與兒童視角?“與文本對話”的操作策略具體又有哪些?
一、對“與文本對話”的理性思考
對于先于學生接觸文本的教師來說,文本的解讀體現了他們的文化視野、審美情趣和邏輯思辨等綜合能力。所謂“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然而,現狀并不讓人樂觀。如“教師的手,真巧!”像是一句由衷感嘆并意猶未盡,而解讀成“教師的手/真/巧”則看似著力贊美,卻缺乏內涵。詩歌基調由此而定,教學效果自然大相徑庭。曲解文本的內涵,只會和目標漸行漸遠,筆者不禁追問:隱藏于其中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一)從“即時見效”到“自由緩釋”的目標轉向
急功近利是現代社會的一大弊端,這弊端在教學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教學活動中,學生為什么就一定要在活動中立刻學會誦讀?誦讀為什么一定要教師起頭或者跟著教師?為什么不能讓學生在品析中體會文本的意蘊,問一問學生:“給你什么感覺?”“你覺得可以用怎樣的聲音和速度來讀?”教師覺得學生達成了目標,而事實卻是:學生沒有體驗、缺乏感悟、不會對話,只是一個認真的聆聽者和忠實的追隨者,與其說他們在感悟文本,不如說在模仿教師,他們的表現讓教師不得不轉身叩問目標定位的準確性。應當看到:一些注重“及時見效”的目標定位,會讓學生讀出教師的期望與標準,努力迎合,卻阻礙了他們與文本自由生長的空間。面對這樣的情況,教師應該調整目標,留給學生“自由和緩釋”的空間與機會,鼓勵學生充分的感悟、體驗和表達。通過這種方式,“與文本對話”才會成為可能。
(二)從“檢驗手段”到“真實表達”的支架搭建
在活動現場,常能聽到這樣的話:“請和我一起來……”,在這樣的視角下,本是主體的兒童的聲音被丟棄和淹沒;同時,復述、誦讀不應簡單地固化為“檢驗手段”,教師應該從兒童視角出發,進行相應的支架搭建,有效地提問與追問、欣賞與感悟、討論與分享……在復述與誦讀中深層次地引導和鼓勵學生的“真實表達”;而兩者間的變遷,折射的是教師理念的變革[1]。
(三)從“形式為上”到“共情為重”的思維轉變
當下,教學形式被空前重視了起來,卻常能看到一些曲解或無效的現象時有發生。流于表面的形式只是漂亮的外在,文本的內涵、意蘊更值得被反復品讀和挖掘。文本最大的價值在于:它永遠處于與理解者對話的意義生成過程之中。因此,在“與文本對話”中引導學生逐漸熟悉文本、沉浸情境和移情共情,才是最好的“形式”。
追根究底會發現,教師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過于關注自己的角色,教學情境的創設、環節的設計、教具學具的提供和運用……但對活動的載體—文本的研讀和研究卻十分忽視。那么“與文本對話”,在實踐層面到底應該注意什么?
二、對“與文本對話”的潛心剖析
(一)關注兒童認知的“起點”
與文本對話,解讀是基礎,而解讀的最高境界,就是“深入淺出”。奧蘇伯爾指出:“影響學習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學習者已經知道了什么。要探明這一點,并應據此進行教學。”如果教師在文本解讀時不探明兒童真實的認知起點,往往就會出現“深入深出”的教學現狀,令兒童茫然不知所措。
(二)關注兒童學習的“趣點”
兒童是好動的、好玩的與好奇的,有著他們自己的興趣世界。因為感興趣,他們就會調動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去關注、去參與。因此,在文本解讀中,教師要努力找準兒童學習的“趣點”,以引導兒童更真實、更有效地展開活動。
(三)關注兒童經驗的“盲點”
所謂“盲點”,是指文本中兒童無法直接感受體驗的內容,而本身又缺乏相關的經驗。準確捕捉兒童的“盲點”,并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來突破它,那么兒童對問題的思考和對文本的意義建構往往會更生動、更深入。
如《賣火柴的小女孩》中,學生很難想象小女孩又冷又饑、又怕又累的狀態。針對文本“她敢從成把的火柴里抽出一根,在墻上擦燃了,來暖和暖和她的小手嗎?”可以設計以下提問:“小女孩一整天都不敢,為什么?”“現在敢了,又為什么?”“從不敢到敢,你覺得可能發生了什么?”由提問逐漸讓學生體會小女孩生活的悲慘和厄運的即將來臨,讓相關的經驗、情感都逐漸豐滿起來,使較為深入地感受故事成為可能。
(四)關注兒童情感的“觸點”
相比成人而言,兒童的情感更率真、感動更直接,找準兒童情感的“觸點”,才能引領他們在審美體驗中獲得精神的提升。繪本《彼得的椅子》中有一頁:彼得為妹妹把小椅子刷成了粉色。可以提問:是什么讓彼得改變了?爸爸媽媽愛彼得嗎,從哪里知道的?彼得愛妹妹嗎,又從哪里能知道?在細致品讀后,學生感受了彼得從失落—難過—理解—釋然—快樂的心理歷程,對“包容”和“愛”有了更多的理解。他們獲得的不僅是語言、音韻和意境,更受到了情感的浸染。
三、對“與文本對話”的感悟追尋
“與文本對話”,如同葉圣陶先生所說的要“潛心會文”和“虛心涵泳”,對文本做靈感式的創生,是教師應當追求的一種理想境界;同時,對文本的解讀,也不應停留于文字的層面,同樣要考慮文字所承載的文學和文本所浸潤的文化。文本不應是棵孤樹,在課程中,在文化的視界中,它可以是片茂密的森林。
(一)民主與首席共存
在價值多元的今天,文本解讀也顯示出了它的多層面性,很多東西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多元共存”。教師需要以兒童視角來讀懂文本、理解角色;但同時也要看到,面對缺乏獨立閱讀能力的學前兒童,教師的作用無可替代。教師是與文本對話的核心與靈魂,引領著對話的過程。所以,教師必須不斷充實、提高和完善自己,只有“信手拈來”,才能“游刃有余”。
(二)開放與回歸一體
文本具有開放性,每位讀者都可以自行理解文本。但開放也當有一個度,超過時就應回歸,回歸文本的起點和文字的本真。教師在與文本對話的過程中,要盡量讓自己與文本相融,唯有如此,教育才會有生成和建構的基礎,才會落足于促進師幼的共同發展。
結 語
與文本對話,遵循課程視野,尊重兒童視角。讓教師們執著地叩響這扇智慧之門,在精神的殿堂里思索、感悟和辨析,感受文本的滋養,和學生一起,行走在與文本對話的大道上,探尋課程創生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