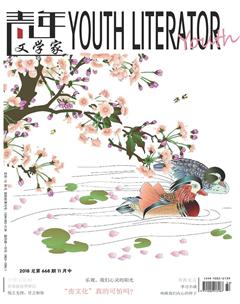周邦彥詠物詞之意象選擇淺析
摘 要:在詠物詞的發展史上,周邦彥是一個關鍵人物。周邦彥工于體物,其詠物詞數量雖不足二十首,卻在前人基礎上進行了多方面的拓展與創新。將他詠物詞中意象的選擇與其人生階段相結合,大體分為詠瑣細之物、詠花柳植物、詠節序風物三個類別,對其每一階段的具體作品進行分析,可以深刻揭示周邦彥在不同人生階段的內心情感變化及其詠物詞的藝術特色。
關鍵詞:周邦彥;詠物詞;意象;選擇
作者簡介:王惠(1994-),女,山東淄博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學科教學(語文)專業教育學碩士。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2-0-01
“詠物”類作品的出現源起于《詩經》,到了北宋中期,詠物詞又在前人的基礎上獲得了長足發展。其中,周邦彥詠物詞中所展現出來的謹嚴的格律、渾融的意境以及精巧的結構更是為詠物詞開辟了一條嶄新路徑,引領詠物詞的創作由探索期進入獨立期,因而其詞作的成就與影響不可低估,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一、詠瑣細之物
汴京初旅時期,周邦彥于太學求學,生活環境單一,活動區域有限,他能接觸到的自然風物并不多,只是偶爾在羈旅懷鄉或閑游坊曲中見到自然風物的出現。這一時期,周邦彥的詞只能稱作片段詠物,其中描寫最成功的作品當屬羈旅懷鄉詞——《蘇幕遮》。此詞雖是小令,卻很好地顯示了周詞的渾然天成、層次鮮明。詞的第一層以烏雀清晨窺檐呼晴這一典型的夏日清晨新晴之景寫鄉愁;第二層,詞人寫到了風荷獵獵的典型江南水景,日日面對這般勾起情思的景物,自然導致詞人情不堪重負;第三層,詞人因日有所思,夜里便時時夢見在家鄉荷塘采蓮的場景。詞人運用白描手法,既有對所詠之物外在形貌的巧妙描寫,又有對所詠之物內在精神的彰顯。
但在此時期,周邦彥真正以物為吟詠對象的詞作,是《看花回·詠眼》和《南柯子·詠梳兒》兩首。《看花回·詠眼》以細膩的筆觸描寫了一位絕色女子的動人明眸,先是靜態欣賞其精致妝容,又寫女子睡意昏沉時似開微合的眼和登高望遠時淚水連連的眼,使人頓生憐惜之意。《南柯子·詠梳兒》則以相似的藝術手法吟詠了一把裝飾精美的梳子。可見,此時周邦彥對身邊瑣細平常的物品產生了濃厚興趣并細致描摹,也從側面反映出他在太學求學生活的空虛。
初旅汴京幾年間,周邦彥繼續沿襲“花間詞”創作傳統,寫作內容和手法均效仿前輩柳永,詞作以戀情詞為主,真正的詠物之作并不多,也缺乏自己鮮明的創作特色。
二、詠花柳植物
隨著詞人生活閱歷增加,周邦彥詠物詞的創作特色開始形成。周邦彥改任溧水知縣四年余,詠物詞數量大增,幾占詞人詠物詞總數的一半。其吟詠對象主要是梅。
周邦彥題為“詠梅”或“梅花”的詞就有四首之多,雖同是寫梅,但因角度不同而風姿各異,其中寄寓的情懷也有深淺之分。《丑奴兒》實多虛少,著重描寫梅花仙子的素凈與幽香,也寄托著詞人對命運的慨嘆。《玉燭新·早梅》則表現詞人對早梅的愛惜之情,形神兼備,化用林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來寫梅之形態,又用壽陽公主的梅花妝不敵早梅的清瘦贊美梅的天然無暇。
在周邦彥的外任詞中,“柳”是另一個突出意象。周邦彥在惜別汴京故友時曾作一首《蘭陵王·詠柳》,雖只是“托物起興,非詠柳也”,但可以算是對以柳入詞的一次成功嘗試。周邦彥集中詠柳的佳作是《蝶戀花》五首,它們分別以新柳、茂柳、飛綿之柳、秋柳為吟詠對象,細致地描寫了柳的各種風姿形態,用筆靈動傳神。
綜上,以花柳植物作為吟詠意象在周邦彥詠物詞中占比最大,花柳植物在前人詩詞中被反復使用,其自身所內蘊的情感內核也與周邦彥當時心境相契合,因順理成章成為其詠物詞的重要意象。
三、詠節序風物
外貶州縣至周邦彥再次遠宦時期,頻頻遷徙異地,周邦彥的心思格外敏感脆弱,每見風物便易生感慨。此時周邦彥已多方面汲取前人創作經驗,技巧更加精工,形成了穩定的沉郁風格。
元符三年,周邦彥時為睦州知府,當年元宵節,詞人心生感慨,寫下一首《解語花·上元》。此詞先極力鋪寫睦州元宵節的熱鬧,進而憶起汴京元宵節令活動。詞人從睦州和汴京元宵游樂的相互比較中突然設置了一個巨大落差——因為游賞情緒的衰減,詞人主動從熱鬧中引退,這種頹廢之感曲折傳達出詞人對自己遠離京師、失意外任的抑郁不平。也是這種屈指年光、已成往事的著筆,使這首元宵詞工麗精粹,成為少有的神駿之作。
周邦彥詠物詞中最好的作品,當屬《六丑·薔薇謝后作》。寫這首詞時,詞人時年五十七歲,薔薇凋謝春事了,很自然地引發了詞人的惜春之情。此詞雖題為“落花”,并不真詠落花。上闋從回憶京城試酒時節入筆,轉入客居地的春歸,再折入落花,折入蜂媒蝶使的多情追惜。景物越轉越細,情感層轉層深。下闋把上闋的意思一一收攏,由春歸落花時節聯想到妻子簪花的美麗形象,結尾對飄流之落花殷切叮嚀,纏綿動人。此詞上下闋一筆駛折,有轉無竭,滿紙都是惜花相思之意。
周邦彥晚年遷徙做官過程中所寫的詠物詞,不僅數量較多而且內容豐富,呈現出渾厚和雅的整體風格特征。隨著人生閱歷的不斷積淀,周邦彥已經能夠將詠物與抒情完美融合,自然流暢,不露痕跡,用筆沉著老練,注重規范法度,在藝術上已臻極境。
結語:
作為北宋詞的集大成者,周邦彥詠物詞的數量在所有詞作中雖所占不多,但是他將創作主體的思想感情深度介入到作品當中,使得所詠之物從“無我之物”成為“有我之物”,大大深化了詠物詞的表現藝術,提升了詠物詞的藝術地位。正是由于這種人與物的高度結合,才為我們以周邦彥的詠物詞為切入點剖析其一生內心情感變化提供了可能。
參考文獻:
[1][元]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2]周邦彥.清真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
[3]孫虹 任翌.周邦彥詞選[M].北京:中華書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