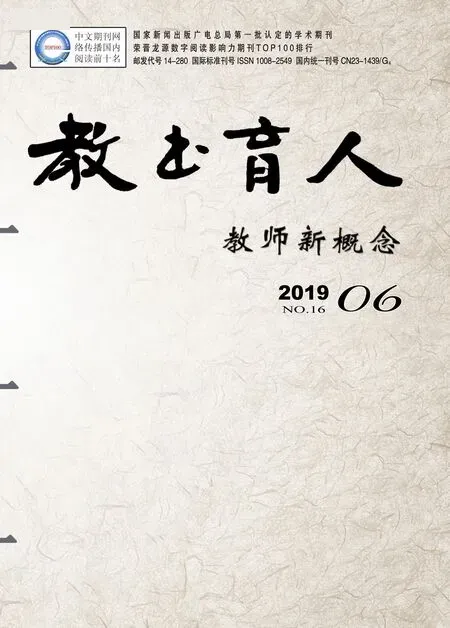根植課堂實(shí)踐,訓(xùn)練復(fù)述能力
李紅松 (江蘇揚(yáng)州市寶應(yīng)縣城中小學(xué))
所謂復(fù)述是指學(xué)生在熟讀文本、理解文本的基礎(chǔ)上,激活自身認(rèn)知思維、運(yùn)用自主語(yǔ)言儲(chǔ)備,將課文內(nèi)容清楚詳實(shí)、富有調(diào)理講述出來(lái)的一種語(yǔ)文能力。新課標(biāo)提出“能復(fù)述敘事性作品大意”的要求,但遺憾的是很多教師對(duì)這一能力的訓(xùn)練并不重視。這就需要教師從文本內(nèi)容、教材編排和基礎(chǔ)學(xué)情等不同的維度展開指導(dǎo),將復(fù)述訓(xùn)練落在實(shí)處。
一、梳理線索,提煉復(fù)述抓手,讓復(fù)述收放自如
復(fù)述需要以概括為基礎(chǔ),針對(duì)學(xué)生的具體學(xué)段,從文本的特質(zhì)出發(fā)進(jìn)行概括,就仿佛是在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上尋找樹木的主干。有了復(fù)述的主干,文本語(yǔ)言表達(dá)細(xì)節(jié)中的“繁茂枝葉”就可以順藤而下。著名語(yǔ)文教育家葉圣陶說(shuō)過(guò):“作者思有路,遵路識(shí)斯真。”無(wú)論文章的篇幅長(zhǎng)短,都蘊(yùn)藏著鮮明的表達(dá)順序,教師可以從文本的不同順序厘清作者的表達(dá)思路,提煉出文本表達(dá)的主線,深層厘清文本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形成課文復(fù)述的抓手。
如選自《儒林外史》的小說(shuō)《少年王冕》的復(fù)述,可以從主人公王冕年齡這根主線入手,組織學(xué)生梳理出王冕在不同年齡段的資源信息:七八歲——父親去世,家庭貧窮;十歲——輟學(xué)放牛;十三四歲——暴雨之后,學(xué)畫荷花;十七八歲——學(xué)有所成,孝敬父母。這樣一來(lái),學(xué)生依托王冕年齡的增長(zhǎng)提煉出生活經(jīng)歷的變化,理出一條清晰可感的抓手,降低了復(fù)述的難度。不同的文本內(nèi)容,提煉復(fù)述主干的方法也可以各不相同。
引導(dǎo)學(xué)生深入解析文本的結(jié)構(gòu)、厘清表達(dá)的脈絡(luò),是展開復(fù)述的基礎(chǔ)和前提。梳理出文本表達(dá)的思路,將原本豐富的課文信息進(jìn)行濃縮,使?jié)摬卦谖谋局械慕Y(jié)構(gòu)逐步浮出水面,復(fù)述就變得收放自如,清晰而富有條理了。
二、具化補(bǔ)充,擴(kuò)展復(fù)述空間,讓復(fù)述有滋有味
很多故事類文本常常留有閱讀空白,讓讀者有二度創(chuàng)作的空間。教師就可以讓學(xué)生在復(fù)述的過(guò)程中進(jìn)行補(bǔ)充填白,引導(dǎo)學(xué)生展開合理性想象,歷練學(xué)生語(yǔ)言表達(dá)能力,讓教學(xué)充滿張力,讓教材在文本中獲得新生。
如教學(xué)《普羅米修斯盜火》一文,教師針對(duì)普羅米修斯被鎖在高加索山一段中“讓他經(jīng)受烈日暴雨的折磨”這一關(guān)鍵性內(nèi)容展開復(fù)述指導(dǎo):首先,緊扣語(yǔ)段關(guān)鍵詞“烈日暴雨”進(jìn)行畫面再現(xiàn)——在“烈日”暴曬下,普羅米修斯盜火經(jīng)歷著怎樣的折磨?在“暴雨”的無(wú)情侵襲下,普羅米修是怎樣的狀態(tài)?其次,教師緊扣“烈日暴雨”引導(dǎo)學(xué)生擴(kuò)展思維,普羅米修斯還會(huì)經(jīng)歷怎樣的自然災(zāi)害?學(xué)生紛紛從生活經(jīng)驗(yàn)出發(fā),羅列出冰雹、霜凍、寒雪等自然現(xiàn)象;最后,教師再組織學(xué)生從中精選一兩個(gè)自然現(xiàn)象,對(duì)普羅米修斯“經(jīng)受折磨”的畫面進(jìn)行再現(xiàn),無(wú)形中豐富了文本中的未盡之言。
這種“疏可走馬”的自主空間,給予了學(xué)生二度創(chuàng)作的自由權(quán)利,不僅可以具化文本的故事情節(jié),更讓文本中的情感與人物形象立體鮮活起來(lái)。在復(fù)述的過(guò)程中,學(xué)生需要對(duì)文本中的細(xì)節(jié)進(jìn)行體悟悅納,更需要對(duì)文本的表達(dá)進(jìn)行儲(chǔ)備和擴(kuò)展,這樣的復(fù)述才會(huì)有滋有味。
三、輻射關(guān)聯(lián),放大復(fù)述效能,讓復(fù)述一舉多得
教師要讓復(fù)述目標(biāo)變得豐富而立體,達(dá)到一定的寬度,讓復(fù)述不再成為單一而割裂的語(yǔ)言訓(xùn)練板塊,要與其他板塊的學(xué)習(xí)巧妙融合,為達(dá)成其他教學(xué)目標(biāo)服務(wù),使得整節(jié)課的教學(xué)因?yàn)閺?fù)述而變得渾然一體。
如《滴水穿石的啟示》一文為了印證中心論點(diǎn),作者先后列舉了李時(shí)珍、齊白石的事例,教師先從“李時(shí)珍”的事例入手,與學(xué)生共同概括事例的大體內(nèi)容,并提煉出概括的語(yǔ)言范式:誰(shuí)在什么時(shí)間做什么,最后做得怎樣?隨后,學(xué)生依托范式快速梳理出“齊白石”的事例內(nèi)容,較為順利地復(fù)述了兩個(gè)名人的故事梗概,但如果教學(xué)止步于此,這樣的復(fù)述既沒(méi)有全新的生長(zhǎng)價(jià)值,又無(wú)法為說(shuō)理文學(xué)習(xí)的其他目標(biāo)服務(wù),就成為一步“廢棋”。為此,教師引導(dǎo)學(xué)生從說(shuō)理文事例選擇的典型性角度出發(fā),分別研制出兩個(gè)事例中所承載的典型價(jià)值,在復(fù)述時(shí)不能純粹從人物和事件的維度展開,而需要著力體現(xiàn)這一事例中的典型價(jià)值,讓學(xué)生在復(fù)述的過(guò)程中為洞察說(shuō)理文事例選擇的策略服務(wù)。
復(fù)述過(guò)程看似紛繁復(fù)雜,但只要我們刪繁就簡(jiǎn)、把握本質(zhì),將復(fù)述訓(xùn)練扎實(shí)地根植于課堂實(shí)踐中,就一定可以學(xué)得扎實(shí)、練得有效,為學(xué)生核心素養(yǎng)發(fā)展服務(w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