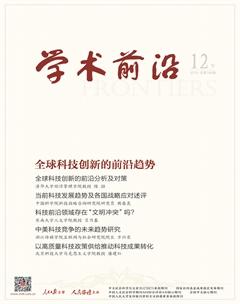生態文明視域下自然資源的刑法保護
管亞盟
【摘要】在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下,自然資源保護需要有刑法的參與。我國自然資源保護的刑事立法存在保護對象不周延、整體保護理念缺失、預防性導向不足、部門法銜接不暢等問題。結合新時期自然資源改革的具體要求,借鑒國外刑事立法的先進經驗,深度挖掘刑事理論的發展,我國自然資源保護方面的刑事立法應當在理念上予以轉變,突出生態價值,側重預防和整體保護。同時,要適當擴充罪名體系,完善懲罰機制,讓刑事立法更好地發揮作用。
【關鍵詞】生態文明建設? 自然資源? 刑事立法? 理念? 生態價值
【中圖分類號】D924.3?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4.012
黨的十八大提出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決策,自然資源管理體制改革也隨即展開。為了可持續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統一確權登記、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改革相繼落地,這些改革都將最終目標落腳到自然資源保護上,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筆者認為,自然資源的保護不僅要依靠管理體制的革新,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法律保障體系至關重要。刑法作為保護法益、規范社會秩序的部門法,需要對此作出回應,構筑起自然資源保護的最終堡壘。
自然資源保護的刑事立法概況
自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增加自然資源保護條款開始,到1997年《刑法》中設置專門章節規制破壞自然資源類犯罪,逐漸形成了刑法法條、司法解釋、專項立法中的“指引條款”的刑法保護格局。
刑法法條。刑法中對自然資源保護的條款可以分成兩類:一是直接規制破壞自然源行為的條款,主要是指《刑法》分則中第六章第六節規定的“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主要規制了非法捕撈水產品、非法捕獵、非法占用農用地、非法采礦、非法采伐等行為,并規定了單位犯罪的處罰規則。
二是間接規制破壞自然資源行為的條款,主要對破壞自然資源周邊行為的規制,比如,前期資格的獲得,獲取資源后的運輸、販賣行為,也即包括了《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走私珍貴動物及其制品、走私珍貴植物及其制品的犯罪,還包括第九章“瀆職罪”中不當使用公權力的犯罪行為。
司法解釋。為了強化自然資源的刑法保護,為打擊犯罪提供更加明確的規范指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曾出臺過多個司法解釋。涵蓋了草地資源、動植物資源、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林業資源的保護。這些司法解釋的出臺回應了司法實踐中存在的疑難問題,對相關概念的范疇、入罪標準、犯罪未完成形態、共同犯罪、量刑、證據規則、刑事政策等問題給出了具體的法律依據。
指引條款與其他規范性文件。雖然刑事立法對于自然資源保護的條款整體偏少,但在改革開放以來,關于各類自然資源的專項立法如火如荼地開展,大都包括適用刑事法律的指引條款。這些指引條款分為兩種:一是指明適用刑法具體罪名;二是不指明適用刑法的具體條款,只是當某種行為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時,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除了指引條款外,還包括規制自然資源犯罪的其他規范性文件,這些文件也關涉立案標準、責任情形、責任追究等內容。
自然資源保護刑事立法存在的問題
可以說,經過數年的發展,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自然資源保護的刑事立法體系。但是,在新的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當前的刑事立法出現了以下問題。
保護對象存在遺漏。在發展過程中,人們逐漸認識到新的自然資源類型的保護價值,反映到刑法層面,就出現了新的需要保護的對象。結合學界研究,加上筆者總結,主要有三個問題需要刑事立法予以關注。
第一,濕地。在早期的研究中就有學者提出,在我國刑法中,沒有將破壞濕地的行為規定為犯罪。[1]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釋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罪時將土地的范圍進行了擴大解釋,包括耕地、林地、草地等各類土地。但是,該條文以“違反土地管理法規”為前提,因此,即便是進行擴大解釋,也必須是“法律及行政法規中關于土地管理的規定”。我國目前雖沒有法律及行政法規層面的規范性文件對濕地資源進行規制,只是有些省級、市級單位相繼頒布了濕地保護條例,但這些規范性文件的效力較低,不足以對適用刑法產生指引。
第二,地下空間。當前,刑事立法對土地資源的關注仍然停留在地表,與民事立法和相關實踐相比,存在滯后。《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百三十六條明確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從地表、地上和地下分別確立。結合不動產統一登記實踐,有學者提出建議,在民法典編纂的過程中,應當賦予地下空間與土地平等的法律地位,敦促自然資源管理部門進行統一規劃、統一管理。[2]這可以給我們啟示,刑事立法也應當有更加立體的視角。
第三,自然資源質量。現有刑事立法走過了計劃經濟時代向市場經濟時代的轉變,對于自然資源經濟功能關注較多,生態功能關注較少。因此,對于破壞自然資源的行為,往往關注破壞的數量,而忽視了質量。有學者認為,由于立法的空白,損害土地質量的行為無法得到規制。[3]實際上,其他類型的自然資源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整體保護理念不強。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深化改革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提出了整體保護的理念。在自然資源部成立之前,我國自然資源管理現狀可謂是“九龍治水”,不同類型的自然資源由不同部門負責。在這樣的理念之下,刑事立法也根據不同的自然資源類型設置不同的行為規范,缺乏對生態功能區的整體保護。
毫無疑問,這樣的立法不符合生態保護的客觀規律,在一個大的生態系統內部,任何一個要素出現問題,都可能對整個生態環境造成影響。刑事立法僅僅關注于某個自然資源類型,一方面會導致法定刑的配置偏輕,達不到懲治犯罪的作用;另一方面,可能會帶來刑法適用上的困難,當各類自然資源都受到影響,行為人可能會因一個行為觸犯多個罪名,按照罪數理論,構成想象競合犯,卻只能適用一個罪名進行處罰,難以為公眾所接受。
近來,國家的頂層設計對這一問題作出了回應,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統籌推進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中適用“國土空間”的概念,強化整體保護的理念,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由一個部門負責領土范圍內國土空間用途管制職責,對山水林田湖進行統一保護、統一修復的要求。刑事立法也應當及時與國家政策接軌,保障國家政策的有效推進。
預防性導向缺失。刑法不僅可以懲罰犯罪,修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還有預防犯罪的作用。預防犯罪的功能能否發揮,關鍵取決于刑法發動的及時性和刑罰設置的均衡性。就自然資源的保護而言,刑法并沒有做到上述兩點。
首先,關于刑罰權發動的及時性。《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的污染環境罪,以及第三百四十二條規定的非法占用農用地罪,仍然是以結果犯的形式存在的。早些年,環境法研究者就不斷提出,環境的破壞不是一蹴而就的,有時候要經過漫長的潛伏期,結果才有可能顯現出來。如果僅僅有行為,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只可能面臨行政處罰,但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面前,許多人會選擇鋌而走險,不僅造成環境執法壓力大,環境破壞行為還屢禁不止。因此,以是否產生結果來劃分行政法與刑法規制的邊界不盡合理,也使得刑法的預防作用微乎其微,需要我們另行尋找劃分標準。
其次,關于刑罰設置的均衡性。刑罰的均衡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從受到的處罰與產生的收益角度上講,如果獲取收益要承擔的風險是行為人所不能接受的,在一定程度上就會迫使行為人放棄行為;第二,相比于其他侵害法益的行為,如果嚴重程度相當,即應當設置相當的法定刑。縱觀我國破壞自然資源類的犯罪,法定刑設置是偏低的。污染環境罪、非法采礦罪、破壞性采礦罪、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的最高法定刑5~7年有期徒刑。與此同時,涉及經濟利益的捕獵、盜伐行為,則可以判處7~10年以上有期徒刑。破壞自然資源、污染環境的社會危害性不亞于毒品和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法定刑的嚴厲程度卻差別較大,難以實現罪刑均衡。
部門法銜接仍有不暢。1979《刑法》頒布實施以后,至1997《刑法》出臺前,自然資源法規相對較少,法規中涉及刑事指引條款的,基本依照《刑法》規定追究刑事責任。比如,1984年《森林法》中規定,盜伐、濫伐林木的,情節嚴重,比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追究刑事責任。隨著自然資源保護法規的逐漸增多,1979年《刑法》中無對應的條款,出現了一些以類推方式適用刑法的案例。但是,1997年《刑法》確立了保障人權的刑法機能,強調罪刑法定,禁止類推適用,使得各部門法與刑法的銜接出現了障礙。
之所以自然資源保護類的行政法規不斷涌現,一方面是由于隨著社會的進步,侵害自然資源的行為不斷發生,資源的價值被不斷認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刑事立法保護的缺失。客觀來說,我國針對自然資源進行保護的刑法條文較少,刑事立法者又缺乏自然資源管理的實踐經驗,無法與行政法規的起草者形成一致認識。因此,即便各自然資源行政法規中規定了指引條款,當在刑法中無法找到相應的犯罪與之對應時,還是只能適用行政處罰,會導致指引條款的作用大打折扣。
自然資源保護刑事立法的完善建議
結合當前的立法現狀,基于以上問題,筆者認為,自然資源保護方面的刑事立法應當作出以下調整。
立法理念的重構。如前所述,由于立法理念的偏差,破壞自然資源的刑事立法出現了后續的問題,涵蓋立法模式、罪名體系、刑罰設置等各個方面,是當前立法完善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在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下,自然資源保護刑事立法的理念應當發生轉變。有學者認為,刑法介入自然資源保護的理論基礎應當是法益、風險刑法和社會危害性。[4]對此進行深度挖掘,筆者認為可以是生態價值、預防性刑法和整體保護。所謂關注生態價值,即不僅要關注資源遭受破壞而帶來的經濟損失,還要實時關注資源的破壞情況;所謂預防性刑法,即要強調刑事手段的提前介入,將破壞自然資源較為嚴重的行為類型納入到刑法規制之下,改變當前單一適用結果犯的立法現狀;所謂整體保護,即前述的將山水林田湖作為整體的生態功能區,盡快推出更高位階的自然保護區法規,為刑事立法奠定基礎。在以上理念的指引下,可以考慮將破壞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犯罪單獨設立章節,細化入罪標準,以體現刑事立法對自然資源保護的重視。
罪名體系的擴充。為實現全面的保護,當前刑事立法的罪名體系還要盡量擴充。首先,要將濕地和地下空間作為直接的保護對象。《自然資源統一確權登記暫行辦法》第十五條規定,濕地可以單獨作為自然資源登記單元。《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明確了土地可以分層確權。可以說,其他部門法已經明確了濕地和地下空間的法律地位。在后續確權之后,濕地和地下空間也成為權利人的合法財產,可以產生經濟價值。同時,作為自然資源,其也要受到國家自然資源主管部門的監管。法律要為其提供保護,刑事立法自然也不能缺席。
其次,明確對自然資源質量的保護。在自然資源統一確權登記試點期間,不少專家認為,自然資源登記不是僅僅摸清家底,由于要為后續的開發、保護提供基礎,質量要素也應當體現在登記簿中。果然,《自然資源統一確權登記暫行辦法》明確規定,自然資源的質量也要寫進登記簿中,可以說,自然資源的質量需要得到保護已經在相關領域達成共識。兩辦印發的《關于統籌推進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中要求建立自然資源動態監測制度,及時跟蹤掌握各類自然資源的變化情況。可以說,在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構建的過程中,質量保護已經具備了技術和制度上的可能。
最后,要實現刑法與各部門法之間的銜接。刑事立法者要對各自然資源管理法規進行梳理,聽取自然資源管理改革一線工作人員的意見,擴充相關罪名,與行政法規中的指引條款相互銜接,以免讓“追究刑事責任”成為一句空話。
完善懲罰機制。為了實現懲罰和預防的目的,筆者認為刑事懲罰應當從以下三個方面予以完善:一是重新配置法定刑幅度。如前所述,我國破壞自然資源犯罪的法定刑整體偏低,尤其是對于自然資源載體的保護力度不夠,未來應當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適當提高懲罰幅度,以做到罪刑均衡。二是改變行政處罰與刑罰的界分標準。在我國行政、刑事二分的立法模式下,有些未能造成嚴重后果的破壞自然資源行為只能適用于行政處罰。如前所述,與一般的自然犯不同,破壞自然資源的行為后果具有一定的潛伏期,不利于刑罰的及時發動。且“后果嚴重”的標準難以客觀化,有時也會造成差異化執法,侵害人權。因此,筆者建議,可以根據質量破壞程度出臺國家標準,并以此作為劃分刑事處罰和行政處罰的分界點。三是實現處罰措施的多元化。自然資源遭到破壞后,懲罰是一個方面,實現環境救濟顯得更加重要。因此,可根據行為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進行差異化處罰,實現懲罰與預防的辯證統一。筆者認為,對于犯罪輕微的,可以僅保留犯罪記錄,創制一些非刑罰措施。對于一般的犯罪行為,在刑法規定下對其定罪量刑。對于犯罪嚴重,再犯危險性較高的主體,可以適用資格刑,使其不能從事相關領域工作,剝奪其再犯罪能力。
注釋
[1]蔣蘭香:《當前我國環境犯罪存在的問題》,《云南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第54頁。
[2]吳春岐、李磊:《地下空間確權登記探索》,《國土資源》,2018年第11期,第44頁。
[3]李祥金、吳小帥:《由“雙軌制”到“三位制”:我國土地犯罪的刑事立法模式研究》,《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第135頁。
[4]焦艷鵬:《生態文明保障的刑法機制》,《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1期,第78頁。
責 編∕馬冰瑩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rogress
Guan Yame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progress,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needs involvement of the criminal law.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on natural resource protection in China, such as the in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bjects, lack of overall protection concept, insufficient preventive guidance, and poor connection between departmental laws. In light of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reform of natural resources system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draw on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foreign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deeply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criminal theory. China's criminal legisl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should change its concept, highlight the ecological value, and focus on prevention and overall protec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expand the crime name system appropriately, improve the punishment mechanism, and make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play a better role.
Keywords: ecological progress, natural resources, criminal legislation, ecological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