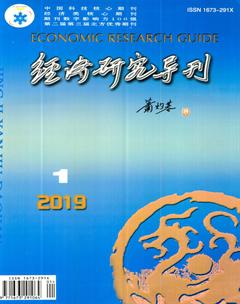社會權(quán)利視角下我國社會救助政策問題與對策建議
祁曉娜
摘 要:社會權(quán)利是保障公民從國家獲得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權(quán)利,對我國的社會救助政策有積極的引導(dǎo)意義。以社會權(quán)利為理論基礎(chǔ),對我國現(xiàn)行的社會救助政策進(jìn)行分析,總結(jié)社會救助政策存在的發(fā)展困境,提出做好政策銜接、強調(diào)主動脫貧、構(gòu)建參與機制等建議,以期促進(jìn)我國社會救助政策的完善。
關(guān)鍵詞:社會救助;社會權(quán)利;困境;改進(jìn)對策
中圖分類號:D632.1? ? ? ?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19)01-0032-02
我國《憲法》中明確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zhì)幫助的權(quán)利。”這使得公民從國家得到救助成為一項法定權(quán)利。當(dāng)前,我國建立起了以低保制度為核心的社會救助政策,它保障了貧困群體的基本生活,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但是我們也應(yīng)看到社會救助政策作為保障基本生活的一項制度,仍存在違背社會權(quán)利要求的地方,需要我們運用社會權(quán)利對其加以審視,從而促進(jìn)政策的完善。
一、社會權(quán)利與我國社會救助政策的價值契合
社會權(quán)利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而產(chǎn)生,是在基本民權(quán)和政治權(quán)利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逐步發(fā)展的,社會權(quán)利的實現(xiàn)標(biāo)志著公民權(quán)真正形成。社會權(quán)利是指公民共享發(fā)展成果,依法從社會獲得基本生活條件的權(quán)利,并且有權(quán)向國家要求條件的滿足。公民社會權(quán)利是人被賦予正當(dāng)理由向國家要求得到基本的平等的社會待遇,而國家則需要承擔(dān)相應(yīng)的責(zé)任,公民享有的獲得救助的權(quán)利便是社會權(quán)利的重要體現(xiàn)。因此,社會權(quán)利的價值訴求對于社會救助的完善意義非凡。
1.權(quán)利是一種資格,是法律賦予權(quán)利主體得到某種利益的可能性,是能夠與其他社會成員參與社會的機會。對于社會權(quán)利來說,它意味著生活陷入困難的人有從國家獲得幫助的資格。這包含兩層意思:一是享有資格的公民偏向弱勢貧困者,因為社會權(quán)利產(chǎn)生于人類社會的不平等,權(quán)利最初是為了維護(hù)窮人的基本生存,盡管后來社會權(quán)利所涉及的內(nèi)容和對象不斷擴(kuò)大,但其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出發(fā)點并沒有改變,因此社會權(quán)利的主體具有一定的偏向性;二是這種獲得幫助的資格需要國家責(zé)任來保證,社會權(quán)利是公民向國家主張的權(quán)利,國家對社會成員的救助責(zé)任不是施舍恩賜而是國家的法律義務(wù),公民有資格要求政府做出一定行為來實現(xiàn)社會權(quán)利。因此,第一層意思要求社會救助政策的對象應(yīng)為所有的貧困人群,他們均有資格獲得救助,第二層意思要求國家積極承擔(dān)救助責(zé)任,保證社會成員獲得基本生活條件,從而擁有共享發(fā)展的資格。
2.社會權(quán)利,“糾正過度的自由競爭所帶來的社會不公正,保障社會正義和社會安全,使人民能夠平等地獲得符合人的尊嚴(yán)的生活。”[1]社會權(quán)利調(diào)整社會利益關(guān)系,具有公平平等的價值內(nèi)涵,這對于我國建立在城鄉(xiāng)二元基礎(chǔ)上的不公平的社會救助政策有直接的批判作用,并且地區(qū)分割的救助政策同樣違背了公平平等的要求。社會權(quán)利要求國家積極作為,公民社會權(quán)利的實現(xiàn)需要國家權(quán)力的支持。但是,國家權(quán)力的干預(yù)要有限度和標(biāo)準(zhǔn),防止權(quán)力侵犯權(quán)利,特別是要有對權(quán)力的程序性規(guī)定,避免由于權(quán)力的自由裁量而侵犯貧弱者的社會權(quán)利。這對于社會救助政策來說,要求政策施行人員應(yīng)正確行使權(quán)力,保護(hù)救助者利益。
3.社會權(quán)利的實現(xiàn)需要政治權(quán)利的行使。公民應(yīng)積極通過行使政治權(quán)利實現(xiàn)和維護(hù)社會權(quán)利,例如公民對政策制定的知情和參與權(quán),表現(xiàn)在社會救助政策中,即要求受助者有表達(dá)政治利益的渠道,特別是當(dāng)應(yīng)享有的獲得救助的權(quán)利受到損害時,有正當(dāng)途徑維護(hù)權(quán)利。
二、社會權(quán)利視角下我國社會救助政策的現(xiàn)實問題
“權(quán)利作為保護(hù)人的需要、平等、自由,以及追求美好生活愿望的社會性措施,不僅是關(guān)乎人們生活幸福的概念,也是調(diào)節(jié)人類基本關(guān)系的重要手段。”[2]社會救助政策正是為了改善民生,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可見,公民社會權(quán)利的價值內(nèi)涵理應(yīng)作為社會救助政策的基本價值取向,每個公民在遭遇生活困頓的時候都應(yīng)平等地享有救助的權(quán)利,并且享受公平的救助待遇。然而,現(xiàn)行的社會救助政策卻有違公民社會權(quán)利的價值理念,存在發(fā)展困境。
1.從政策覆蓋對象上看,與社會權(quán)利主體要求脫節(jié)。社會權(quán)利產(chǎn)生于國家對貧富差距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沖突的關(guān)注,直接面對的是社會不平等問題,社會權(quán)利主體具有特定性,偏向社會貧弱者。社會救助政策應(yīng)該覆蓋所有的貧困群體,而當(dāng)前救助對象覆蓋面窄,使得許多本應(yīng)獲得救助的困難家庭被排斥在制度之外,阻礙了其權(quán)利的實現(xiàn)。當(dāng)前我國的社會救助政策以低保救助為基本保障,輔之以專項救助,這些制度的瞄準(zhǔn)對象主要是低保家庭,個別有條件的地方,建立了面向低收入群體的支出型貧困家庭生活救助制度,其受助對象有所擴(kuò)大。但是這在全國并不普及,從全國范圍來看,低收入家庭、家庭收入超過低保線而有特殊困難的家庭仍面臨著救助漏洞。如《社會救助暫行辦法》中的規(guī)定,教育救助對象為低保家庭成員和特困供養(yǎng)人員,就業(yè)救助的受助對象為低保家庭有勞動能力的失業(yè)者。可見,在救助對象上依賴于低保線,而忽視了其他可能需要救助的困難人員,導(dǎo)致其救助權(quán)利無法實現(xiàn)。
2.從救助供給上看,社會救助供給違背公平平等的要求。建立在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基礎(chǔ)上的社會救助政策在救助內(nèi)容和救助水平上存在城鄉(xiāng)差異,農(nóng)村居民無法享受和城市居民平等的社會救助待遇,導(dǎo)致權(quán)利實現(xiàn)不公,權(quán)利平等難以保障。以我國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低保為例,低保水平存在城鄉(xiāng)差距體現(xiàn)了制度的不公平。從近三年的數(shù)據(jù)來看,城市居民低保標(biāo)準(zhǔn)均顯著高于農(nóng)村,如2017年城市低保標(biāo)準(zhǔn)為每人每月540.6元,農(nóng)村為358.4人。而且,各級財政在城市和農(nóng)村低保的支出也有大的差距,各級財政在城市低保的人均支出達(dá)到了農(nóng)村的2倍。很明顯,政府對于城市和農(nóng)村的低保扶持力度并不相同,對城市扶持力度大,對農(nóng)村扶持力度比較小。
3.從政策執(zhí)行上看,公權(quán)強化阻礙權(quán)利實現(xiàn),背離政策初衷。“權(quán)力過大,權(quán)利會受到擠壓,社會法律關(guān)系便無法健康、和諧地發(fā)展。”[3]現(xiàn)行社會救助制度,管理者壟斷救助資源的分配,制衡機制缺失,難以避免權(quán)力尋租或救助對象瞄準(zhǔn)失靈的現(xiàn)象。公權(quán)力的利益偏好及“唯經(jīng)濟(jì)論”思維可能削弱其關(guān)注社會救助發(fā)展的動力。許多管理人員人為隨意確定被救助對象,使得部分真正需要救助的人被剝奪了獲得社會救助的權(quán)利。政策規(guī)定每個人在陷入困境的時候都應(yīng)有權(quán)利獲得社會救助,然而政策執(zhí)行中,利用公權(quán)而損害公民受助權(quán)利的現(xiàn)象卻屢見不鮮,這在農(nóng)村低保政策中可得到印證。有學(xué)者通過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某地基層政府出于發(fā)展目的扭曲低保政策的初衷,將本應(yīng)用于救助的低保資源用于鼓勵對自己有利的烤煙種植中,給村民帶來嚴(yán)重的不公平感[4]。因此,當(dāng)前我國社會救助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公權(quán)力壓制社會權(quán)利實現(xiàn)的困境,公權(quán)力傾向于掌控社會,以消除社會穩(wěn)定的隱患,與此同時最大限度地獲得利益。在這樣的邏輯下,困難人群應(yīng)享有的權(quán)利便徒有其名而無從落實。
4.在制度保障方面,過分依賴國家責(zé)任,公民社會權(quán)利被動實現(xiàn)。首先,當(dāng)前我國的社會救助制度是一種單純的政府行為,救助過分依賴政府的責(zé)任。無論是低保還是醫(yī)療救助、受災(zāi)人員救助等,均是自上而下政府單項救助的過程,已有的社會救助行政法規(guī)和部門規(guī)章強調(diào)的都是政府單方面給予貧困人群救助,受助人群被動等待救助,這就導(dǎo)致社會救助過分依賴政府責(zé)任,而缺乏公民在權(quán)利滿足上的主動性,顯然不符合現(xiàn)代公民權(quán)利的要求。其次,在救助政策制定、實施等各個環(huán)節(jié)缺乏公民參與的保障機制,是我國社會救助政策的又一現(xiàn)實困境。政治權(quán)利沒有有效行使導(dǎo)致社會權(quán)利訴求受阻,社會救助政策需要通過公民參與來保證救助內(nèi)容合理與切實落實,然而貧困群體只是被動接受政策幫助,難以接近政策的制定中心,成為邊緣群體。由于參與渠道不暢,導(dǎo)致受助者在權(quán)利無法保障時,采取群體性事件的方式來維護(hù)權(quán)利。
三、社會權(quán)利視角下我國社會救助政策的完善
社會權(quán)利重新定義了國家與個人的關(guān)系,個人被賦予正當(dāng)理由向國家要求得到平等的地位與待遇,而國家則需要承擔(dān)起相應(yīng)的責(zé)任。社會救助政策在促進(jìn)社會公平、維護(hù)社會和諧方面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們?nèi)钥梢园l(fā)現(xiàn)當(dāng)前社會救助政策還存在許多不符合公民社會權(quán)利要求的地方,需要我們不斷改進(jìn)完善[5]。
1.進(jìn)一步完善政策設(shè)計,做好制度銜接。我國社會救助制度以嚴(yán)格的低保線作為準(zhǔn)入門檻,而且與低保配套的教育、住房等專項救助往往與低保掛鉤,而非低保戶的困難家庭卻得不到應(yīng)有的救助,社會救助城鄉(xiāng)分割也不利于救助公平。因此,應(yīng)盡快實現(xiàn)城鄉(xiāng)社會救助政策設(shè)計的統(tǒng)一,例如長沙等地的城鄉(xiāng)低保一體化改革,實現(xiàn)了低保標(biāo)準(zhǔn)城鄉(xiāng)統(tǒng)一,今后應(yīng)在各地試點實踐的基礎(chǔ)上,逐步促進(jìn)全國實現(xiàn)城鄉(xiāng)社會救助統(tǒng)一。其次,要做好制度之間的配套銜接,改變以往“一切以低保戶為貧困戶”的標(biāo)準(zhǔn),根據(jù)致貧原因有針對性地進(jìn)行救助,區(qū)分有無勞動能力者,對有勞動能力者進(jìn)行技能培訓(xùn)和教育,鼓勵自立脫貧;無勞動能力者給予生活救助,實現(xiàn)分類救助,救助內(nèi)容恰當(dāng)。
2.轉(zhuǎn)變救助理念,強調(diào)主動脫貧。目前過分依賴政府責(zé)任,這種消極被動的單項式救助不利于制度發(fā)展,救助部門應(yīng)以積極的眼光看待受助者,他們并不是單純依靠救助的無能之人,他們也是寶貴的人力資源,也可以通過積極主動的方式實現(xiàn)自我救助,主動實現(xiàn)自己的權(quán)利。如西方發(fā)達(dá)國家主張的“以工作換福利”,就是強調(diào)通過個人的能力實現(xiàn)自助,而非消極等待。不過分依賴政府責(zé)任,并不代表著政府不履行主要職責(zé),政府仍然是社會救助政策的主導(dǎo),要在政策導(dǎo)向、為貧困群體提供提升能力的渠道、資金供給、制度監(jiān)管等方面發(fā)揮應(yīng)有的作用。
3.建立與完善公共協(xié)商機制,疏通參與表達(dá)渠道。公民獲得應(yīng)有的社會救助無法僅僅依賴于社會救助權(quán)利獲得法律的認(rèn)定,更需要的是一種公民與國家能夠互相表達(dá)自身目標(biāo)與訴求的互動機制。因此,我們需要在國家、社會與公民之間建立溝通的公共協(xié)商機制,政府決策能夠更有民眾基礎(chǔ),同時民眾的訴求能夠具有有效的傳達(dá)途徑。貧困群體也有自身的權(quán)利訴求,不應(yīng)因其處于相對弱勢就無視其利益的實現(xiàn)渠道。《社會救助暫行辦法》作為我國公民社會救助權(quán)利的最新確認(rèn),卻只規(guī)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受災(zāi)、醫(yī)療、教育、住房、臨時救助等權(quán)利,并沒有保障公民參與的內(nèi)容。因此,政策制定應(yīng)該規(guī)定和完善公民參與社會救助協(xié)商的方式和渠道,同時必須從制度上對監(jiān)督環(huán)節(jié)進(jìn)行規(guī)定,公民參與才能得到公平對待。
四、結(jié)語
社會權(quán)利對于我國的社會救助政策有積極的借鑒意義,當(dāng)前我國的社會救助政策在政策供給和執(zhí)行等層面存在發(fā)展困境,本文從社會權(quán)利角度審視政策困境并提出相應(yīng)的建議,即做好政策銜接,強調(diào)主動脫貧,構(gòu)建參與機制,早日實現(xiàn)社會救助的完善。
參考文獻(xiàn):
[1]? 張翔.基本權(quán)利的受益功能與國家的給付義務(wù)[J].中國法學(xué),2006,(6).
[2]? 楊春福.自由·權(quán)利與法治:法制化進(jìn)程中公民權(quán)利保障機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51.
[3]? 楊福學(xué).法益視野下低保權(quán)利和低保權(quán)力的衡平發(fā)展——以浙江省農(nóng)村低保制度為例[J].重慶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2017,(6).
[4]? 梁晨.農(nóng)村低保政策的基層實踐邏輯——以武陵山區(qū)某村為例[J].貴州社會科學(xué),2013,(10).
[5]? 楊華.論社會權(quán)的雙重價值屬性[J].長春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