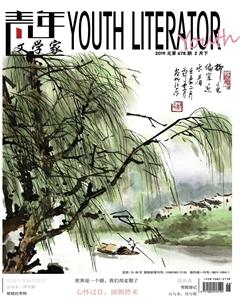淺談《一個人的村莊》中的哲思
許靜琳
摘 要:劉亮程是1990年代末期出現的重要散文作家。他是真正的農民作家。他是一個在大西北土生土居土長的人,作為一個農民,他“常常扛著一把鐵锨”,“與蟲共眠”,飼養牲畜以歲月;作為一個作家,他是整個村莊“唯一的旁觀者”,“和那些偶爾路過村莊,看到幾個生活場景便激動不已,大肆抒懷的人相比”,他“看到的是一大段歲月”,而這歲月在他的眼中又是那樣的與眾不同。他以對鄉村的真切體驗,用綿密厚實的細節堆積了一座文學的“村莊”。《一個人村莊》文集收錄了《寒風吹徹》《今生今世的證據》等多篇出色的散文,這些散文則以通脫而又富有靈氣的語言表達、簡單的敘事傳達出深遠而厚重的哲思。其中,作者常用寒冷、時間、荒蕪來表現人的孤獨,而逐漸荒蕪的家鄉則慢慢成為了他的靈魂上的領地,精神上的家園。本文將從幾個方面淺談《一個人的村莊》中的哲學之思致。
關鍵詞:一個人的村莊;哲學;孤獨感;時間;寒冷鄉土;遺失;靈魂領地
指導老師:繆軍榮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6-0-02
一、孤獨的哲學
劉亮程描寫的“孤獨”,不僅僅是一種心理感受,同樣也是一種生存狀態。“一個人在暗處處理著自己的事情,一村莊人在暗處處理著自己的事情。這是一大片原野上的事情。”這種沒完沒了的孤獨令人感到恐慌,“每個人最后都是獨自面對剩下的寂寞和恐懼,無論在人群中還是在荒野上,那是他一個人的”。這種孤獨主要反映于對寒冷的深切認識、鄉村封閉所帶來的心靈隔離、時間變遷帶來的荒蕪。
1.對寒冷的深切認識
劉亮程的文字總是顯出一種對寒冷的敏感,他對黑夜、冬天的寒冷幾乎是抱有一種清醒而刺骨的認識。因為劉亮程的生存環境十分惡劣,更經歷了一個不幸喪父的童年,他對于寒冷的孤獨感夾雜著對生命的渴求,對死亡的探討。“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冬天,有多少人放下一年中的事情,像我一樣用自己的那只冰手,從頭到尾地撫摸自己的一生。”在他筆下,寒冷是一個人的,是靜默的,是那些年老的生命需要苦熬度過的,也是成熟的靈魂用來收集,整理,“圍著火爐和書,一遍遍堅定不死的決心,寫出一些并不發出的信”。這種寒冷所帶來的是一個鮮活生命獨自邁向人生終結的孤獨感,但卻不是全然的畏懼,而是在清醒認知之后的接納,柔化,心懷悲憫。
李陀曾評價道:“劉亮程的才能在于,他好像能把文字放到一條小河里淘洗一番,洗得每個字都干干凈凈,但洗凈鉛華的文字又有一種厚重。捧在手里掂一掂,每個字都好像重得要脫手。”雖然作者總是用最精準的文字來向我們展現寒冷的孤獨,簡單卻沉重,悲憫而深邃;但我以為,深刻地感受人生的寒風吹徹,方可珍惜現世里的點點溫暖。
2.鄉村封閉所帶來的心靈隔離與精神干枯
劉亮程生活的地方是風沙彌漫的新疆,自然條件十分惡劣,外在的生存環境影響了作者的生命體驗和觀感。他筆下的鄉村沒有生機勃勃的氣息,對于人事的描寫十分簡易,偶有描寫,即便出現了,大多是佐證的材料,并不具備其該有的生命力。這便顯示出鄉村所獨具的封閉性,也就是費孝通所言的“地方性”。對作者來說,鄉村的生活是單調的、日復一日的,每個人都在按照一成不變的軌跡生活,默默地處理一個人的事情,默默地處理整個鄉村的事情。區域上的封閉使得人們的心靈逐漸與外界隔離,他們形成一個個孤立的圈子,與不變的熟人打一輩子交道。這種封閉帶來的心靈隔離是孤獨的,并且它不僅僅是個人的孤獨,個人的無理可依的空茫,而是群體心靈上的孤獨與精神干枯。它指明了生存環境的單調與荒涼,更指向一個群體的生存狀態、心理狀態。“我投生到僻遠荒涼的黃沙梁,來得如此匆忙,就是為了從頭到尾看完一村人浸長一生的寂寞演出”,作者發現了這種心靈的隔離與精神干枯,他才更想要渴望他的聲音中“有朝一日爆炸出驢鳴”。
3.時間變遷帶來的荒蕪
“時間”在劉亮程筆下經常出現,這是鄉村的時間,也是劉氏的時間,既是自然形態的,也是感性化了的。諸如“一生”、“一輩子”、“多年前”、“多少年后”等描述時間的詞語經常出現在他的文章中。他把時間巨大、漫長、不動聲色地改變鄉村一切的特質寫出來了。在巨大的時間下,人變得渺小,不論你是否愿意,時間使一切事物有了變遷,給人與村莊帶來了荒蕪。“一代又一代人熟透在時間里,浩浩蕩蕩,無邊無際。誰是最后的收獲者呢?誰目睹了生命的大荒蕪——這個孤獨的收獲者,在時間深處的無邊金黃中,農夫一樣揮舞著鐮刀。”時間的流逝、生命的此消彼長、鄉村的日漸荒蕪讓作者這個生存在此處的“旁觀者”感到孤獨,這種孤獨是一種見證者的孤獨,是對無限的時間下有限生命個體、事物逐漸被消磨、侵蝕的獨自觀看。
二、鄉土遺失下的哲思
鄉土與農村有著復雜的關系,物質上,地域地貌、生產生活、民俗文化等方面,鄉土等同于農村;但在精神想象、文化審美上,鄉土又超越了僅僅一群人聚集的地方,鄉土不僅是一塊地理空間,同時含有歷史信息、文化傳統、心理指向、情感投射等豐厚意味。以寫散文著稱的劉亮程,他筆下的“村莊”,是對鄉土文明價值的思考與表達。20世紀90年代的鄉土散文中,寫作者無一例外地呼喊著“尋找失落的鄉村記憶”、“鄉土文明的挽歌”等宣言,當故鄉的面貌遭到破壞,隨時間變得衰敗、荒蕪,對往事的鋪陳便如記憶般涌出。然而,記憶中的場景、人物、事件等一一浮現時,已經是一種虛空的幻想,因為家園本身已經不再是曾經的模樣,它在“遺失”。當作者走出鄉村,被社會所浸染,他明白那些不符合當代現實需求的人事風物,失去了在現實中功利性或非功利性功能,遺失是一種必然趨勢。
古往今來,許多遠近聞名的作家在年輕時,紛紛選擇背井離鄉,此后,記憶中的鄉土面貌對于他們來說無疑是一種遺失。然而正是這種存在狀態的改變和消逝,證明了它的存在,它不再以一種現實狀態存在,而是以一種精神狀態繼續存在。余華先生說:“毫無疑問,離開成就了我。”在家園生活時,我們往往不能夠體味到其存在的精神內核,隨著離開,故土荒蕪,遺失家園時,現實中的鄉土便以另一種方式構筑了個人的靈魂領地。
當劉亮程背井離鄉,單槍匹馬地去闖蕩生活,家鄉變成了故鄉,昔日的黃沙梁沒有變成想象中的樣子,而是荒蕪。這比繁榮更強大,它更深遠地浸透在生活中、靈魂中。就像史鐵生的地壇,永遠成為了靈魂的領地。
當家園荒蕪,他發現,所有踏上回家的路都是虛途,因為那個現實存在的實體早已遺失了。但這份遺失卻帶來對鄉土深刻的思考,“我走的時候,我還不知道曾經的生活有一天,會需要證明”“那些永遠匆匆忙忙走來路上的人,他們走到自己的歸宿了嗎”他在遺失中尋找回歸,最終,遺失的鄉土成為他精神上回歸的處所,幫他構筑了自己的靈魂領地,“當我死去,我已經全部的歸屬你”。
綜上,家園的遺失促成的是精神上的“回歸”。回家,真的那么重要么?黑爾塞說“它領你回家。每條通道都是回家的路,每一步都是誕生,每一步都是死亡,每一座墳墓都是母親。”回家,像是一種精神召喚,一個靈魂歸宿。自然的個體盡管呈現出不同的生命形態,最終卻都要歸入永恒的入口,回家,我們殊途同歸。盡管現實中的家園荒蕪,可那塊靈魂領地的入口卻一直為他敞開。
根據張振金在《中國當代散文史》中指出,八十年代以來的地域文化或鄉土散文呈現出新特點的具體表現,我們不難發現,《一個人的村莊》更偏向于“吸收現代文化、哲學思想,觀照地域文化和鄉村市井生活,以生命體驗和理性思考的結合,闡發深途、鮮活的寓意哲思,作品富有思辨色彩和獨特境界,表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時代精神”。他以獨到的見解將鄉村哲學融于詩意的語言,給當代浮躁的社會帶來了別樣的哲思。
參考文獻:
[1]《一個人的村莊》劉亮程 春風文藝出版社.
[2]從話語回到故鄉——論1990年代鄉土散文的話語類型 李保森.
[3]《靈魂的領地》周鴻 周敏慧 名作欣賞雜志社 2009年.
[4]《寒風吹徹中的現世溫暖》劉亮程 2017年.
[5]《中國當代散文史》張振金.